实验精神中没有自命不凡的成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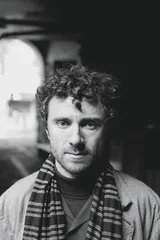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现在你在英国享有怎样的名声?对政府官员来说,你是那个什么都能设计的人?
赫斯维克:能有机会完成三个国家性的项目,我也觉得很幸运。这里的兴奋之处是提醒英国政府,如何把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部分。历史上英国是有创造力的国家,对出色的想法很有信心。而现在政府官员常常被视为畏惧创新的事物,觉得它们晦涩难懂,总是满足于一些无趣的东西。像上海世博会英国馆,我们不是为了向世界展示英国,而是试图显示英国还具有回到那个英国的能力。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们的各种项目中,似乎不存在所谓的赫斯维克风格?
赫斯维克:强化一种建筑风格,然后把它运用到世界各地,无论当地的具体情况如何,在我看来是一种无礼的做法。四处旅行你会发现许多地方越来越相像,加拿大和阿布扎比会出现相同的建筑,看到一座建筑就能认出是谁设计的。有时候,建筑风格比场所本身更有名。
三联生活周刊:那你认为在建筑和设计中重要的是什么?
赫斯维克:我们把所有的抱负放在项目中,做出与众不同的设计,即使像停车场、发电站这样一般人不会有所期待的场所。我觉得有趣的是如何设计出与众不同的停车场。我们设计的发电站旁边是2000家住户,如何为他们的生活增添一些东西?我想我的热情所在就是这样处于缝隙之间的项目。你也可以说我不是那么自信,所以去找一些冷僻的领域。不过,我确实是把人的价值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三联生活周刊:必须不断地保持独特的创造力,是否也是巨大的压力?
赫斯维克:在我看来,每个项目都是发明创造。其实无论艺术、时尚还是建筑,能够捕捉人们想象力的是那些有创造力的东西。也许因为英国过去有人为了飞翔而跳下悬崖的传说,“发明”这个词经常和“疯狂”联系在一起,我不在意这种“疯狂”的标签,毕竟在实验精神中并没有狂妄自大、自命不凡的成分。我们工作室的任务是“不以专家的方式成为专家”,不是说我有个想法交给团队去做,我们一起发明和锤炼,有时候到最后已经分辨不出想法的最初来源。我的角色是不断地推动,没有他们我什么也不是。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批评认为你们的作品过于有趣而流于肤浅?
赫斯维克:有些东西可能是视觉上吸引人的、看起来肤浅的,但同时包含了缜密的思考,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见得两者是截然对立的。像上海世博会“种子教堂”、奥运圣火盆等是很严肃的项目,如果事情看起来像是为了好玩,我就会有点戒心。我在意的是如何在重力影响下支撑起事物,如果能对付这种重力,你的设计就能获得你想要的轻盈感。
三联生活周刊:说起来奥运圣火盆具体是怎样的机械装置?它是如何升起的?
赫斯维克:它是一个靠电力启动的机械装置,总共有10个活动环,一个接一个地升起,204个花瓣铜器也是每个都有自己的汽油和电力供给。这里的难度是如何让机械装置像舞蹈一般轻盈优美地升起,而不是显得很吃力的样子。其实在开幕式前两天,它还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优美程度。最初我们得到这项委托的时候,他们一再对我们说,不管你们做成什么样的圣火盆,一定不要有活动的部件,因为悉尼奥运会上的点火装置就被卡住了2分钟。最后,我们居然设计了有最多活动部件的圣火盆,204个组件也都是不同的形状。幸亏各国代表的入场游行长达两个小时,让我们够时间把花瓣装到机械装置上。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现在上海有一个较大的地产开发项目?
赫斯维克:在中国的地产公司中,有少数特殊的、有追求的人意识到过去大量的建造开发对国家的文化发展没有什么贡献,能够接受创新构思的项目。不过,通常人们认为视觉上吸引人的、有创新的项目会有足够的资金供挥霍,但我们的项目大都是用低价的材料,在紧张的预算限制中,找到可以承担得起的方案,其中重要的是想法。
三联生活周刊:项目规模越来越大,是否你们思考和工作方式也有所改变?
赫斯维克:人的尺度千百年来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在整个策略上思考大的规划,同时对建筑的氛围保持敏感,创造出让人置身其中感到舒适的空间。无论规模大小,我们的设计最后都是落实到人的尺度。 自命不凡成分精神没有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