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之道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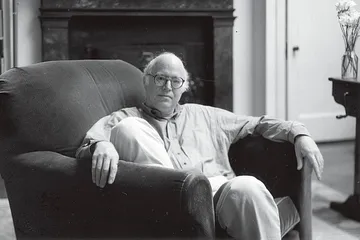 ( 理查德·桑内特
)
( 理查德·桑内特
)
合作能力的退化
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在《共同:合作的仪式、乐趣和政治》(以下简称《共同》)一书中探究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形成与维持。《共同》是桑内特计划的关于“人们为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技巧”的第二部。他在“三部曲”的第一部《手艺人》中提出,人类有天生的把事情做好的冲动。《共同》讨论的是合作的手艺。
早在德国社会学家西美尔问“社会是如何可能的”之前,哲学家和学者们就致力于发现合作的秘密。18世纪,伯纳德·曼德维尔和亚当·斯密认为,追求自利导致了合作。从19世纪晚期开始,社会理论家们更关心的是合作的缺失或衰落,而不是它的存在。在社会经常被诊断为自私和贪婪的时代,人们越来越难对合作的潜力产生热情。与这种当代体验一致,桑内特感知到了当代社会赋予合作以意义时面临的困难。通过对过去与现在的对比,桑内特指出,社会的合作能力受到了腐蚀,他警告说,我们正在失去使复杂的社会正常运转所需的合作的技巧。
歌德的朋友和秘书爱克曼曾经对歌德说,他认为社会需要爱和被爱。歌德回答说:“你这种天生的倾向并不普遍,希望他人会与我们和谐相处是很愚蠢的,我从不抱这样的希望。我总是把每个人看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会努力去研究和理解他的特点,但不会希望得到他的同情。”桑内特的新书是对爱克曼和歌德所代表的两种人的思考:一种是团结一致,追求头脑和意志的全面和谐;另一种是彬彬有礼,跟与自己不同的人或对自己有敌意的人相处的艺术。桑内特跟歌德一样,不信任团结一致,视之为多愁善感和强迫,他更喜欢彬彬有礼,有技巧地管理差异。他认为,彬彬有礼在过去30年间退化了,迫使人们回到团结一致的部落主义。他认为罪魁祸首是造成不平等、破坏工作场所的信任的涡轮式资本主义。他的主要证据来源于他对华尔街职员的调查。这些人鄙视他们的老板鲁莽的赌博,但又不能或不愿意去制止,他们的品德被当代的契约与自由裁量奖金给败坏了。他甚至怀念过去的流水线,它虽然很单调,但至少能够促成工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就像托尼·朱特注意到的,现在左派本质上是保守的,想保留过去的成果而不是建设更好的未来。
历史经验表明,合作通过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联系的深化而加强,合作的加强与不假思索的习惯和态度的发展是同步的,合作总是具有自愿与主观性的维度。它还需要信任。西美尔说,相互信任“既比知识少,又比知识多”,知道期待不会落空,人们才敢去信任别人,与人合作。桑内特在上世纪70年代就发现,体力工人拥有的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是他们创造的非正式纽带,这使他们能够应对异化、他们的工作与老板的要求,感到自己有些能动性。这些非正式的网络还能在危机期间强化相互尊重与合作,在发生紧急状况时能清楚地看出非正式关系的积极作用。在意外发生危机时,正式的规则与方式往往不足以应对新的环境,非正式网络更加灵活。为了效率,人们手中剩下很少自由决断的空间,他们只被期望遵守程序而非合作。今天,非正式的、自发的行为往往被认为是违反劳动合同,关系的正式化是因为担心非政治关系的不确定性。官方更喜欢权威,致力于预防意外,非正式关系则是流变的、不可预测的,正式化要把非正式关系捆绑到它的逻辑内。管理机构殖民人们的生活世界,掏空了非正式关系的内容,然后把它用做管理工具。在许多机构中,合作变成了团队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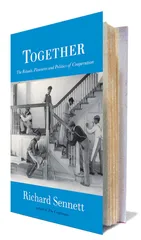 ( 著作《共同:合作的仪式、乐趣和政治》 )
( 著作《共同:合作的仪式、乐趣和政治》 )
桑内特认为,我们仍有感到乐观的理由。很多部落社会殖民世界都是因为土地和资源的冲突,但冲突结果成了无尽的创造力,促成了很多合作。早期的帮派形成了部落,后来,合并后的部落又进一步合并为酋邦,酋邦又变成了国家。在其中的每一步,以前相互竞争的群体形成了相互合作的联合,产生的财富要大于冲突。
英国哲学家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在《新政治家》上撰文说,桑内特提出的应对合作危机的两种补救方法都令人难以信服。第一个办法是以间接、默会和若无其事的老式外交艺术处理冲突,纽约的韩国商店老板与他们的拉美裔雇员谈判时就使用了这种方法。桑内特肯定不是提议把开设“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课程作为提高美国企业内人际关系的办法,但他提议的又是什么呢?他提出的第二个从老的工作室吸取了灵感的办法就更不可行了。他指出,许多手艺在社会领域都能够类比,就像手艺高超的工匠在一块木头上的硬结周围刻,而不是砍掉它,高超的谈判者会回避而不是镇压反抗。桑内特两种办法的失败都是因为同一个问题:在面对政治问题时,他提供的是个人化的解决办法,改变人的内心。他的一些提议很接近于老套的励志。比如,他对失业问题的反应是,建议被辞掉的工人在面试时表现得更加若无其事。政治问题需要政治的解决,而不是告诫人们振作起来。
“头脑风暴”的规则
美国神经科学作家约拿·莱勒在《纽约客》上说,美国广告人亚历克斯·奥斯本在1948年出版的《你的创造力》一书的第33章《如何组织一个团队来创造创意》中说,当一群人在一起工作时,成员们应该发起头脑风暴,用大脑去冲击一个问题。奥斯本说,头脑风暴能让10个广告人在90分钟内想出87个方案,几乎每分钟一个。他说,头脑风暴最重要的规则是,不要批评别人或做出负面反馈。如果人们担心他们的想法会遭到其他人的嘲讽,这一过程就会失败。他写道:“创意是一朵柔弱的花,夸奖会使它开放,贬斥会掐断它的蓓蕾。忘掉质量,现在只求得到许多答案。完了之后也许你的笔记本上全是荒谬得让你感到厌恶的想法,不要介意,放飞想象,让你的心灵提供答案。”头脑风暴立刻流行起来,成为最常用的创意技巧。当人们想从团队里榨出最好的想法时,人们仍会遵守奥斯本的规则,禁止批评,鼓励自由联想。头脑风暴背后的假定是,如果人们不敢说出错误的想法,结果他们就会什么也不说。但头脑风暴的问题是它不管用,几十年来的研究不断表明,开展头脑风暴的团队想出的想法远远少于同样数量的人独自工作时想出的想法的总和。但奥斯本指出,人类的创造越来越成为一种团队行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本·琼斯说,科学的进步导致尚未解决的问题都是非常难的问题,研究者们被迫变得越来越专业,因为一个人的大脑只能处理那么多信息。但他们又必须合作,因为最有趣的未解之谜都处于学科的交叉点上。“100年前,莱特兄弟可以自己建造一架飞机,现在波音公司单是设计和生产发动机就需要几百名工程师。”
难题的解决需要跨专业的合作,头脑风暴又没有用,团队该如何开展工作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查兰·奈米斯的研究表明,头脑风暴的无效源于奥斯本为它指定的规则:批评和辩论不但不会妨碍创意,而且会激发创意,因为争议会鼓励我们更充分地了解别人的想法,调整自己的观点。
还有社会学家研究了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团队创造力最强。美国西北大学教授布莱恩·乌齐想知道团队成员的关系对作品的水准有何影响,关系亲密的人组成的团队更好,还是相互陌生的人组成的团队更好?他对1945到1989年上演的474部百老汇音乐剧的创作团队做了统计分析,绘制了几千位艺术家的关系图。乌齐发现,创作团队的成员之间很陌生的话,其作品也不太成功;成员之间关系太熟,作品也不火爆,因为艺术家们的想法太接近不利于创新。最佳团队是熟悉程度中等的团队,这样的团队中有一些老朋友,也有新来的人。这种混合意味着艺术家们可以高效地互动,他们有熟悉的结构可以仰仗,也能吸收新想法。
既然为了创新,团体成员之间需要互动,就要为他们的互动创造物质条件,有研究说,最好的研究成果的特点是,其成员相互之间的距离在10米以内,成员之间的距离超过1公里的,其论文很少被人引用。新一代的实验室和公司办公室都努力使员工经常偶遇。1999年,乔布斯在规划皮克斯的总部时,最后决定整个大厦只在其中庭设一对卫生间。有人觉得去方便要走这么远很浪费时间,但后来发现,自己在前往卫生间的路上有不少收获。 合作头脑风暴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