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20世纪
作者:薛巍(文 / 薛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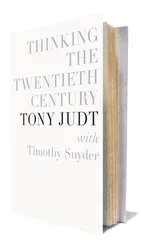 ( 著作《思考20世纪》
)
( 著作《思考20世纪》
)
知识分子的作用
任教于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托尼·朱特2010年因病去世,享年62岁。在出版《战后欧洲史》之后,他计划要写一本20世纪社会思想史。当疾病夺去了他的写作能力后,他的朋友、耶鲁大学教授蒂莫西·斯奈德提议把他们两人几周的对话编成《思考20世纪》一书。《卫报》说:“在这部不可思议的书中,两位探险者开始了一段只有其中一位能返回的旅程。他们要去的未知之地是一块我们称之为20世纪的可怕的大陆。他们的路线是穿越他们自己的心灵和记忆。两位旅行者都是忍受他们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困扰的职业历史学家,他们需要跟对方交谈,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
斯奈德说服朱特,除了谈观点外,也谈谈他自己和他的个人生活。如朱特自己所说:“如果你未曾陷入20世纪的幻想,你就不能充分地了解它的状况。”
朱特曾先后在剑桥、巴黎、伯克利和纽约执教,因此眼光一点也不褊狭。《旁观者》杂志说:“这是一部散漫的非系统化的著述,如果他本来想描绘的像是20世纪智力风景的地图,这部谈话录更像是在一位熟知这片风景的伙伴陪同下在其中漫步。朱特拥有不轻信、心态开放、持续注意多个研究领域、容忍复杂性、记性好等诸多优点。”
该书的第一部分概述了20世纪的知识史,第二部分集中讨论知识分子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社会民主党和历史学家应该干什么。最后得出一个悲观的结论:“我们将会发现,知识分子和政治哲学家面临这样一个情境,在这种情境下,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是考虑如何预防一个更糟糕的世界。”
 ( 蒂莫西·斯奈德
)
( 蒂莫西·斯奈德
)
朱特说,知识分子需要表明,他对地方性谈话的贡献,原则上会让这一对话之外的人感兴趣。不然,所有的政策专家和报纸专栏作家就都可以声称他们是知识分子了。但他又说,美国知识分子在伊拉克战争上的表现不能令人满意,只有一些记者表现出了正直与坚定。他还说过,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得出真理并解释它为何就是真理。在他看来,20世纪知识分子的罪过是“以自己眼中的他人的未来的名义裁定他人的命运”。
朱特花了很多时间攻击哈耶克,(“哈耶克患有政治自闭症,表现在他区分不了他不喜欢的那些不同的政治派别。”)维护凯恩斯,还说70年代的文化研究只是用“女性、学生、农民、黑人或同性恋等对当前的权力与权威配置感到不满的群体代替无产阶级”。福山评论说:“结尾处对公共知识分子的长篇讨论表现了朱特最不满的地方。他批评了很多人——托马斯·弗里德曼、大卫·布鲁克斯、迈克尔·曼德尔鲍姆、朱迪斯·米勒,包括我,批评我们要么轻则无知,重则盲从权力。”
 ( 托尼·朱特
)
( 托尼·朱特
)
福山说:“该书中给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它所描述的20世纪与现在的区别。我教的本科生都出生于柏林墙倒塌后,对他们来说,20世纪的意识形态斗争既没有意义,也很无趣。他们很幸运地没有生活在观念会变成改造社会的残暴计划、当一名知识分子经常会成为严重罪行的同伙的世界。”
朱特在讨论历史和思想史时,坚持要做切身的、语境化的理解。他道德感极强,对政治立场的美学与心理学也很敏感。他注意到凯恩斯的经济学和茨威格的小说有一个相似之处:对逝去的世界的怀恋。他说,英国人受到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吸引,与其说是喜欢其原则,不如说是因为它是“疲惫、怀旧、灰色的小英格兰所想念的一切”。
除了对对手严厉的批评与敏锐的感知能力,这本书中还有不少警句式的句子:“尼采如果出生在英国,会成为摩尔。”“柯拉柯夫斯基那时注意到,改革波兰就像要油炸雪球一样(不可能)。”
他抱怨说,他的前妻帕翠亚好像对她身处的任何地方都感到不满意,几年间朱特不得不跟着她往返于英国和美国。帕翠亚对朱特与一位波兰知识分子的谈话感到不耐烦。“帕翠亚忍受不了这种交谈,对自己被排斥在外非常不满,只想回家,躺在床上读《新闻周刊》,吃南瓜子。”
自由市场以外
1月底,艾伦·格林斯潘为《金融时报》撰写了《为资本主义一辩》一文,他在文中说:“自从启蒙运动孕育出资本主义以来,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生活标准及质量,在几乎停滞了数千年后,增长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平均寿命延长了一倍以上。过去200年间,全球实际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得地球能够养活7倍于以往的人口……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是合理的,只不过它所反映的是全球化和创新,而非缘于资本主义本身。”他认为,资本主义只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更多地监管资本,“无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存在什么样的缺陷,在被尝试用做其替代品的制度中,没有哪一种制度能成功满足所在国人民的需求”。
托尼·朱特则相信,相对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才是正道。他说:“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位列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中,它们并没有一个深深地偏向类似于回到德国式独裁的方向——哈耶克所说的他们因为把主动权交给政府要付出的代价。所以,对政府参与建设良好社会的两个最强的反驳——它在经济上行不通和它会导致独裁——都错了。”
今天,知识分子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把握经济和社会现实,朱特说,这种能力的消失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50年代末开始,知识分子主动地停止关心经济生活中明显的、可见的不公正现象,就像这些不公正现象正在被克服。知识分子们说,关注“巴黎伦敦落魄记”好像很幼稚,说真正的不公正比这要复杂,或者认为真正的压迫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收入的不公平分配。所以,左翼知识分子在发现不公正现象方面变得更加聪明了,对单纯经济上的不公平和困难不那么感兴趣了。第二阶段,自70年代末起,知识分子们不问某种行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问某一政策有没有效率。他们不问一项措施是好是坏,只问它能不能提高生产效率。他们这么做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不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不加批判地假定,经济政策的意义是生产资源。在生产出资源之前,讨论资源的分配是没有意义的。这有点像是软性讹诈:你不会不现实到把目标置于手段之前吧?我们是合理地建议一切始于经济,但这等于把知识分子缩减成了跑步机上的老鼠。当我们讨论提高生产效率或增加资源时,我们怎么知道何时停下?到什么时候,我们算是有了足够的资源,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分配了?我们怎么知道可以谈论甜点和需求而非产出与效率了?
朱特说:“我们又进入了一个恐惧的时代。人们再也不觉得拥有了进入一个行业的技能,就能让自己受用终生;人们再也不确信自己可以合理地期望在成功的职业生涯之后,可以舒服地退休;从现在到将来的合理推论都烟消云散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恐惧的年代是对未知的未来的恐惧,是对政府不再能够控制我们的生活环境的恐惧。”
朱特认为,恐惧的复归及其政治后果为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了最强的辩护:它既能保护个人的安全不受或真实或想象的威胁,又能保护社会团结不受威胁。“20世纪不只是民主与法西斯、左与右、自由与极权之间的斗争。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在辩论政府的兴起,自由的人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政府?他们希望它实现什么目标?由此看来,20世纪最大的赢家是19世纪的自由派,他们的继任者创立了福利国家,他们打造出了强大、高税收、积极干预的民主宪政政府,它能够包含复杂的大众社会而无需诉诸暴力或压迫。放弃这一遗产很愚蠢,所以下一代人面临的选择不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历史的终结还是历史的回复,而是以集体目标为基础的社会融合的政治,还是以恐惧的政治腐蚀社会。” 知识分子政治世纪思考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