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费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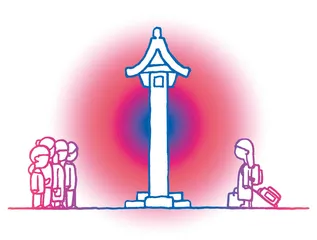
小姨从美国回来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她回来时的情形:虽只待了两周,可走时却颜容憔悴,几乎声泪俱下地述说:“以后再也不回来了。在美国每次都千盼万盼地想回来,总以为家就在这里,可每次回来后却又发现哪里都不是自己的家,于是又沮丧地回去。我已经找不着根了。”
虽然每次都嚷嚷着再也不回了,可过不了两年,小姨就会带着全家又回来。回来前总是会忙碌个把月,为大家精心地挑选着合适的礼物,总是满载而来,然后领受着大家的盛情:亲戚各家轮番在豪华酒店的宴请;朋友各位的喝茶、美容、SPA、桑拿加足疗;大家会少不了地聊到名牌、房子和车子。而小姨总会感觉与美国的生活是那样的错位。她总说:“在美国我们生活很简单的,穿的只要自己舒适就行了,吃的也不讲排场,健康安全就好了;周末一家人会去游泳、看孩子打棒球,或去听免费的音乐会。在芝加哥能经常欣赏到顶级音乐家的音乐会呢。遇到圣诞等节日开派对的时候,也是各家准备一个菜,没有哪家会感觉特别累。”每次走时小姨又会满载着盛情、关爱还有无尽的累而归。
小姨这次是积攒了她所有的假期一个人回来的。这两年她皈依了基督教。她看到国内的公婆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希望他们在离开人世时能够平静祥和;兄弟姐妹们为儿女之事而平添烦恼,希望开导他们能够不要过于强求;侄儿侄女们忙碌着事业、婚姻和家庭,也希望我们凡事不必过于执著,能够常常怀着一颗平安喜乐的心来对待万事万物。在电话中小姨也特意叮嘱:这次回来一定不要去外面酒店吃饭,在家里吃饭更安全;各家也可以各准备一个菜一起聚聚就好;也不打算安排很多朋友的应酬;如果能够去一个宁静的山村待上一两天,那就最好了。我们也一再强调不需要她给大家买礼物,问她可以准备什么带回美国,她调侃着:“国内的好东西都在美国呢,真的,什么都不需要。”
可说归说,自打接到小姨要回来的电话起,母亲和二姨就忙碌开了。那阵势比往年过年可隆重多了。过年是一年一次,小姨是两三年才回来一回呢。三姨也献策道:“等她回来时是十一月末,还可以赶上吃梁子湖的大闸蟹。”我也打算休休我宝贵的假期,带她去随州山村看看千年的银杏谷,泡泡温泉,回来时还可以带点香菇出口基地的香菇回美国呢(也算是找到了可以带回美国去的东西了)。
终于等到小姨回来的那一天了。她跟我们一起在随州的大山里转悠,山路上非常安静,除了路边偶有收香菇的摩托车驶过,河边的鸭群悠闲地在河里游着;看着我们在农家收土鸡蛋、银杏果,她在一旁也欣喜地吃着多年未吃过的柿子,竟然不听我们的劝阻,一口气吃了三个;看见种植香菇,也一手拿一枚最大的香菇,满脸童真地拍照;沿途还将好喝的土鸡汤、腊肉菜薹等所有好吃的饭菜拍下来,说是回去也可以让她先生和孩子们饱饱眼福。看见路边的走地鸡,她也会欣喜地多次叫唤:“一定要再去农家捉只土鸡带回去啊。”在菜市场还竟然擅自做主,买了一条很大的武昌鱼,在归途中后备厢里那条已遭凌迟的鱼还多次不停地蹦跶,弄出巨大的声响。她很认真地侧耳聆听,边听还边对我们说:“快听,这鱼竟然还活着呢。”黄昏时远方的袅袅炊烟升起,山里的房子在薄雾中静默着。
我还陪小姨去我们小时候生活的长堤街转了转。这长堤街与那全国闻名的汉正街平行。那曾经记忆中很宽大的街道现在看来却是那么的狭窄;街口卖早点的那家小店自是早已不在;小时候夏天趴在竹床上吃早点做暑假作业的那条小巷竟然不到1.5米宽;好不容易见到一张儿时熟悉的面孔,也依稀只是那个轮廓尚与记忆中的面容相吻合。等到小姨、小舅和我一起爬上老屋的阁楼,看到外公、外婆的遗像蒙尘纳垢,被寂寞地遗忘在阁楼的一角,小姨再也忍不住了,她号啕大哭道:“你们儿子只知道分房子分金子,父母的相片谁都不要。我们儿子老问我外公、外婆长什么样,我们家有没有家谱,我老是答不上来,这照片我带回美国去。”
这次小姨依然是满载而来,走时也依然是满载而归:带着给朋友们的众多有中国特色的礼物,还有我们为她准备的香菇、茶叶、腌制的香肠,甚至还有周黑鸭;还有我每回出去旅游时收罗的有各地特色的小礼物,一并带走的最沉重的还是那深深的失望……
前几天小姨从美国来电,说两个儿子都放寒假了,看到他们在家里时不时地晃荡,可由于她的假期全用完了,无法带他们去欧洲滑雪。去欧洲的机票价格只有来中国的机票价格的一半,她还郁闷地喃喃道:“早知道会是这个结果,也许应该带孩子们去欧洲滑雪的。”
每次我都希望小姨能够不带什么礼物地轻装回来,然后我们也要尽量轻松地迎接她的回来。这样当她一有想回来的念头,她就能够立马实现了。我们就能够有更多机会更好地交流了。可这个愿望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