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智力工具箱里还缺点啥?
作者:陈赛 ( 美剧《生活大爆炸》剧照 )
( 美剧《生活大爆炸》剧照 )
美国的电视剧喜欢调侃科学家在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方式是多么的可笑。《生活大爆炸》里就有许多生动的例子。比如佩妮正在为要不要和莱纳德约会而纠结,谢尔登搬出了“薛定谔的猫”,智商一向不高的佩妮立时醍醐灌顶。用一个量子力学的实验来形容男女之间的感情,却如此生动准确,可谓编剧的神来之笔,同时也说明,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在应付日常生活方面并非毫无可取之处。
在这个“聪明是新的性感”的时代,科学家一直在锲而不舍地寻找智力的物理源头——智力不仅取决于大脑多个区域的效率和能量,还取决于不同区域之间的连接速度和强度。他们发明了可以提升大脑智力的药物,还有可以插入大脑的电子器械。一切都是为了让人变得更聪明一点。
Edge一直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扎堆”的地方。这是一个刻意保留了原始论坛形态的精英网站,汇集了西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自从1998年起,网站每年都会向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多位知识精英提出一个问题,比如去年是“互联网如何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更早一点的还有:“你对什么感到乐观?”“你最危险的想法是什么?”“什么是你相信,但不能证明的?”
今年的问题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史蒂芬·品客提议的,被认为是迄今为止Edge提出的最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科学概念”可以来自哲学、逻辑、经济学、法学,或者其他分析性学科,答案不能超过1000字——如果一个概念需要1000个以上的文字来解释,它对我们的心智是负担,而非工具。
一般来说,普通人应付日常生活靠的是经验主义。我们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训练,以至于觉察不出日常思维的种种误区,比如顺从性偏见、集体迷思、自利性偏见、道听途说等等。这些思维误区会影响我们对生活的判断,从最琐碎的细节,比如预测多快能穿过一条街,到足以影响一生的重大决定,比如应该跟谁结婚,当然还有我们的政治和道德立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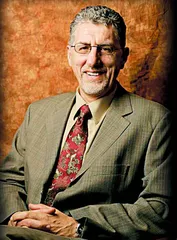
“科学概念”可以作为一种智力资本,提升普通人的智力水平,最早是新西兰科学家詹姆斯·弗莱恩提出来的。他认为,当一个科学概念(SHA)从某个学科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用语,比如“市场”、“安慰剂”、“随机样本”等,只要你学会准确使用这些概念,就可以将它作为一种批判性思辨的模板,并在真实世界中加以验证。
正是这位弗莱恩教授发现,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的总体智商每年都在持续提升(IQ测试一般包含多个子项,每一个子项代表不同的思维技巧。我们在几何图形、识别抽象的相似性、故事叙述等方面的技巧提高了,但数字记忆、词汇和常识方面并没有提升)。科学界用他的名字为这种奇怪的现象命名——弗莱恩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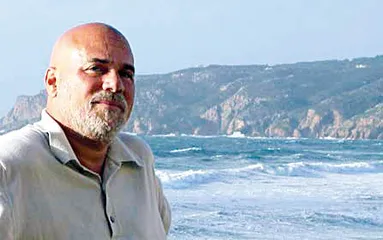
在排除了教育、营养等诸多可能性的原因后,弗莱恩教授得出的结论是,人类IQ的普遍提升,并不是我们的智力本身出现了飞跃,而是因为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这个世界对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需求在不断变化。比如我们越来越倚重抽象逻辑,而不是个人经验,来把握这个世界。所以当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狗和兔子有什么关系”时,现代人的回答往往是:它们都是哺乳类动物。如果100年前,你得到的答案会是“狗可以用来抓兔子”。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逼迫人们不得不在新的问题面前进化出新的智慧。这次Edge收到的160多个答案中,其中不少都暗含了环境对认知需求的变化,比如“认知过载”、“信息流”、“集体智慧”、“合作”等。
《连线》英国杂志的主编推荐的概念是“个人数据挖掘”。2003年,Google总裁艾瑞克·施密德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自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一共制造了5EB(1EB=10亿GB)的数据。现在我们每两天就产生这么多数据。个人数据的累积已经超出了我们的应付能力,无论在信息的获取和使用上,都要求一种更科学的方法。每个人都应该思考,如何从这些海量的数据中提取有意义的信息和模式,用于预测和指导行为的依据?如何从数据的关联中发现隐藏的趋势或风险因素?“‘个人数据挖掘’作为一个认知工具会时刻提醒你,在一个过度分享的环境里,如何利用数据发现自我,从而做出更有益于自己的健康、事业与情感的决定。”他写道。
 ( 约翰·波洛克曼 )
( 约翰·波洛克曼 )
媒体学者道格拉斯·洛西科夫(Douglas Rushkoff)推荐的概念是“技术的偏向”。人们总是以为,技术和媒介是中立的,它们的使用方式或内容才决定其影响力。所以,我们毫无保留地接受身边的各种技术,iPad、Facebook、汽车,而从未考虑过它们内置的偏向。比起枕头,枪内置了杀人的偏向;比起自行车,汽车内置了郊区化的偏向。在普通人的智力工具库中加入这个概念,我们能更有意识,更有目的性地使用技术,而不被技术的意志所蒙蔽,比如iPad是一种偏向于消极消费,而非积极创造的工具。为了抵制这种偏向,你应该找一个有键盘的。
Haecceity(此性)也是一个有趣的概念。它的本意是指“个体的本质”,对某一物体难以觉察的心理归因,使它在相同的拷贝中独一无二,比如你的结婚戒指。克隆技术、基因工程、数字复制,这些技术正在不断地破坏我们对物体完整性的信仰。“此性”的价值就在于抓住了大部分人对于“真实”的直觉。

其实,关于人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聪明,弗莱恩教授还有一个理论——人是社交动物,不同心智之间的启发是相互作用的。20世纪以前,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接触和交换新的想法,但20世纪相继出现的各种大众传播技术极大地加速了思想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随着互联网的出现,信息、思想的交换和共享已经变成普通人的日常思维习惯。Edge的创始人约翰·波洛克曼(John Brockman)就喜欢自称是“思想世界的旅行者”。Edge和TED的走红证明了人们对思想的渴求。思想是这个时代的摇滚。■
约翰·波洛克曼、Edge与第三世界

作为Edge网站的创始人,约翰·波洛克曼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过去30多年来,他的品位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人的智力生活。
约翰·波洛克曼是移民后代,父亲是奥地利人,他从小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贫困的天主教社区长大。上世纪60年代,他是当时纽约先锋艺术派的一员,和鲍勃·迪伦一起唱过民谣,给安迪·沃霍尔的地下电影做过经理。约翰·波洛克曼并无科学背景,最初对科学也并不感兴趣,但因为当时科学是先锋艺术家们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约翰·波洛克曼也逐渐被裹入其中。
此后30年,他一直是美国出版界的金牌经纪人,代理的作家都是美国一线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如史蒂芬·品克、理查德·道金森、丹尼尔·丹尼特、马丁·里斯、克雷格·文特等人。在他的穿针引线之下,这些知识精英逐渐汇集到同一个平台上,从最初的线下聚会到Edge网站论坛,形成了所谓“第三文化”的阵营。
“第三文化”的概念是波洛克曼从C.P.斯诺那里借来的。1959年,C.P.斯诺在《两种文化》中提出,知识界逐渐分裂成两个极端: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二者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斯诺的乐观设想是,“第三种文化”将会弥补科学家与文学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但在美国的现实情况是,科学家直接取代了传统知识分子的角色,直接面向公众解释生命的意义。
波洛克曼认为,物理学、进化生物学、信息科技、基因、神经生物学、心理学、工程学、材质化学……这些学科的进展都关系到“做人意味着什么”的重要问题。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同时有了工具和意愿,对人的本质进行科学研究。
波洛克曼一直拒绝把Edge变成一个Web2.0网站。这仍然是一个经过严格编辑的精英论坛,而不是一个任何人都能加入进来的共同辩论平台。英国的《观察家》杂志曾经把Edge称为“在线皇家协会”,这是英国人所能给予的最高的赞美。波洛克曼曾说,这个网站的价值不在于使科学流行起来,而在追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正在关心什么问题。所以,自从1998年起,网站每年都会向全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多位知识精英提出一个问题。■
可以让你变聪明的科学概念
确定性的无用性,卡洛·罗威利(Carlo Rovelli),法国物理学家
不确定性是知识最初的源头。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经科学证明”的事实,而只有概率的程度。科学的根基是向“怀疑”保持开放,质疑一切,尤其是自己的前提。当新的证据和论据出现,一个好的科学家永远准备好改变视角。对普通人来说,理解这个概念,可以在未知面前保持谦卑的态度。
10的次方(Power of 10),
卡尔·佩吉(Carl Page),企业家
1968年,查理和雷·埃姆斯事务所制作了一部长10分钟的纪录片,名为《10的次方》(Power of Ten),从一个正在野餐的家庭为原点,展现了我们的世界从1025米(10亿光年)到10-16米(0.1飞米)之间的不同形态。这部纪录片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关于“尺度”的概念,能帮助我们理解宏观世界与微观世界中很多难以把握的概念,比如我们一生有109秒,全世界的GDP总和是1014美元,大脑中有1015个神经突触等等。
亚自我,道格拉斯·T.肯里克(Douglas T.Kenrick),心理学家
30年前,认知科学家科林·马丁戴尔(Colin Martindale)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认为我们每人都有不同的“亚自我”,各自负责不同的功能,比如寻找伴侣、与朋友相处、在职场奋斗、照顾后代,而不是一个统一的“自我”在控制你的大脑。这个概念能帮我们理解人类行为中的某些不一致和非理性,比如一个人可以对朋友言听计从,却对父母粗暴无礼。
实验法,罗杰·尚克(Roger Schank),心理学家
科学家最基本的一种思维方式是,如果你想知道些什么,就得动手做实验,分析数据,归纳结果。如果将日常生活中的一切事务,如参与政治、抚养孩子、处理人际关系等都视为一种“实验”,会给我们的人生打开一个新的视野,效率也更高。
折中原则(Mediocrity Principle),
梅尔斯(P.Z.Myers),生物学家
“折中原则”是科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理解人类从何而来,万物如何运转的入口,但对普通人来说,却是很难把握的一个概念。折中原则的基本意思是,你并无特殊之处,人类并无特殊之处,地球也无特殊之处,世上发生的绝大部分事情只是自然的、普遍法则的结果——这种法则适用于任何地方、任何事情。至于如何理解这些规则,则是科学的目标。
集体智商(Collective Intelligence),
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科普作家
人类成就的关键不是个人智慧,而是网络现象。人类社会的进步,是通过社会分工,每个人各司其职,交换、分享和结合成果,最终完成一些他们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事情。就像经济学家雷纳德·里德(Leonard Read)在《我,铅笔》一书中所观察到的,现代社会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制造一支铅笔,它的知识散落在成千上万个石墨矿工、木材工人、设计师和工厂工人身上。■ 波洛克工具箱智力科学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