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指的故事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特鲁贝尔说,过去,罗马商人用手能数到100万——双手并拢,十指交叉。蒙田在《雷蒙·塞邦赞》中说:“我们用变化万千的手势来表示需要、答应、呼人、辞退、威胁、祈祷、恳求、否认、拒绝、询问、赞赏、计算、表白、后悔、害怕、难为情……”现在,这些手势的四分之三大多数人已经不再使用了,我们转而大声说出来、用笔写下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手势很贫乏的世界,手势像很多小语种的口头语一样在迅速地消失。也许只有在意大利手势仍很繁荣。“老派的英国男性可以手插在衣兜里,一个手势也不做地过完一辈子。他一生中可能只会被动地做一次手势——在教堂里牧师给他做祝福的时候(食指和中指并在一起给他往里弯)。”
特鲁贝尔的专业背景使得他更注意手指在装饰和表达方面,反映在绘画和雕塑上的用途,他很少说到在美术馆不太能见到的手在力量和日常生活方面的用途。关于后一个方面,蒙田在随笔中专门写过大拇指:“医生说,大拇指是首要的手指。在拉丁语中它的意思是另一只手,似乎拉丁人有时也把大拇指做整只手讲。罗马人规定,大拇指受伤的人免于上战场,似乎是因为无法紧握武器。有个人打赢了一场海战之后,便把战败敌兵的拇指都砍掉,使其失去战斗力,无法再划桨。”
中世纪时期,在法国克鲁尼修道院,教士要宣誓保持沉默,但手语的出现使得教士们能够像可以说话时一样健谈、贫嘴、八卦。在他们的手语中,表示鲑鱼的手势跟表示妇女的手势是一模一样的,因为那时女性发型上的褶子很像鲑鱼。从理论上说,这会造成各种误解。但是,由于教士不得随意谈论女性,所以“捕捉、剖开和油炸××”只会指鲑鱼,发生误会的情况被降到了最低限度。
特鲁贝尔几乎没写到手艺,但分别用两章写了手套和美甲。这两章中包含了很多奇闻轶事。色诺芬嘲笑波斯人戴手套御寒非常女人气,就像英国人嘲笑戴手套的法国足球运动员一样。在美国小说家菲利普·罗斯长篇小说的《美国牧歌》中,主人公的父亲是一个手套工厂的老板,他在带人参观工厂时说:“看到接缝了吗?皮子边缘缝的线的宽度——手工如何就看那儿。针脚和皮子边缘之间大概只有三十分之二英寸宽。瞧瞧这接缝多么笔直。所以我们的手套那么上乘。因为笔直的缝线、上乘的皮料,还有它的色泽、韧度。像新车里面一样好闻。我喜欢上乘的手套。它给我带来无与伦比的快感。”到20世纪中叶,女性美甲流行起来后,戴手套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开头说:“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但特鲁贝尔提到,亚里士多德发觉很难对触觉加以分类,在《论灵魂》中说它是一种相比之下比较阴暗的感官,比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低级,因为连最原始的生命形式都有一定的触觉。触觉跟性、睡眠、疾病和死亡等生理过程的关系更密切,其他感官能够感知和判断远处的事物。但亚里士多德有时又把触觉作为最核心的感觉:既然我们是在寻求感觉物体的本原,既然感觉是可触的意思,那么很明显,并非一切对立都构成物体的形式和本原,只有与触觉相关的才如此;因为正是靠了对立,即触觉方面的对立,事物才区分开。虽然触觉很低级,但是它对我们的存在感具有决定意义。所以蒙田说,不要试图去超出我们身体的局限:“试图去抓住比我们拳头大的东西、搂住比我们臂弯宽的东西、跨过比我们两腿能够伸展的距离宽的沟,这是不可能的、吓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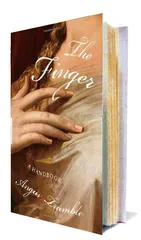
(文 / 小贝) 小说故事手套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