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谈谈马斯克与苏东坡
作者: 高塬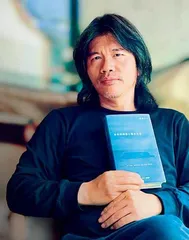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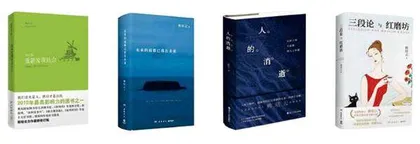
作家熊培云最近一直待在老家——江西九江的一个村子里,观察田野里的油菜花,在山岗上听德沃夏克,和邻居拉家常……远离城市和互联网,他“心里安静下来”。对作家来说,除非自己爱热闹,否则,一张安静的书桌比什么都重要。
熊培云曾经是爱热闹的。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席卷全球时,他刚刚大学毕业,读的是历史和法律,却进了报社。每天写新闻评论,一个月40多篇,什么事儿都要讲两句。作为最早一批网络用户,他还在论坛、网站、博客上激扬文字。
2002年,熊培云从报社辞职,赴法国巴黎大学深造。游历各地的所见所闻,欧洲时事的现场直击,借他山之石,熊培云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有了更多思考。其间,他开始写书,书写得厚,写起来还刹不住,《重新发现社会》《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自由在高处》《这个社会会好吗》……光看书名就透着一股知识分子的热切劲儿。这些社科类书籍销量竟也意外的好,“如果这个环境已经在给你做减法,你首先该想到的是给自己做加法,要相信时代每一天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这样的句子,无论何时,总能打动人心。2010年,《重新发现社会》获得了第六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熊培云也尝过热闹的苦头。如王朔所言“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约莫10年前,熊培云渐渐收了声,转而开始写诗。2014年出版诗集《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后来又有《未来的雨都已落在未来》。他也写小说,《三段论与红磨坊》,讲一个昆虫学家静悄悄地躺在床上,陪伴他的是几只猫,还有无穷无尽的梦。
直到去年年底,那个熟悉的熊培云又回来了。他关注时下最热的科技变革,写下《人的消逝: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以下简称《人的消逝》)一书,洋洋洒洒近500页,从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讲到《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从古罗马角斗场延伸到互联网、硅基生命……技术正在重塑社会的结构,成为反思时代问题的重要切面。当机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做得比人类更好,人类与科技最好的关系是什么?科技至上还是文化至上?生而为人的意义何在?《环球人物》记者就相关问题与熊培云进行了一番笔谈。
物的危机与人的危机
《环球人物》:《人的消逝》一书是您时隔多年回归社科类写作,这本书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熊培云:《人的消逝》的思考与写作,最早起源于我在南开大学教书时,有关微博的一个小课题。然而,我并不擅长限时的命题作文,纵大限已到,仍一字未动。相较于简单且应景地剖析为何人之间互掷刀剑,我宁愿关注价值深邃恒远的“人之消逝”。而且,拜当年在巴黎大学所受科技人类学课程的熏陶,以及网络时代的日常实践,在授课之时我对互联网的异化已积累诸多批评。
2017年秋天,我开始了在英国牛津大学为期一年的访学,因此有机会比较系统地思考问题。还记得在那段时间里,经常坐在户外的长椅上写下所思所想,有时甚至会坐到午夜,看熙来攘往的人流陆续散去,对“人之消逝”也算是有了更多的体悟。
《环球人物》:相比《自由在高处》《重新发现社会》等前作,《人的消逝》从技术史框架来探讨人性危机,您在书中写道:“技术进步是死神又换了一把镰刀”“手机是一个随时出卖、背叛我们的卧底”。在普通读者看来,这些话有耸人听闻之嫌。您是反技术的吗?
熊培云:《人的消逝》并不否定人类所取得的科技成就。它着重并集中探讨的是随之而来的人类正在面对的两种危机:外在危机和内在危机。
外在危机,主要是物的危机。一方面,是工业化以来人类对自然之物的竭泽而渔导致严重后果;另一方面,是人造之物对人类的反噬。具体到原子弹、互联网与人工智能,仅从安全计,这些人造之物完全有可能在其“觉醒的一刻”将人类推向深渊。
内在的危机,从本质上来说是人的危机。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伴随着物的发达以及人对物的高度依赖甚至崇拜,一个人已经越来越不需要另一个人了,人与人变得疏离、冷漠,每个人重新孤绝地回到塞满机器的电子山洞。
物的危机与人的危机合二为一,这就是我担心的“人的消逝”。
马斯克试图把地上的我们的肉身送上火星,而苏东坡则是将天上的月亮放进我们的心里。科技与人文,一个向外,一个向内,一个安置身体,一个安放灵魂,哪个更重要呢?
把飞船开到想象的月亮上
《环球人物》:在您的心中,人与科技理想的状态是怎样的?
熊培云:从1996年上网以来,我差不多是互联网进入中国后最早触网的那批人。我曾热情地拥抱科技,直到我出国留学之前还在互联网公司做兼职。我甚至一度认为活着就是为了看到未来有什么新的科技。后来我意识到,科技发展和人类进步是两回事。我开始从对科技的狂热中冷静下来。说到底科技只是工具,不是目的。我认为最好的状态是我们与技术同行。
《环球人物》:科技浪潮下,有人说文科、文学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您怎么看?
熊培云:我出生于江西永修,在江边长大。16岁时,有一天我背着一个军用书包出远门,里面装着由几个作文本订成的诗集,和在学校食堂买的两个馒头。记得那天风和日丽,我坐一辆小巴士,到100多里外的九江日报社投稿。
后来考上南开大学,我开始了或许是一生中最孤独的4年,每天生活在自己创造的“天堂”里。有个老乡见我终日沉浸于精神世界,便劝我说天堂是没有的,不要整天胡思乱想了。我说,要是没有想象中的天堂,宇宙要人类何用?他接着说,人类的飞船都已经开到月亮上去了,早就证明天堂是不存在的。于是我就问他,你能够把飞船开到我想象中的月亮上去吗?当然他做不到,我们谈论的是两个世界。
人生在世,免不了各种身心俱疲。马斯克试图把地上的我们的肉身送上火星,而苏东坡则是将天上的月亮放进我们的心里。科技与人文,一个向外,一个向内,一个安置身体,一个安放灵魂,哪个更重要呢?我想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吧。有时候并非简单的机器驱逐了人,在所谓人的消逝之前,很多人已经自我驱逐了。就像我在小说里感叹的,很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虽然每日辛辛苦苦,却从未真正走进自己的命运。

人是最初的起点
《环球人物》:从最早做新闻评论算起,您对社会的观察与写作已有近30年,一直以来,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熊培云:说得更远些,从高中时握住了诗歌的笔算起,我真正关注的永远是人。最近这些年,我试图重新捡起诗歌和小说,无论社科还是人文,在我这里,人都是最初的起点。
《环球人物》:您在书中写了一段自己关于“人”的观察:“人变得更自由了,也变得更无依无靠了……人正在毫无悬念地变成时间海滩上一块光滑的鹅卵石。”随着技术的发展,人与人连接、联系变得更便捷,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似乎更远了。
熊培云:自从有了互联网,许多人的生活同时走向了反面。他们面对的不是时空的扩大,而是时空的坍缩。既然从前需要用脚去丈量的地方,现在按一下鼠标就可以了,那么他就宁可足不出户。与此同时,数字世界的24小时开放,不是让人拥有更多时间,而是使得时间被各种无用的信息填满。
世上的每个人安安静静地躺在互联网铺好的信息摇篮里。在那里,空间四通八达,时间终日明亮,不仅晨昏一起消失了,遥远的地方和附近的人群也消失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缩略为人与手机的关系。
我曾经和朋友讨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人与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爱,而我认为是“亏欠”。比如父母养育了孩子,孩子感到对父母有所亏欠。比如洪水来袭,军人冒死护堤,当地的民众为军人的勇敢牺牲感到亏欠。或者,大风大雨天外卖员送来订餐,订餐者为他们的辛劳感到亏欠。
以上种种,亏欠像是榫卯结构一样将人类紧紧地咬合在一起,可如果这一切都是机器和技术实现的,人就处于某种互不需要的状态。相较于恩重如山的压迫或知恩图报的负担,它更多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互助互利后泛起的“情感的涟漪”或者“隐秘的纽带”。恰恰是这些构成了人类有情的风景。
《环球人物》:除了社科写作,您最近还出版了一部小说《三段论与红磨坊》,为什么会转向虚构创作?
熊培云:《三段论与红磨坊》是去年夏天写的,我花了两个月写完。和日常的修修补补相比,虚构是另起炉灶,与现实世界平起平坐。
前段时间,我心血来潮,试着给DeepSeek下指令,让它写个短篇小说,出来的是很平庸的作品。技术目前还达不到人类创造主观世界的能力,因为它并没有生活经验,它更多的只是一个数据库。而我们每个人是多么与众不同。尽管在不远的将来,人造的技术或许将驱逐真实的人类,甚至取而代之,但一个柔软而诗意的心灵世界,将是人类留存于世的坚强堡垒。
编辑 陈娟 / 美编 苑立荣 / 编审 张勉
熊培云
1973 年生于江西,作家、学者。现执教于南开大学。代表作《重新发现社会》等。近期出版《人的消逝:从原子弹、互联网到人工智能》,引发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