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极端宽容,又极其暴力?
作者:张星云 阿道夫·希特勒曾下令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但他痛恨虐待动物,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并且很喜欢自己养的狗布隆迪。布隆迪死时,他伤心不已。波尔布特曾是红色高棉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在他发起的政治运动下,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的人罹难,但在青年时代当法语教师时,他很受学生欢迎,人们都觉得他亲切和善、为人诚恳。为什么极度暴力的人也会有和善的一面?想要解开这个谜题,也许要从1987年说起。
阿道夫·希特勒曾下令杀害了数百万犹太人,但他痛恨虐待动物,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并且很喜欢自己养的狗布隆迪。布隆迪死时,他伤心不已。波尔布特曾是红色高棉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在他发起的政治运动下,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的人罹难,但在青年时代当法语教师时,他很受学生欢迎,人们都觉得他亲切和善、为人诚恳。为什么极度暴力的人也会有和善的一面?想要解开这个谜题,也许要从1987年说起。
此前的十多年里,哈佛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兰厄姆一直在坦桑尼亚自然栖息地研究野生黑猩猩,1987年他的兴趣转向动物行为研究,他开启了一项对黑猩猩的新研究课题,并前往东非和中非的多个黑猩猩栖息地进行考察和研究。但就是在这段时期,一个不容忽视的发现再次扰乱了他的研究计划,他在非洲雨林中发现,黑猩猩有时会表现得异常暴力,一个族群的雄性黑猩猩会联合起来杀死其他族群的黑猩猩同类。
1996年,他和戴尔·彼得森共同出版《雄性暴力:猿与人类暴力的起源》,被学界视为历史上第一部将人类学、心理学、灵长类动物学结合在一起来分析人类暴力起源的研究著作。他们认为,雄性黑猩猩的种种暴行是人类暴力的雏形:雄性强暴雌性是为了延续自己的基因,族群之间的武力冲突并非为了争夺食物,而是为了消灭异己。他们由此得出结论,人类本质上具有暴力倾向,而且是从黑猩猩基因中袭承下来的,是进化的结果。显然这一结论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了极大争议,人们认为,暴力传统违背了人性的许多方面,人类按理说应该是高度社会性的生物,是善于合作和利他的。
之后的很多年里,兰厄姆逐渐成为全球重要的灵长类研究学者之一。在继续研究黑猩猩的同时,他也开始研究其姊妹种倭黑猩猩。倭黑猩猩是从黑猩猩的祖先分化出来的,两者是与人类联系最密切的猿类物种。它们看起来很相似,以至于两个物种在被发现后的许多年里,都没有被分别确认为独立物种。
但很快兰厄姆就发现,两个物种的行为有着极大不同。黑猩猩好斗,而倭黑猩猩更平和。黑猩猩族群是由体形较大且善于使用暴力的雄性主导,通过恐吓和殴打同类来维持统治,追求等级、竞争和权力。而倭黑猩猩生活在母系社会,雌性并非用暴力,而是通过情色维系和统治族群,以平等、宽容和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兰厄姆还经常能观察到雄性黑猩猩和倭黑猩猩都会进行的一种“球赛”游戏,两只雄性在树干周围互相追逐,试图抓住对方的睾丸。雄性倭黑猩猩可以与来自其他族群的同类一起玩这个游戏,但雄性黑猩猩只能与同一族群的其他成员玩游戏,遇到其他族群的同类,就会立即显示出敌意。
作为与人类联系最密切的猿类姊妹种,为什么这两个看起来如此相似的物种的暴力倾向会如此不同?这与人类的行为又有什么关系?这些疑问,是近年灵长类动物学研究中被反复讨论的。兰厄姆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人类既像倭黑猩猩那样极其宽容,又像黑猩猩那样极端暴力?
纵观人类历史,几个世纪以来,人类文明不仅充斥着战争、政治迫害、屠杀,同时还发明出了心脏手术、太空旅行和单口喜剧,后者需要人类高超的协作能力才能达成,包括高度的宽容、信任和理解。那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人类进化出了如此善良、优秀的品质,但同时也进化出了使用极端暴力的能力呢?
2019年,兰厄姆时隔23年出版新书《人性悖论:人类进化中的美德与暴力》,试图探讨人类暴力更深层的进化史。他在杜克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肯尼斯·道奇(Kenneth Dodge)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将人类暴力分为两种类型——反应性攻击倾向和主动性攻击倾向。反应性攻击倾向是感性的,往往是因受到挑衅或刺激后在愤怒或暴躁状态下的暴力行为,比如酒吧打架。而主动性攻击倾向是理性的,是有预谋、有计划且深思熟虑的暴力行为,比如谋杀、团伙犯罪。地球上的野生动物,通常是反应性攻击倾向和主动性攻击倾向都很高,尤其是肉食动物,狼、狮子、斑鬣狗如此,黑猩猩更是如此。但反观人类,人类的反应性攻击倾向极低,面对挑衅或刺激有着极高宽容度和忍耐力,正因如此,人类才拥有了温顺的美德。兰厄姆举了个例子,数百人可以在狭小、不舒服的飞机座位上安静地坐几个小时,这对其他动物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人类的主动性攻击倾向却是地球上最高的,所以人类才能频频发起最需要精心计划的暴力行为——战争。兰厄姆进一步追问:人类是如何进化成如此的?
 在野生动物中,低反应性攻击倾向,也就是宽容、忍耐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品质,只有被人类驯化过的动物,才会拥有温顺的特质,比如宠物狗不随便咬人,家养兔子可以让孩子们随便抚摸。
在野生动物中,低反应性攻击倾向,也就是宽容、忍耐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品质,只有被人类驯化过的动物,才会拥有温顺的特质,比如宠物狗不随便咬人,家养兔子可以让孩子们随便抚摸。
上世纪50年代末,俄罗斯遗传学家德米特里·贝尔耶夫(Dmitri Belyaev)曾做过一场著名的驯化试验,他在俄罗斯大大小小的狐狸养殖场里寻找到130只最为温顺的银狐,将它们圈养起来,并对它们的一举一动进行评分,只有进攻性最低、最温顺的狐狸才有机会进入试验的下一阶段——繁殖后代。就这样繁殖到第六代时,狐狸开始表现出“驯化综合征”,它们不仅对着人类摇尾巴,还会等待人类抚摸,甚至会像狗一样舔人的脸,当研究员叫它们的名字时,它们会跑向人类。贝尔耶夫1986年去世,但是实验并未终止,他的团队继续着驯化狐狸的实验,如今已经到了六十几代。不仅在行为上,甚至在外观上也出现了很多“驯化综合征”迹象,这些狐狸的毛色要比野生狐狸淡很多,出现色斑,耳朵低垂。
兰厄姆根据这一经验,最终在倭黑猩猩上找到研究的突破口。虽然倭黑猩猩是从黑猩猩的祖先分化出来的,但它们很温顺,反应性攻击倾向很低。并且他还发现,倭黑猩猩表现出许多“驯化综合征”的特征,它们的大脑比黑猩猩小,脸和眉脊更小。贝尔耶夫就曾认为,被驯化的物种头骨变小是为了表现得没那么具有威胁性,而被“抑制生长”的大脑使成年倭黑猩猩保留了很多幼年行为,比如喜欢玩耍。
但显然倭黑猩猩是野生动物,并不是被人类驯化的,进化过程中也没有受到人类的影响。经过多年的观察,兰厄姆发现,对于母系社会的倭黑猩猩来说,雌性倭黑猩猩们通过联合行动,来压制族群中好斗的雄性,反应性攻击倾向低的雄性黑猩猩更容易获得交配机会,这样一来,倭黑猩猩便通过自我驯化,在基因选择中不断降低自己的反应性攻击倾向。
兰厄姆认为,人类如此低的反应性攻击倾向,也是自我驯化的结果。早在20万至30万年前刚出现智人的时候,人类的自我驯化就已经开始了,语言的出现极为关键,这让身体瘦弱的男性们可以联合起来,谋杀在族群中欺凌他人的强壮男性。这一行为不断发展后,就成了死刑。人类通过死刑,杀死族群中反应性攻击倾向最高的人,或者通过长时间的监禁,使其减少获得交配的机会,以完成遗传选择,达到自我驯化的效果。
人类通过主动性攻击行为,共谋实施死刑,共同创造出更大的社会控制体系,这种关系比任何其他物种都更深刻。一个不守规矩、违背群体规则或名声卑劣的人会受到死亡威胁,个人道德感正是在这种自我保护的动机下演化而来的。而且,这种个人道德感达到了其他任何灵长类动物所不及的高度,拥有强烈顺从行为的人类可以获得安全,而强烈顺从行为导致群体内竞争减少,人们更加尊重他人利益,群体内部更加团结,群体得以蓬勃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遗传选择机制作用下,经过1.2万代之后,人类的反应性攻击倾向越来越低,而主动性攻击倾向越来越高。但兰厄姆认为人类的自我驯化还没有完成,人类的反应性攻击倾向还有可能进一步降低,人类还有可能变得更温顺。与此同时,更公平、更和平的社会并不会轻易出现,因为人类强大的合作能力不仅可以用来禁止暴力,也可以造成更大的暴力。
 ——专访哈佛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兰厄姆
——专访哈佛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理查德·兰厄姆
三联生活周刊:1996年你发表的《雄性暴力:猿与人类暴力的起源》在当时的生物人类学界争议极大,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你怎么看当年的这本书?它在这十几年里,对人类理解自己的暴力起源,起到了什么作用?
理查德·兰厄姆:《雄性暴力》1996年得出的结论至今有效,不过现在我们有了更多支持这一结论的信息。2014年的一项研究涉及18个黑猩猩族群和4个倭黑猩猩族群,所用的样本数量是《雄性暴力》的5~10倍。那项研究再次明确证实,黑猩猩的联合杀戮行为是其物种特征,与倭黑猩猩正好相反,并且这种特征不是人类对其环境干预造成的结果。许多证据都在支持我1996年得出的核心结论:在动物界,杀死自己同物种的行为动机是权力分配,实力强大的族群试图杀死更孱弱的同类族群,但如果双方势均力敌,就会保持和平状态。
但在1996年,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存在着强大的自我驯化现象,暴力也还没有被分为反应性攻击倾向和主动性攻击倾向。这些观点,我都在《人性悖论:人类进化中的美德与暴力》里进行了详细阐述,因此可以说这本最新出版的书是对《雄性暴力》的极大补充。
其实我的这两本书都是在说,人类的暴力和攻击行为存在一个生物学基础,当我们将人类与我们的近亲进行比较时,会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大部分生物人类学者和大众读者都认同我的想法,但肯定也有人不认同。
三联生活周刊:关于暴力的演变,后来哈佛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认为,人类越来越不暴力了,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人们不再向往战斗至死的荣誉战争,也不再有公开处决,很多国家谋杀率在下降。他的观点在人类学界同样引起巨大争议,如今你怎么看史蒂芬·平克当年提出这一观点的影响?
理查德·兰厄姆:我很欣赏平克,觉得他的研究细致、准确。但他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争议,比如他预测随着凶杀率的持续下降,人类最终会走向世界和平。但在我看来,他没有足够强调的一点是,即便未来战争次数越来越少,但由于核战争的威胁,战争造成的潜在死亡人数仍然是非常高的。此外,战争死亡人数往往与和平状态的持续时间成正比,世界大国处于和平状态时间越长,一旦爆发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也就会越高。
三联生活周刊:为了解释人类的暴力行为,你提出了两种攻击倾向的概念,将人类攻击倾向分为反应性攻击倾向和主动性攻击倾向,并以此提出“人性悖论”理论,虽然人类个体更善良了,但人类也更善于组织并使用有目的性的暴力。按照你的理论,如何区分各种人类的暴力行为?哪种暴力形式会被历史淘汰掉?哪种暴力形式会越来越普遍?
理查德·兰厄姆:主动性攻击是理性的、有计划的、针对特定目标的暴力,比如抢劫或者蓄意袭击。而当一个团体而非个人有计划地实行主动性攻击,那将是更加危险和恐怖的,比如街头犯罪、战争或极权统治。反应性攻击则是应对威胁或挑衅的一种自发的冲动反应,施暴的动机往往是情绪使然,激情冲动,攻击的对象通常就是发出威胁的一方,比如酒后斗殴。
校园霸凌和性骚扰可以被视为主动性攻击,也可以被视为反应性攻击,这要看施暴者的动机。属于主动性攻击的性骚扰者,或者性侵者,最后更倾向杀死受害者。
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的社会对这两种暴力的施暴者都会进行惩戒,但实施反应性攻击的人更容易被针对,这些人最终会被捕入狱,而善于使用主动性攻击的施暴者则备受社会青睐,因为他们能帮助某一群体在类似战争的冲突场景下通过计划好的暴力取得利益。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社会,人们越来越少冲动性地使用暴力,而是越来越擅长使用有计划的暴力。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你的说法,在野生动物中,温顺是一种罕见的品质。人类则通过自我驯化,变得越来越温顺。是否可以说,自我驯化就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方式?按照你的“人性悖论”,人类的善良是真正的善良吗?还是一种在死刑、监禁等强大暴力下产生的驯化效果?是否还可以说,死刑和道德审判,曾经是人类改善社会的重要方式?甚至是人类有别于其他动物进化的重要方式?那现在呢,它们的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
理查德·兰厄姆:是的。如果我们回到30万年前海德堡人向智人的进化过程,我们可以说,自我驯化是人类进化的主要方式。智人与其直接祖先之间的解剖学差异就在于自我驯化。同时,语言也是人类进化的关键因素,正是复杂的语言系统开启了自我驯化的过程。
如果我们将人类的善良定义为低反应性攻击倾向,或者说更不愿意打架,那么人类的善良就是真实的。但如果我们也承认,人类通过死刑等主动性杀戮消灭了最具攻击性的个人,那这确实导致了顺从的人获得了基因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使用死刑是残暴的,但它的确使现在的人类比30万年前的祖先以及大多数野生动物更善良、更温柔、更不具进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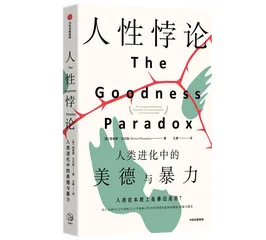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你的说法,倭黑猩猩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而黑猩猩是典型的父权社会,黑猩猩更暴力,追求的是等级、竞争、权力,倭黑猩猩更宽容,追求的是平等、宽容和协商解决。这种比较是否可以投射到现代人类社会的性别比较之中?是否可以说,男性天生更愿意使用暴力?女性天生更善于合作和理解?
三联生活周刊:按照你的说法,倭黑猩猩生活在母系社会中,而黑猩猩是典型的父权社会,黑猩猩更暴力,追求的是等级、竞争、权力,倭黑猩猩更宽容,追求的是平等、宽容和协商解决。这种比较是否可以投射到现代人类社会的性别比较之中?是否可以说,男性天生更愿意使用暴力?女性天生更善于合作和理解?
理查德·兰厄姆:男性肯定比女性更多地使用反应性攻击,尽管研究较少,但男性很可能也比女性更多地使用主动性攻击。
进化让性别在心理学上的差异变得更明显。但合作中的性别差异研究重点并不关注他们是否合作,或者合作多少,而是关注与谁合作。男性往往人际网络广阔,拥有很多合作伙伴,但通常关系浅薄;而女性合作伙伴相对较少,通常是与有血缘关系的人合作,但关系牢固深厚。基于化石分析和猿猴行为学研究,30万年前的人类男性祖先比女性更具进攻性,鉴于此,我们可以说相比于女性,男性更多地参与到了自我驯化的过程,针对反应性攻击倾向低的男性基因选择推动了人类的进化过程。其实女性的变化也很多,中更新世的女性比现在的女性更坚韧,但我们对这一变化过程研究很少。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最高法院新近推翻了“罗诉韦德案”,在一些国家,女性的生存权、堕胎权都在受到威胁,为何在人类进化了这么久之后,男性依然对女性保持着持久的暴力?你在书中提到,人类这一自我驯化的过程尚未终止,那么,未来人类的父权制社会将继续吗?是否会出现像倭黑猩猩一样的母系社会?
理查德·兰厄姆:人类社会是父权制的,部分原因是男性比女性更高大更强壮,但父权制度更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性的,男性主导组成了立法、宗教和行政等机构,并通过制定制度来控制女性。这种制度层面的男性统治可以追溯到智人时代,当时男性结成联盟来控制最具暴力倾向的个体,就像黑猩猩或者大猩猩一样,现在男性仍然结成联盟制定法律来控制最暴力的男性,让他们入狱,这样的联盟也被用来控制整个社会,包括控制女性。而对倭黑猩猩来说,雌性比雄性更容易结成联盟,这与人类相反。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书里说,面对死刑的威胁,人类为了个人安全而顺从,进而产生道德感和群体团结,那舍生取义、大义灭亲的集体主义精神真的存在吗?群体利益超越个人利益会是进化的最终结果吗?按照你的说法,人类的进化过程还没有结束,那将来人类会更加顺从,也更加会使用更强大的有计划的暴力吗?
理查德·兰厄姆:人类不像蚂蚁那样是纯粹的集体主义,但人在精神层面的本性倾向表明,当条件合适时,我们可以搁置自己的个人目标,将自己的利益融入更大的整体目标之中。
你关于未来的问题很吸引人,但显然人类进化取决于许多不可知的因素,以至于我们对未来的预测也仅仅是猜测而已。不过,回顾过去一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不难发现其中一些趋势始终很强劲,比如我们正在不断失去文化多样性,比如语种和方言的消失,比如人们正在组成越来越大的群体和联盟,死于暴力事件的比例越来越低,家庭生育率更低了,个体寿命更长了,在生活方式上更依赖于其他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人类这一物种能够再存活几千年,我们可以合理地预判这些趋势都将会持续下去。因此,未来的人类可能生活在一个说同一种语言的统一超级大国中,生活在一种个人暴力被高度控制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家庭小而长寿,人们为了更大的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自由。
但当然,其他影响因素很可能与现在不同,我们可以预料到即将到来的资源竞争、新的战争和新型武器,以及太空殖民的未知影响、不断变革的生殖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等。总之,蓄意或意外使用大规模新型武器的威胁是非常大的,未来的挑战之一是找到方法来减少这一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