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滋有味的老鲍
作者: 张宝明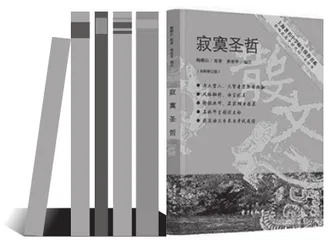
在朋友圈的短视频上,我终于见到久违的老同学鲍鹏山了。
说起鲍鹏山的爆棚,那可不是一夜之间的事。记得在分别20年之后,忽然有一天在书店了翻到了这位大仙的《寂寞圣哲》,一下子勾起我对他的一些片段记忆:在江南一个小城的一所大学的一个大班里与他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他是四班,我是五班,你来我往,纯属日常。毕业那年,去了西北边陲支边的义举让他成为一名“好男儿”。见到他的时候,已经是脸庞黑黝黝、头顶白花花的西北汉子了。文字耐读,又很畅销,那股羡慕嫉妒恨的感觉一下涌上心头:岂能便宜这小子,于是连拉带拽的签名本《寂寞圣哲》传到了俺的案头。不过,让人心中很是不快的也是这本书的签名:“张保民兄哂阅”,我名字的三个字被他写错俩。这也佐证了我们的过往不是属于“甚密”一类。
最我老鲍在商务印书馆新出版的签名本《中国人心灵》传寄于我,而且签名一字不差:张宝明三字完全正确。
《中国人的心灵》还有个副题“三千年理智与情感”。当我回复拿到后,他还特意嘱咐说:“看看上面盖的章!”原来“偏安斋”印章是他很在意的事情。老实说,我这次关注的是他有没有将我的名字写错。我在看过签名后首先注意到的还是他在后记中为自己“种瓜得豆”之喊冤叫屈:“这本书在这么年里不温不火。”
的确,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插花栽柳间阴差阳错。老鲍说的不温不火一定是和他作品的其他版本相比而言的。不必遮掩,就我看到的这本洋洋洒洒的文字而言,它并没有《寂寞圣哲》那样让我入胜。这话儿也许会惹得老鲍不快活,但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事实。
老鲍不好惹,因为他总是乱说乱动(我就在一篇小文中将其比做“思想多动症者”《美文》2023年第1期),万一被他尥了蹶子、任起性子和我怼起来,真都不好收场呢。看来,与他对话还得说点题外的话。这,还得其从他新出版的《孟子开讲》说起。
以我的阅读史说,看到《中国人的心灵》后,我首先联想到另外两个近代人物。一是梁启超,再就是辜鸿铭。前者有1899年写就的《中国魂》,后者则有1915年付梓的《中国人的精神》。梁氏所谓的“国魂”意指“兵魂”,是尚武精神的旨归;辜氏所谓的“国神”则是指“从容、冷静、练达”的人情世故或说处世之道。具体到鲍氏,那则是对礼义之邦、文明古国三千年诗词歌赋小说散文中慈悲情怀的发掘与打捞。
培根铸魂是当下的一个热词。当“国魂”“国粹”“国学”“国故”乃至“国神”“国心”“国根”纷至沓来之时,于是乎关于如何铸造的祖传秘方或出奇制胜的雄才大略也都会出来大显身手。撇开众说纷纭的各式看家本领,我们单挑梁氏、辜氏、鲍氏这三氏的底牌亮亮。
想当年,梁氏有鉴于日本武士道的成功之道,情急之下抛出了制造兵魂一招:“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其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中国魂安在乎》,《清议报》1899年第33册,P3)辜鸿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在军国主义风卷残云之势下,更是在中西文化物质与精神、动与静的比较下出手,将梁氏“师夷长技”的“硬碰硬”幻化为中国人固有“良心”以昭示于世人,颇有从“硬碰硬”到“软着陆”的人文关切。他意在世衰道微的人类走势中寻觅到意思可以突围的曦光。在这位老夫子看来,凭借武力打天下的军国主义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相形见绌:“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荷枪实弹的“乌合之众”需要放下屠刀,以立地成佛的心态向中国人求恕问道。
比起梁公的以“刚”克刚、辜公的以“柔”克刚,鲍公(他和包拯的确是小老乡,不过此鲍非彼包)更多地将注意力聚焦在了中西两“岸”(此岸与彼岸)的死缠烂打上。毋庸讳言,三者出的都是(我的)“中国心”这张牌,但在立意上却有语境与语义的千差万别。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道德,一个时代有一个的表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为此我们可以说的天花乱坠,直到口吐白沫。鉴于老鲍那样讨厌的弯弯绕,我们暂且打住。
不过,既然说到老鲍的此岸与彼岸的生命苦海之摆渡,我们就不能借机上“岸”。原来,《中国人的心灵》之所以不温不火,还要从起文本的经意上说起。经意,也就是文章的经营意识。说白了,也就是文字的谋篇布局、立心开意。当我拿到老鲍的《孟子开讲》(中国青年出版社2023年8月版)时一看便知:前者为后者的深度和高度给出了非同寻常的铺垫意义。这样说,也从另一个视角为其自我炮制的冤情——“不温不火”作了旁注:比起后者即将到来的畅销,前者需要小火慢煮,细细品味,即使是“圣哲”也要经得起这一常销而非畅销之新常态的“寂寞”。
讲来讲去,读来读去,还是老鲍铸造的这一杀手锏最为拿手,最为烧脑,也更让人闹心。原来,他一直在为传统社会中的理性寻找道德依据。这里,他在理性和道德之前平添了一个“前”字,也就是有他所谓的“前道德”。这一度让我想起意大利18世纪的历史哲学家维柯,正是起《新科学》中的“前智慧”(诗性智慧)为起反现代、反启蒙的创制(我更愿意将其视作另一种现代和启蒙)披荆斩棘、另辟蹊径并让后现代的学者们乐此不疲。
老鲍振振有词:
任何问题的终极性解决方法必须是简单而直接的。对于“前道德问题”的解决,宗教是这样,世俗的解决方案也必须是这样。孟子的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简单到只有四个字——人性本善。如果人们问牧师,我为什么要做好人?牧师回答,好人上天堂。如果人们问孟子,我为什么要做好人?孟子的回答,是:因为你是人。
原来,“前道德”就是解决为什么要做好事的理由。子路曾问道于先生“君子亦有穷乎”这样的大命题。这个问题其实对中外古今的各色人等都是一个严峻的心灵考问。当然,孔子的“君子固穷”的回答已经将题中应有之义说得无懈可击。但是当亚圣的“接着讲”击鼓传花般落在了“锦上”且必须“添花”的关口,也就有了鲍鹏山的口吐莲花:
在孟子看来,做好人没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因为我们是人,人的本性是善,所以只要是人就只能做好人,不做好人就不是人。就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人得人,人的本性是好的,所以正常的结果就只能是好人,如果不是好人,那便不再是人。
做好人没有理由,这就是“此岸”人文关怀,而宗教的好人死后可以上天堂的教义则给出了“彼岸”的终极牵挂。由此,我从“开讲”中读出了“开读”的理由。毕竟,这是老鲍文字给出的理由。
然而,在说出开读的理由后,对于老鲍的“前道德”我还是留有余地。道德作为人类特有的伦理关怀,既然有“前道德”,那就有“后道德”。显然,这是作者没有摆平或说“圆寂”的问题。在他认定孔孟老先生都给出答案或说正解的同时,我更想在前道德、道德、后道德之间做一次哪怕有蹩脚嫌疑的“添足”: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技术理性沧海桑田,但人性初心依旧。如果需要让“道德”在社会秩序的良性编排中相得益彰,那就必须有法治(文明)的紧随其后。“善小”与“恶小”从来都不是挂在唇齿上的说教。有道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虽不是王道,却是人类社会走在文明钢丝上的一条正道。否则,即使将那些口惠的文字吹得天花乱坠,也终将无济于事。
说到这里,我也不无担心,一贯伶牙俐齿的老鲍会不会冲我顿足:道德与法治截然两途,虽不是“此岸”与“彼岸”,终还有“此一时”和“彼一时”之辩。
(作者系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