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应当有两支笔
作者: 陈定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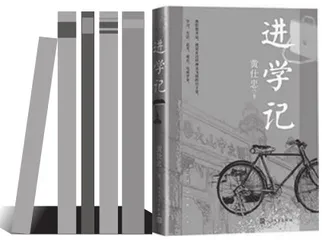
人生是一个进学的过程。黄仕忠这本《进学记》,记录了他从读书求学、访书问学到指导学生的一些人和事,从中也可以窥见一代学人的人生历程。责任编辑希望我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为此书作序,读着仕忠的文章,我也渐次打开记忆的闸门,就借此机会,说一些回忆和感受。
壹
我本科在西南师范大学(后与西南农业大学合并,更名为西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三年后,有感于专业基础不足,我放弃教职,报考研究生,在1987年秋天进入中山大学,师从李新魁教授学习汉语史,专业是汉语音韵学。
黄仕忠比我早一年到中大。他在杭州大学中文系读本科、硕士,毕业后留校教了一年书。虽然已在《文学遗产》《文献》《杭州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过论文,但自觉学识尚浅,若久滞一地,眼界便会受限,所以想再作深造。他的专业当时只有王季思先生招生,就考来了广州。
我们俩在本科同学里年纪偏小,都属于“听话”的那一拨,平时只想着怎么把书读好。同时在家里都排老幺,父母身体健康,上有哥姐,所以可凭兴趣做自己想做的事。不经意间,我们离家越来越远:我从蜀水(成都)到了巴山(重庆),又来到羊城;他从西施故里(诸暨)到了西子湖畔(杭州),再南下珠江水边,缘分让我们相逢于康乐园。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中大,学风甚好,导师认真教,学生勤勉学。研究生阶段的同学,至少是从本科直接读上来的,在工作与深造、做学问与走仕途之间摇摆,不免有“选择的焦虑”。我俩因为有过工作经历,目标早已明确,所以每天只是读书做笔记,拟题写文章,听导师讲授指点,与同学交流心得,专注学业,岁月静好。
我俩的专业,一个是语言,一个是文学,就像巴山蜀水与会稽山阴,似乎相隔甚远,实际上又很相近,因为都是做古代典籍的相关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也是我的研究材料,二者互为表里。语言学是一门传统而现代的学科,强调实事求是,力求得出“科学”的结论;文学则属于古老而前卫的领域,需要张开想象的翅膀,面对复杂的人性,鲜有定论。我们很少就对方的研究本身作讨论,只是分享各自对学术的理解和导师的趣事,印证老师们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又或是交换师长的相互看法,倒也蛮有意思。
黄仕忠于1989年夏天毕业,留校在中大古文献所任职。次年夏天我毕业时,未能留校。当时有去行政机关和出版社等几个选项,我去了花城出版社,以为在这样的机构,或许有继续做学问的机会。我先在古典文学编辑室,两年半后转到《随笔》编辑部,再一年半后,因偶然的机缘转向图书批销,从此断了做学问的念想。
贰
1990年11月,我和黄仕忠在广州结婚。既无婚纱照,也未办婚礼,把碗盏瓢盆合在一起,就是成家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全民经商热潮兴起的时候,“学问无用”之说渐起。不过这些好像和我们没关系,我俩从来不曾有过经商下海的念头,也不觉得自己是做生意的料。虽然收入不多,但两个人挣,两个人花,也没有太大压力。编辑工作安定,只要认真细心便好,不像做学问那么“烧脑”,收入比在大学当老师还高些,其实很适合我。
黄仕忠在古文献所,不用坐班,不用上课,每天编校古籍,撰写论文,也是悠然自得。他认为自己平生喜欢的,就是读书做学问,如今不但每天有书可读,而且每月还有工资可领,这已经很好了;至于学问有用或无用,在未做成之前,是没资格置评的,何况在大学里,总归还是要讲学问的。所以他不仅安之若素,还觉得自己的进学经历是在杭州和广州,学术的中心则在北京,应当去亲历体会一番,才算完整。
那一年,教育部开放了人文学科的博士后流动站,黄仕忠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北大袁行霈先生。袁先生咨询后,遗憾地告知,只有应届毕业的博士才有资格,那时黄仕忠博士毕业已经三年,职称是副教授。但他这个人,一旦认定了目标,便是非办成不可。再咨询有关部门,得知可以申请做访问学者,于是在1993年秋到1994年夏,他赴北大跟随吴组缃先生访问学习了一年。正是在这一年,我的事业也发生了转折。
1993年10月,诗人顾城去世。我大学低一级的学妹兼好友,是一位新诗爱好者,她从海外带回许多关于此事的纵深报道。我们合作编成一本书,题为《朦胧诗人顾城之死》,交由花城出版社出版,希望赶在11月首届“南国书香节”上发行。但以当时社里的出版流程,不可能在一个月内赶出来,社长建议我走“非常规”流程,由我们具体操办此书的编辑校对和印刷发行,才赶上了时间。这本书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借此机缘,我们合作注册了一个公司。
半年多后,1994年6月18日,因偶然的机缘,我在广州市图书批发市场租下了一个位置不错的档口。只是刚签约,我就得去编新一期的《随笔》。五天后,仕忠结束在北大的访学回到广州,才知道这件事。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够两天的铺租,但他二话没说,第二天就去打扫铺面,粉刷墙壁,搬书开张,成了我的第一位“员工”。我则在编完稿后,设法向亲戚朋友借了一笔钱,交上了“两按一租”铺面费用。在我去档口时,对面的老板娘对我说:“你家那个戴眼镜的马仔很不错。”只是他才帮了不到十天,就因急性阑尾炎住了院,“牺牲”掉了他的阑尾。不过这已让我赢得时间窗口,得以安排好有关事宜,从此正式进入图书批发行业。
但是既要组稿、编稿,完成出版社的任内工作,又要管理一家新开张的公司,这个公司每年还要向出版社交管理费,我实在忙不过来。也想过让店面员工承包经营,但他们不敢承担经营责任。而这个时候,公司已经产生债权债务,我也不能一走了之。于是从1996年元月一日开始,我正式办了当时颇为流行的“留职停薪”手续,专心经营公司,并在当年秋天,开办了第一间零售书店——学而优书店。
回想起来,他说要去北大一年,我一点也没觉得诧异,就让他去了;我签下这个档口,他说签都签了,那就做吧。他后来才说,其实不无担心,只是觉得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机会,成与不成,试过才知道;哪怕亏了,只要及时收手,大不了苦上两年,总能还清的。我的很多重要决定,大多是源自我的直觉及偶然的机缘,他通常会提出意见或建议,却从来不曾反对。——事实上,对他的选择,我也是同样支持的。
叁
留校任职的前十五年,仕忠的工作较为清闲。我曾与他讨论过,是否可以像有些老师那样兼着炒个股之类,他笑而不接。其实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也没想过“炒更”(打短工,兼职),更不要说炒股了。按他的说法,要保持一份静气已是不易,一旦沾染外面的气息,再想静心做学问,就难了(正如我一样)。
另一方面,他的兴趣很广,并不会一头钻进故纸堆里就不出来。他的博士论文做“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上溯到《诗经》时代,下延至现当代文学,结束于1988年谌容的小说《懒得离婚》。他不仅着眼于文学本身,也关注当代社会中的婚变事件,且有感于大学生和返城知青的婚恋所遭受的舆论压力,展开文学社会学的研讨,对妇女解放、婚姻道德等现实问题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以传统学术为基石而又十分关注当下,或许正是这代学人的特色吧。
1998年,他应邀为江苏文艺出版社编选了一本《老中大的故事》,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发掘诸多鲜为人知的文献,进而对现代高等教育的变迁和院系调整等事件有了新的感悟。他曾考虑过将来有机会要做一做这个题目。
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热”中,他从区域文化的角度,观察广东的改革开放,解释广东“先行一步”背后的文化因素,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讨论广东人的“文化品格”。这组文章以散文的笔触、独特的视角、严密的逻辑和简洁的文字,受到了读者的肯定。但当朋友们鼓励他趁势而为,往风头正劲的文化散文一路发展时,他却又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
对我办书店这事,他也很感兴趣,认真分析了学而优书店得以快速成长并走向成功的原因,饶有兴味地从中体悟市场经济及其包含的“物竞天择”的含义,考察“二渠道”这条“鲶鱼”所起的作用。他也喜欢听我讲书业界朋友的故事,他说,将来有机会时要写一下中国出版业的故事。
在我的图书批发门市刚开张的那段时间,我心里没底,问他到底是赚还是亏呢?他盘算了一下“流水”,说应该还是有得赚的。我说那就可以了。之后我的业务快速发展,他却又从旁观角度,认真地做着“学术探讨”,认为我在普遍缺少诚信的社会背景下,做事踏实,讲究信用,因而赢得了同行的信任,获得许多资源和合作机会;读书、教书到编书的经历,又使我对好书有着某种直觉,出手较稳较准;虽然在商言商,但图书毕竟不同于一般商品,发行图书其实也是在传播文化,我们更多想的是怎么把事情做到最好,就像做学问那么认真,而不是只计算着怎么才能赚最多的钱,无为而无不为,这是学而优书店能够赢得读者青睐、获得某种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
这些分析让我很受用,不但因为这是比较真实的我,也因为这让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知。像我这种算术很差的文科生,原本就不太会“计算”,把事情做好就行,这既是我的出发点,也是我的归宿。我自认为对于书业有着一定的使命感,只要不亏或者少亏,就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已经很好了呢。
不仅如此,他还由此引申出文艺与娱乐产业的关系,觉得可以把市场竞争、市场准入、客户分级等概念运用到戏曲研究之中,来解读演剧相关的活动。有人把底层演剧与文人剧作对立起来,以为是文人“侵占”了艺人的舞台,他却从“把蛋糕做大”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这让他与单纯待在象牙塔里的学者,有了一丝丝不同。
他自认是在做严肃而高尚的学问,但他并不认为在象牙塔里做学问就一定是高尚的。学问之事,犹如一枚钻石胸针,在兵荒马乱、食不果腹的时候,便是一块无用的石头;在经济发达、社会安宁之时,它的价值才会凸显。既然如此,我们有什么理由轻视经商做实业、为政府缴纳税收、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家呢?
他又说,我们的书价太便宜了,因为大家只计算纸张及印刷的成本,从来不觉得写书人的“知识”有价值,才会觉得书价太贵。问题是说书太贵的,还都是读书做学问的人,这其实是让自己的“精神生产”贬了值呢。
我赶紧制止他:这些在自己家里说说就好了,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讲,你会被口水淹没的,何况我们家本来就是开书店的。
肆
黄仕忠其实是一个十分固执的人,连导师黄天骥先生也是这般觉得。因为他总喜欢对别人的话说“不不不”,而要说服他,则是难上加难。他在北大任教的同乡老友说:黄仕忠总要说得他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不和他争了。
对这话我深有感触:仕忠喜欢寻根究底,书呆子脾气上来,每句话、每个字,甚至一个语气,都要如他的意,才肯放过。有时候兴冲冲告诉他一个想法,希望得到他的肯定,结果他往往来一个“其实你还可以如何如何”,当头一瓢冷水,搞得你兴致全无。
我有时说他刚愎自用,而且从来不肯认错。他却并不生气,辩解说,一个学者,需要有一点“刚愎自用”,才能坚守本心,如若不然,他便不是他了。世间滔滔皆如是,也不妨有那一小撮人并不如此。所以他甘居“另类”,因为他想的与做的,与别人很不相同。他自我解嘲说:这是诸暨人性格所致,硬碰硬,不屑取巧,无意捷径。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硕士生导师徐朔方先生就是这样,真可谓有其师必有其徒,所以我也只好随他了。
他认为自己很幸运,上大学时还不满18岁,但同时又经历了在乡村底层的艰难岁月,早早就懂事了。他能考上大学,主要靠自学。在大学里,也能自己安排读书。后来读研究生,师承徐朔方、王季思先生,不仅受到系统的学术训练,而且接续了民国学风,从中感悟到学术与人生的关联。因为读书还算认真,基础也还扎实,平时总想着“另辟蹊径”,所以他很早就在专业上有自己的看法。他半真半假地说,岭南属“化外之地”,学术竞争强度没江浙高,生存不难;何况已辛苦太太开书店赚钱了,既然如此,也就无须在意世俗的眼光和管理方的要求,埋头做自己认定的学问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