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口沉银考古手记》序言
作者: 唐际根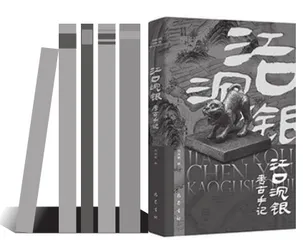
宝藏传说,史不乏载,民间更多。
四川便流传着一个著名宝藏传说:江口沉银。
据说张献忠当年撤出成都时,携带了一批财宝。行至今眉山市一带,张献忠突遭明军将领杨展伏击。激战之后,献忠大败,船队与船上所载珍宝,俱沉入锦江与武阳江相交处。锦江与武阳江,其实是岷江分流而成,二者合流之后,再奔东南。相合之处,又称“江口”。
张献忠沉银时曾封锁消息,但终究纸包不住火。藏宝消息不胫而走,并且越传越神、越传越乱,藏宝之处也由江口滋生出青城山、峨眉山、成都、新津等地点。当年张献忠江口沉银有亲眼所见者,一位叫欧阳直的人甚至描述了细节:献忠沉宝时曾将金银装入“木鞘”,然后沉江。“木鞘”之说,后来竟得证实。据《蜀难叙略》记载:杨展击溃张献忠后,获悉沉银之事,令人“以长枪群探于江中,遇木鞘则钉而出之”;从顺治到乾隆年间,不断有人在江口打捞出金银;道光、咸丰年间,二帝曾先后派官员在江口寻找张献忠的“沉银”。“木鞘”也不止一次被发现。因此张献忠江口沉银,既是秘密,又非秘密。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献忠沉银一事逐渐被淡忘,到江中打捞宝藏的行为也逐渐绝迹。沉银一事,似乎被“封存”了起来。
2005年,沉银之事再起波澜。是年,彭山县(今彭山区)政府为解决当地居民饮水问题,在岷江河道内铺设管道。施工过程中挖出一段木鞘,内有五十两的银锭7枚。银锭刻有湘潭、京山等地名,经鉴定其时代系明代。岷江出水金银的消息,再度招致少数人以身犯险。2014至2016年间,眉山警方从案犯手中追缴金锭、银锭、金册、银册、“西王赏功”币以及各种金银首饰若干。
岷江江口持续发现金银的事实,让文物考古界决定组织力量正式发掘。刘志岩的这部《江口沉银考古手记》,讲述的便是江口考古过程。
考古发掘与盗掘文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是挖宝,而前者是科研。许多学者认为:过往的历史,只有通过正式考古发掘获得地下文物证实,才能转化为“信史”。一些执拗的学者为了“表白”自己学术严谨,常常会瞪大眼睛给考古结论找碴儿。对于张献忠沉银或藏宝这类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问题必“严密监视”。即使江口一带历年都能打捞出明代金银,即使出水过“西王赏功”币和“大西大顺二年”金册,但只要不经过正式考古发掘,就无法证明张献忠曾经藏宝于此。因此江口发掘的首要意义,便在于对张献忠当年是否在江口沉银给出结论。这就决定了发掘不能有丝毫差池,发掘主持人须谨慎行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最终决定由志岩先生主持江口发掘。尽管他自己说是因为此前他曾在彭山“考过古”。实际情况是当时需要一位有水准、有能力的学者,方能担当此任。
施加在发掘主持人身上的压力,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受到了。
中国考古学家的陆地发掘,水准早已领先世界。在殷墟,发掘技师凭借一把小铲、几根钢条,便能将朽蚀在黄土中的商代木质马车清理“剥离”出来。沉船打捞及水下发掘也有先例。我曾应邀参加广东“南海一号”沉船的发掘方案论证会,会上9位专家经反复讨论,最终拿出的方案是将“南海一号”沉船拖至海岸,排水之后再采用陆地作业的方法发掘。然而江口沉银的发掘既非陆地发掘,又不同于“南海一号”,毕竟沉在水下的明代金银散布范围远大于一艘沉船。
刘志岩决定召开论证会,以期讨论出合适的发掘方案。参加首次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论证会的均是国内重量级学者,既有经验丰富的田野考古学家,也有专门从事金银器研究的学者,最终大家选定了“围堰式发掘”。
所谓“围堰式发掘”,是先在水中修建围堰,然后把围堰内的水排干,将水下环境转变为陆地环境,再按陆地方法发掘。“围堰式发掘”是在潜水考古和整体打捞都不现实的情况下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如果当时我参加论证会,相信也会给“围堰式发掘”投一票。
选定“围堰式发掘”后,刘志岩和他的队友们轻松了不少。接下来是选点,即框定“围堰”的具体范围,这是考古发掘布设“探方”之前的步骤。围堰并排水之后,考古工作“转换”成了陆地发掘,一切变得相对简单。张献忠江口沉银的神秘面纱也被逐渐揭开。2017年2月5日,一枚刻有“银五十两,匠张道”的银锭发掘出水。到2017年4月,考古队在大约10000平方米的发掘范围内,清理出各类文物30000余件。
科学发掘,实证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随后便是荣誉加身。2018年4月,江口沉银遗址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8年6月,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江口沉银——四川彭山江口古战场遗址考古成果展》。国家博物馆从30000余件文物中精选了500件展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享受到了最新的考古成果。我有幸参加了开幕式,清晰记得当时的盛况。
发掘是考古工作的第一阶段,主要解决发掘现场的基本问题,如文物出水前的位置何在?怎么让文物出水?文物当年如何沉底?沉底之后的数百年中发生了什么变化?除了这些,刘志岩和他的团队还要解决更多深层学术问题,例如出水文物有哪些类别?银锭、银钗、金册纯度如何?功能如何?张献忠当年通过什么手段,又从何处获得各种金银制品?明代末年的“大西”辖区内一枚银锭购买力几何?等等。
深层学术问题的回答需要时间,最终给出答案可能要等发掘结束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但考古队显然已经着手研究这些问题。他们通过测绘地图标注出水文物的位置;从水文动力学和物理学角度分析文物的沉底位置与外观变迁;利用科技手段检测文物成分和观察文物伤情。这些工作都属于为回答上述问题做准备。而人文社科角度的研究更是伴随发掘始终。仅仅一枚“蜀世子宝”印,便揭开了张献忠劫掠蜀王府、霸占明代蜀王之物的史实。倘若有更充裕的写作时间,我想志岩先生会列举部分成分检测和文物伤情探测结果以飨读者。
考古学有三大基本功能:证史、补史、构史。江口沉银遗址经过6期考古发掘,出水文物总计70000余件。如此丰富的文物,最终会勾画出一幅怎样的历史画卷呢?作者的这部著作,算是反映整个江口考古工作的序曲,我们期待第二部、第三部江口考古成果陆续出版。
这部书最大的“看点”是选题。毕竟江口沉银的考古背景是有着“屠蜀”恶名的“张献忠绝唱”,是社会广泛关注的历史事件。依托这样的背景写作,其实是巨大的心理挑战和学术挑战。我猜想作者写作此书的心境既是急促的,又是从容的。从容表现在书的内容与结构。全书以时间为序,叙述发掘缘起、发掘过程、管理过程和科研过程,又不时插入各种考古常识,普及考古类别、勘探技术、发掘方法、考古与盗墓的区别等,还插入国内各大学考古专业的设置,甚至不惜笔墨介绍发掘过程中的志愿者招募、田野工作现场的婚礼以及疫情期间大家的工作与生活。这样的编排,使得读者在围观“围堰式发掘”、享受明末重大历史事件的特殊魅力的同时,还能顺便了解考古,称得上独树一帜。
2019年,我曾在江口考古现场听作者介绍发掘过程。这次收到《江口沉银考古手记》一书,一口气读完,仿佛又回到美丽的岷江,并遥想起明代末年的历史烽火。遂写下上述文字,为江口发掘这次重大考古活动有了一部记述全程的重要著作道贺。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暨高等研究院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