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重庆学生的“下乡”活动
作者: 谭锋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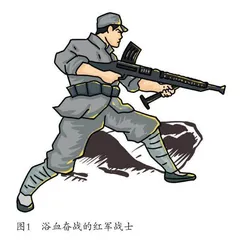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政治生态环境复杂,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与争取群众活动。重庆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学校的支持下,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亡活动,这对唤醒农民的民族意识、引导农民支援抗战前线具有重要意义,也促进了党组织在重庆农村地区的恢复和发展,更对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工作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激励全体人民联合抗日。随着沿海以及北下的大学汇聚重庆,学生们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宣传抗日救亡活动,从城市深入农村地区。
重庆学生下乡的环境条件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既是国民党的控制中心,又是中国共产党开展秘密工作的地区。在这种条件下,重庆学生面临着多重考验,承担着重要任务。
第一,重庆的政治生态环境。重庆作为战时陪都,其政治环境伴随抗战形势、两党关系的变化而表现出复杂的特征。1939年,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策略重心逐渐由对外抗战转向内部争斗,其在抗日立场上也由积极抗战转变为消极应对。此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活动更加艰难,学联解散,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停止工作,而是通过秘密的方式和“合法化”组织开展工作。学生活动也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由轰轰烈烈变为秘密进行,相较于城市的黑暗环境,农村的广袤空间为学生活动提供了更多可能。
第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引领。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学生下乡并不是偶然,而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对于学生的重要性、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途径不断认识的结果。
青年学生是革命斗争浪潮中最先觉醒且至关重要的群体。这样的热血力量如何与农村结合?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中强调:“要想把现代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非要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认为知识青年应速去农村,只有农村基层有了改变,社会才能真正进步。此后,《中国青年》针对“到民间去”这一思想有了更多具体指导。全面抗日战争时期,10多所大学迁入重庆,为沉闷的西部地区注入了新血液。《新华日报》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研究社会各阶层,为乡村服务。众多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肩负起唤醒、团结各阶级共同抗日救亡的重任。
第三,重庆学生下乡的条件。学生到农村地区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不仅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学生自身的知识与能力,还需要有交通、经济等多方面的保障。
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有悠久的革命传统。五四运动时期,多所学校联合成立川东学生救国团,学生走上街头宣传,带头抵制日货。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同反革命势力斗争,在土地革命时期与军阀势力顽强斗争、配合中国红军战斗,这种革命的传统在重庆学生中保留了下来。1936年6月重庆救国会作为秘密组织成立,重庆进步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展开工作。
内迁的报刊、书店为学生学习先进文化提供了途径。重庆集结了全国主要的日报,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书店遍布学校及周围市镇。在城市中的学生有充足的资源,了解先进文化、看清国际局势,各区县则急需文化的普及和开发。
学校支持学生深入农村,这是重庆学生下乡得以成功的现实基础。重庆大学在校刊中强调,“到乡村去”是中国文化界的一致呼声,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重庆大学学生在学校的支持下,开展乡村动员工作。同时,学校也积极给予物质支持,重庆大学学生后援团的经费主要来自学校津贴、重大救国会存款以及他人捐助和自筹。
重庆学生下乡的主要行动
正如张宗植所说,“中国西南部的地理特征,便是纵横列错的重山叠嶂,在这些高山深谷之中忍耐劳苦生活的人民,大都没有沾染现代文化的惠泽。”重庆学生深入周围农村地区,用多种多样、通俗易懂的形式宣传抗日救亡,开办识字班进行教育活动,吸收进步党员、巩固党组织建设。
第一,抗日救亡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时代主题,重庆学生下乡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农民明晰现状,唤醒农民的民族意识,动员农民积极参与抗战。兰毓钟在回忆中提到1938年区委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党组织,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先进的学生们在校期间在学校周边宣传,放假后或组织同乡同学回乡工作,或以团队形式深入农村。
乡村消息不通,农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对于时局的了解不多。因此,壁报成为重要的宣传工具,重庆大学、复旦大学等众多团体都有出版壁报的组织,其内容针对农村的特点,主要以色彩鲜艳、醒目的图画为主,辅以简短有力的文字来突出主题。棉花街壁报乡村号第五期以巨大的飞机残骸为中心,配文“送死的寇机”,通过简单的图文向广大乡村民众传达当年重庆击落日机的消息,以增强其抗战的信心。复旦大学的《旦复旦》刊载国内外时事、社会评论以及抗战图画,对黄檞镇的民众产生积极影响。当时的黑白木刻就将广大农村群众围绕壁报谈论、学习的画面展现出来,反映了农民对于壁报的接受程度高。除了壁报以外,简短明晰的标语也是学生们在乡村地区宣传时事的重要工具。例如,“主和即汉奸”“实行对日绝交”就是在汪精卫等人主张言和,实行投降主义时,学生群体制作的标语,他们在城市聚众反对,在乡村地区揭露“主和”的真面目,引导农民聚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壁报、标语存在于乡村群众生存的客观环境中,乡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着爱国主义教育,封闭的乡村不再沉寂。
相较于潜移默化的隐形方式,易于流传的歌曲与富有感染力的剧目则能直接引发乡村群众共鸣,动员其参与抗战。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大中小学生从上至下逐步从城市深入农村,众多宣传小分队为乡村群众带去精彩感人的表演。例如,简单浅显的歌曲《打倒日本》,“打倒日本,除汉奸,除汉奸;大家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救中国,救中国。”这类歌曲通俗易学,曲调激昂澎湃。在演出时,儿童跟学最多,成人则内敛害羞,但是唱声一起全场肃静,唱声一停,掌声雷动。《救亡进行曲》《码头工人之歌》等都是当时全国传唱的歌曲,带有强烈的抗日情感,激发了乡村群众的抗日情绪,鼓励其贡献自身力量,支援抗日战争。
话剧演出模拟真实场景是学生在乡村最有效的宣传方式。《放下你的鞭子》描述了九一八事变后,一对东北父女流离失所以卖唱为生的故事,以小人物的命运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激发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反抗。巴县中学宣传队在冷水场、马王乡和石桥铺上演《热血》《民族公敌》等剧目时,观众冒雨观看且情绪高涨,在看到日军残暴的场景时,观众必发出“打呀!打倒日本人!”的呼声。另外,在全面抗日战争后期,国内形势发生变化,逐步由反侵略转变为争取民主,育才中学学生团队演出了更贴近重庆人民生活的方言剧目《啷格办》《不太平》,《啷格办》旨在反映现实,揭露国民党军队弃土逃跑的丑恶。
重庆学生在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紧紧追随中国共产党的步伐,在国统区的广大农村地区,通过隐形、显性的方式对乡村群众进行爱国教育,鼓励他们参与抗战,并取得重要成就:一方面,乡村群众的思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另一方面,乡村群众各尽所能积极捐款支援前线。
第二,加强农村文化教育。全面抗日战争时期,乡村地区的教育资源十分薄弱,乡村群众接受教育的机会微乎其微。学生在假期深入农村,不仅分析局势、宣传抗日,也积极教乡村群众识字,有利于提升其思想觉悟。
众多学校迁入重庆,为重庆注入了青年力量,学生下乡宣传也为乡村地区带去了教育资源。学生群体秉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观念,到乡村开办识字班、文化补习学校。北碚文星场抗日宣传队推广平民识字教育,由于农民白天要忙碌于农活,因此识字教育只能在晚上进行。傅杰回忆:“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自己煮饭,白天做准备,晚上提一块小黑板,写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找个院坝就开始教学。”在此过程中,学生不断深入农民,了解农民苦难,在帮助农民时也坚定了自己抗战的决心与信心。复旦大学迁入北碚后,进步师生紧紧围绕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积极响应党的政策。该校的地下党员沈钧等深入东阳乡、白庙乡办文化补习夜校,开展以抗日救亡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偏僻的乡村为国民党统治者所漠视,但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中国共产党教育农民的经验中有许多“合法化”组织形式,对发展乡村教育有重要意义。识字班与国民党合法机构相结合,如大公职校胡琼仙等20多名党员在假期与铜梁县民众教育馆合办识字班,教识字,宣传救亡道理;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基督教女青年会乡村服务队,在潼南办识字班、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另外,中国共产党在重庆也成立了许多合法机构。陶行知成立的育才中学,由中共中央南方局直接领导,其学生多来自沦陷区,有强烈的革命意愿。陶行知先生主张向社会学习,育才中学重视社会调查,加强学校与群众的联系。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许多农村的青壮年都是文盲,其家庭经济困难,交不起学费,上不起学。育才中学在农村附近办起了识字班,教学内容包括识字、政治,教学成果非常可观,许多人学会了记账、写信,在政治觉悟上也有明显提升,他们认识到穷人不是天生的,是因为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只有跟着共产党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才能得到解放。
学校师生在乡村地区开展短期或长期的文化教育,对农民具有重要的启蒙意义,一方面使农民掌握了实用的技能,另一方面也激发了农民的爱国热情,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基础。
第三,巩固党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下乡,在实践中促进党员、党组织自身的完善,并在与广大乡村群众的接触中吸纳进步分子,进一步充实了党组织。
学生提升了抗战宣传的实践能力,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前期准备工作到完成,学生们对共产党的认识逐步深化。魏亦臣呼吁学生:“我们应该积极去做救亡工作,我们不怕季节的热火,我们怕,人为的太阳光,因为它是永久的燃烧着,而今的朝鲜就是这样。”经过大家共同讨论,彼此对抗战局势、抗战意义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学生深入乡村,对农民、乡村有进一步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重视农村的方针政策有更强的认同感。同时,在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的过程中,学生对于歌曲、话剧等宣传内容的认知也不断深化,坚定了抗日救亡的决心。另外,假期中的党员培训也是提升学生党员党性的重要途径。他们在下乡活动中发现先进分子、培养先进分子,学习《大众哲学》《中共党史》以及党的知识、纪律,发展了一批党员。
培养进步农民,发展农运骨干。经过思想启蒙的农民不仅在思想上认同中国共产党,更通过实际行动向党靠近。乡村中的青年农民参加夜校学习、唱抗日歌曲,在自身思想逐步解放的基础上,持续将党的思想传播到乡村的各个角落。北碚数十个农村少年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赶赴北碚多地进行宣传。农村党员的培养为党组织在农村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为解放战争时期在重庆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了群众基础。
学生下乡活动,从思想上、能力上锻炼了党员,培养了一批新的学生、农民党员,巩固了农村地区党组织,也为解放战争时期鼓励知识青年下乡提供了经验。
重庆学生下乡的当代价值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学生深入乡村地区,宣传抗日救亡、将知识送到乡村、发展农村先进分子,唤醒了民众的抗战热情,有效地支援了抗战。总结重庆学生下乡的历史经验,能够为新时代的青年学生工作提供借鉴。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青年学生的力量,保证学生工作方向的正确性。在重庆学生下乡活动中,中国共产党对宣传内容的把控,对党员的培训都是方向性的引导。在新时代,我们要培养担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必须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的灯塔作用,为新时代学生驱散迷雾,指引方向。
第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学生是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承上启下的群体,他们既受到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影响,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不断革新自我,在斗争中创新。在重庆学生下乡活动中,学生了解乡村、调查乡村,根据乡村实际情况改变宣传方式,根据时事变化,创作不同的歌曲。育才中学学生创编了许多抗战歌曲,深受群众欢迎。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注入新活力。
第三,注重知识到乡的方式。重庆学生下乡活动,分析了战争局势、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将知识送到乡村。在新时代,农村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中心,改变农村发展相对落后的现状,需要将知识送到乡村。一方面,根据当地农村所需,组织知识分子开展有针对性、趣味性的讲解;另一方面,号召学生毕业后扎根农村,为农村基层建设贡献力量。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下乡活动,对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学生下乡打破了乡村的沉寂,带去了新思想、新力量。学生通过简单直白的表演,激发了农民对前线战士的同情和敬佩,增强了其对侵略者的憎恶之情,充实了抗战力量;同时促进了乡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强了基层政权的建设。重庆学生下乡的历史经验对当今的学生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四川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