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化生育:当代柏林生育观冲突何以产生
作者: 王腾远
莉妮从椅子上站起来,展开双臂,踮起脚尖,以一种形象的姿态展示着她在不用带孩子的情况下所能获得的自由与空间,然后她说,“不用带孩子的时候,在公共场所很容易找到归属感。没人会以一种严厉和不赞成的方式盯着你。”莉妮是柏林的一位单亲妈妈,也是文化人类学家梅伽娜·乔希(Meghana Joshi)的众多受访者之一。她声情并茂地向乔希倾吐着在柏林所感受到的“儿童不友好”。然而,在对待儿童与生育的态度上,柏林这座城市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吊诡。

“有孩子”和“没孩子”群体的空间争夺
刚到柏林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乔希就注意到一家咖啡店的门上,除了禁止吸烟的标识,还贴着另一张大大的警示牌——禁止婴儿车进入。店门口横置一大块长方形石头作为路障。而另一家以儿童友好著称的咖啡馆,则创新性地将带孩子的成人与不带孩子的成人在物理空间上分隔开来。前厅的主要空间让给带孩子的家庭,而柜台后面的两个小房间隔离出来给其他顾客。这两个咖啡馆在柏林并非特例,截然不同的经营风格,成了当代柏林分裂的生育观及其对峙状态的一个缩影。除了咖啡馆,这种对峙与吊诡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0年后,柏林人的生育观成为乔希持续关注的对象,并于2023年出版了她的著作《孩童遍地——当代柏林的显化生育与无子现象》(Children are Everywhere: Conspicuous Reproduction and Childlessness in Reunified Berlin)。这是一部研究当代柏林“显化生育”话语,以及“转折一代”生育观念的文化人类学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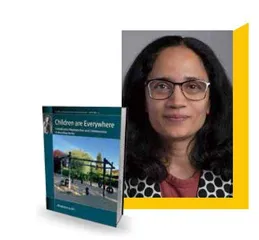
在本书中,作者将“显化生育”定义为一种社会话语和实践。这一话语旨在使“生育”呈现在公众的意识中。这种“显化”集中体现在公共空间中对婴儿车、儿童及相关设施的关注上。在作者看来,“显化生育”力求突出生育的价值,并通过以孩子为中心的物品和观念进行展示,塑造“强势”的母亲角色和“积极”的父亲角色。在国家层面,“显化生育”意味着政府在社会舆论和实际政策中将鼓励生育放在显著的位置,并努力创造“儿童友好”型社会。作者认为,物理和象征意义上的“显化”标志着当代德国生育制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偏向异性恋核心家庭,并将拒绝生育的人群边缘化。这一制度上的转变引起了德国社会中“有孩子”和“没孩子”群体的对峙。受到排挤与边缘化的无子群体,呈现出一种对儿童的“不友好”,包括禁止婴儿车进入公共空间、在公共场所对家长发出愤怒的嘘声或大声指责他们对孩子缺乏管教,针对游乐场或托儿所的噪音提起法律诉讼,通过舆论制造刻板印象,等等。
在作者看来,“儿童不友好”实际上是对一个日益“儿童友好”的德国所产生的个人和社会层面的不满的外化。种种不满与对峙在柏林“转折一代”中体现得尤其明显。转折一代是指在1989年前后成年的一代德国人。之所以将转折一代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在作者看来,当今柏林人对待儿童的态度,可以追溯至冷战时期东、西德迥异的社会语境与家庭政策。
本书第一章关注了两个群体对于城市空间的“争夺”。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自20世纪90年代初,西德人和其他欧洲地区的人开始向柏林移民。新移民逐渐使得大量的柏林社区中产化(gentrification),极大地改变了柏林的城市景观。在乔希的访谈对象中,那些居住在米特区(Mitte)和普伦茨劳贝格区(Prenzlauer Berg)等社区的单身男女发现,在充斥着儿童咖啡馆、游乐场和婴儿车的社区中,酒吧、书店和画廊正在消失,几乎没有空间让他们继续那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同时,随着租金日益高涨,许多长期居住在柏林的人只得离开。在访谈时,作者敏锐地捕捉到,这些不婚不育者的抱怨中,通常流露着对柏林昔日的伤感与怀旧。曾经的柏林以对边缘人群的包容而闻名。学生、失业者、艺术家、朋克、社会活动家等都在这座城市找到了安身之处。而如今的柏林正快速将这些曾经赋予城市波希米亚风格的群体拒之门外。如今,在鼓励多生多育的政策与话语下,他们的生活空间正在被不断挤压。作者以“光脚游乐场”的建设以及《反噪音法规》的修订作为这一趋势的具体呈现。
格尔利策公园是柏林较小的公园之一,有着开阔的草坪。在这里,经常能看到人们读书、聊天、烧烤、晒太阳、骑自行车、玩飞盘或踢足球。当作者沿着公园的边缘散步时,也不断有青年人向她兜售毒品。尽管公园中散布着大大小小的儿童游乐场,但利用率并不高。一位40岁的妈妈告诉乔希,“公园正变得越来越糟,狗到处乱跑,没有拴绳子,到处都是尿骚味,垃圾遍地,还有空酒瓶、碎玻璃。这里成了游客、失业者、酒贩和毒贩的天堂。所以游乐场里根本没孩子玩。”为了满足孩子与家庭的需求,地区办公室开启了“光脚游乐场”计划。他们试图扩大儿童游乐场的面积,并用围栏进行隔离,禁止遛狗、烧烤和饮酒。尽管遭到经常来公园的人和附近居民的抗议,地区办公室还是修建了光脚游乐场,以满足孩子和家长的需求。德国政府建立儿童友好型社会的决心同样体现在噪音法规的修订上。2011年,柏林成为德国首个修订《噪声法规》的州。法规规定在游乐场、日托中心及其他类似儿童活动场所,孩子们玩耍、嬉笑和进行体育活动时产生的噪声,不能等同于工业噪声。这一修订意味着,公民不能再以儿童玩耍噪声过大、有害健康和安宁为由,要求日托中心搬家,也不能阻止在居民区附近修建游乐场。

冷战遗留的家庭政策
当代德国对于儿童态度的差异也和冷战时期东、西德的家庭政策与性别角色有关。第二章探讨了显化生育中的女性议题及其历史根源。“施瓦本”(SWABIA)是中世纪时期一个颇具民族特色的公国,位于如今德国西南部。在当地,施瓦本人被赋予了诸如整洁、勤奋、节俭、富裕并且重视家庭等特征。“施瓦本妈妈”(Swabian Mother)这一形象除了以上民族特征,通常被人提起的是对孩子过分的投入与溺爱,以及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已婚”“三十多岁”“丈夫养家,不用工作”“有一到两个孩子”“在市中心买了房子”“互相攀比昂贵的婴儿车”……然而,乔希发现,这些刻板印象忽略了冷战时期东、西德迥异的制度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以及对当代德国儿童话题的影响。
通过梳理历史文献,乔希发现,在冷战时期,东德和西德的家庭政策存在显著差异。社会主义的东德,更加支持女性平衡就业与育儿。当女性外出工作时,公共机构承担起育儿责任。在西德,国家从家庭和生育的私人领域中退出,既是为了与纳粹的遗产划清界限,也是为了与东德有所区别。在西德的模式中,人们期望男性养家糊口,女性成为主要的家庭照顾者。统一后,德国政府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开始“追赶”其他欧洲国家,制定出更“性别平等”的家庭政策,为女性提供生育和职业发展的机会,也让男性更多地直接参与育儿,诸如将男性的陪产假延长至6个月,陪产假期间可以领取67%的薪水。“施瓦本妈妈”的形象与理念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德家庭政策的遗产。在作者看来,这一历史因素在当代柏林人对待儿童的态度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作者梅伽娜·乔希本身的身份与视角构成了本书的一大亮点。作为印度裔学者,乔希调转了以往大都来自欧美学界对南亚的“人类学凝视”,首次以南亚学者的视角研究德国人口与生育问题。在深入柏林日常生活的同时,乔希发现她独特的身份不仅更容易让受访者敞开心扉,而且当她将南亚经验作为对比,时常让她有意外的发现与洞见。书中丰富且生动的民族志记录,结合生活史的分析阐释,为我们呈现了那些不易察觉的微观边界的形成,以及围绕生育问题而展开的失去、排斥与包容的复杂互动。
中产阶级化
又称“绅士化”,最早由英国社会学家露丝·格拉斯(Ruth Glass)于1964年提出。在社会学和人类学语境中,“中产阶级化”多指富裕家庭或投资涌入相对贫困的城市社区。这种情况由特定经济波动、历史事件或政策激励引发。这些“绅士”通常年轻且从事白领工作,迁移让他们更方便地到达工作地点,也能更轻松地享受城市的娱乐和设施。这通常会再次推高房价,从而进一步振兴该地区。然而,贫困居民可能因生活成本等增加而被迫搬走。同样,社区的景观也会随之重塑, 比如许多颇具特色的酒吧、商店可能会被更昂贵的高档精品店和餐厅所取代。
(责编:刘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