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号屠场》:外星人如何教人类反思战争?
作者: 杨殳小说《五号屠场》是否可以这么理解呢?比利是在目睹人类不可救药的愚蠢暴行之后,不得不以精神崩溃来逃避创伤,虚构出外星人绑架的故事并从他们那获得洞见,看清了人类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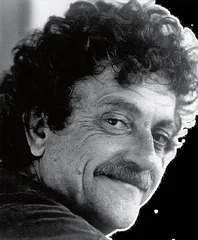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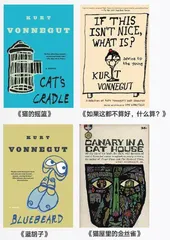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打仗片”,那种血脉偾张的感觉很上头。如今我依然对战争故事感兴趣,却多了一份警惕:如果战争故事唤起的只有掷地有声的激情,而缺少对战争的反思,就很值得怀疑。
战争意味着什么?《五号屠场》用不同寻常的故事给出了回答。
战争意味着什么?
本书开篇,作者讲了创作期间的一段经历。有天他带着手稿拜访老战友征求意见,却遭到战友妻子的白眼。她怒气冲冲地说:战争中你们还只是不懂事的娃娃!作者承认,战争中他们正处于“童年期的末端”。可这位妻子依然愤怒,认为他在小说中不会实话实说:“你会假装你们不是些娃娃,而是男子汉,让弗兰克·辛纳屈、约翰·韦恩或者其他一些魅力十足、好战的、有一把年纪的无耻之徒在电影中表现你们的故事。战争看上去无比美好,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战争。送去当炮灰的是些娃娃,就像楼上的娃娃们。”冯内古特当即举手发誓,故事里不会有约翰·韦恩们的用武之地。
《五号屠场》里没有一个男子汉,主要角色都刚成年。他们被丢进战场,就像毕业后被分配了一份工作。无论美国兵还是德国兵,怀里揣着的只有两种恐惧:既怕自己被杀死,也怕自己不得不杀人——他们“没有方向、没有敌我、没有意义,只有死活”。
该书的情节框架取自作者的经历:二战尾声,主人公比利像无数美国年轻人一样被送到欧洲战场,但他连军装都还没摸到,就被德军俘虏,送进了德累斯顿战俘营。很快,盟军开始了轰炸,比利和其他美军战俘及四名德军看守躲进了屠宰场的地下储藏库。当他们从地下爬出来,发现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废墟中,不见一个
活人。
比利在战后受到嘉奖,以战争英雄的身份开始新生活。后来他遭遇了空难,却再次成为幸存者。出院之后,他说起了一件不为人知的往事:我曾遭外星人绑架,被送到一个叫特拉法玛多的星球上,关进了那里的动物园。没人相信比利的故事。他却终其余生都执着于此,要把从外星人那学到的真理讲给人类。
若按传统现实主义或批判现实主义的写法,或许不得不强调战争如何残酷,把人逼成了疯子。但冯内古特觉得这样过于理性——会让恐怖的事“具有可阐释性”。战争中一个人的遭遇该如何阐释?他写了至少五千页又都撕掉,最终把故事讲成了碎片:“书不长,杂乱无章、胡言乱语”,因为“关于一场大屠杀没有什么顺乎理智的话可说。”
于是,《五号屠场》的终稿成了一部“后现代”经典,“元叙事”代表作。小说的叙述者犹如一名阴阳怪气的说书人坐在你面前,要给你讲讲比利的故事。他似乎不知从何说起,这儿讲一段,那儿说一段,时而打断故事点评一二。
在进入比利故事的第一句里,冯内古特先抛出了自己的科幻设定:“听我说:比利·皮尔格林从时间链上脱开了……他多次看见过自己的出生和死亡,任意造访了发生于两者之间的所有事件。”这句开场白好似惊堂木一响,打乱了惯常认知。接下来他以“杂乱无章”的讲述,让读者从现实逻辑和思维惯性中抽身而出。
在1976年《五号屠场》的重版序言中,冯内古特讲了一个故事:媒体请他谈论对战争暴行的看法,他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他人生最大的黑色幽默:“毋庸置疑,战争暴行颂扬的是无意义。我无言以答……德累斯顿轰炸耗资巨大,策划精心,但毫无意义,最终整个星球上仅一人从中获益。那就是我。我写了这本书,为自己挣到不少钱和名声,事情就是这样。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我从每个死人身上赚了两三美元。我做的算什么生意。”

科幻设定让我们进入了外星人的立场。据比利讲述,外星人绑架了他和一位女明星,关在外星动物园里展览,吃喝拉撒睡都要直播。这种处境中的他代表了全人类,对外星游客说:“我来的星球上,有史以来一直纠缠在疯狂地屠杀中……地球仔一定是宇宙的恐怖生物……把和平秘诀告诉我,让我带回地球,拯救我们所有人。”
外星游客说地球仔的问题真是愚蠢。因为特拉法玛多人有着不同的时空观念,可以同时看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他们掌握了非线性语言,可以从高于自身的层次审视自己。受到这种时间观念的影响,比利的认知发生了本质转变。他意识到每个现在都毫无原因,也不会成为任何未来的原因。就像我们所谓的平行时空,所有时刻并行存在,且永远存在。死去的永远死着,活着的永远活着——“事情就是这样”。
于是他对命运的理解不复从前。他掌握了人生诀窍:在时间中跳跃着度过,不理会痛苦的时光,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好的日子。不幸的是,比利学艺不精,无法精准控制时间跳跃,他不知道下一个瞬间自己会进入哪个时刻。这时我们渐渐明白,原来故事碎片并非胡言乱语,而是比利在不同人生之间的随机跳跃。
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愚蠢,在于自始至终它都被当成结束战争的“手段”。下令的政客视其为战略,执行轰炸的飞行员则高高在上。没有人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据解密史料记载,这次轰炸是精心策划的,先投高空炸弹爆掉建筑物顶层,再投燃烧弹确保所有东西烧起来。
小说里写到,比利在时光跳跃中看见“整个城市变成了月球”。他和其他幸存者只能在滚烫的废墟里爬行。“谁也不讲话,事实上也没有什么话好说。有一件事是没有问题的:城里所有的人,不管是谁,按理都活不成了。如果城里还有人在走动,就表示这次大轰炸的计划还有缺点:月球上是没有人的啊!”
他们遇到了美军——自己人——的侦查机。飞机见到活人就扫射,试图斩草除根,确保更好地完成任务。对于这一行为,比利,或是作者这样解释:事情就是这样——目的是为了加快战争结束。
逃离死城后不久,比利和其他幸存战俘又被押回德累斯顿挖尸体。冯内古特称之为挖“尸矿”(corpse mine)。尸体太多挖不完,干脆用喷火枪就地烧掉。这项工作里有比利,有冯内古特的战友,还有冯内古特本人。《五号屠场》是老冯和战争中几十万次的死亡共同写成的。
有历史学家认为德累斯顿大轰炸是“惩戒性”的,敌人在杀死我们的平民,所以这是公平的。对此,冯内古特没有做出直接评价,他讲了个故事:耶稣正在跟父亲学木匠活。两个罗马兵走进来,拿出一张设计图,要求次日完工,要做一个十字架。耶稣父子很高兴接了这个订单,而那个蛊惑人心的煽动者将被钉死在这十字架上。冯内古特还在小说中引用了杜鲁门下令用原子弹炸日本后发表的宣言,宣言核心意思也强调“惩戒”的正义性:敌人比我们坏,理应惩罚,上苍保佑拥有原子弹的是我们。

这种观点该做何解释呢?冯内古特依然不发表看法,只是反复讲另一个故事。战争临近尾声的一天,比利他们在德累斯顿挖尸体,一个战友从废墟里捡了一把茶壶,于是看守抓住他枪决了。还能做何解释呢?听听外星人的看法:没什么好解释的,就你们地球人爱问为什么。在小说里的外星人看来,人类喜欢解释原因、分析和预言,是因为看不到整体时间。这不难理解,如果看得到无限,意义也就消失了。可是人类从来没拥有过全知视角。人类必须解释。人解释世界,再对解释做出解释。最后难免满口都是自以为是的谎言。
德累斯顿大轰炸之后,交战双方动用了解释机器,指责对方不义。战后几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军事专家和政府都参与了这一行为。大轰炸能叫大屠杀吗?大轰炸算是战争罪吗?吵得不可开交。任何试图通过战争叙事寻找因果逻辑的行为,都是人类在为自身的愚蠢和荒诞找借口。战争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冯内古特问战友:这一场仗打下来,你有什么收获?战友想了想说:我再也不相信政府了。
事情就是这样。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