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的入侵
作者: 杨殳
小说《父怪》,作者是美国科幻小说家菲利普·迪克,发表于1954年12月,中文仅八千多字。一晚,八岁男孩查尔斯突然如受惊中邪,死活不愿和父亲一同晚饭,并声称眼前的男人虽然看起来是爸爸,但其实是“另一个人”。母亲对此不甚重视,也并未意识到在某些瞬间,丈夫的眼神变得极其陌生。随后,查尔斯在小伙伴的帮助下确认了自己的猜想:真正的父亲遭到不可言说之物入侵,内部已被吞噬——那“东西”取代了他。
随后孩子们发现,独处时的“父怪”会突然瘫倒变软,像“被关闭了电源”。他们推测定有什么东西在控制“父怪”。果然,他们在院里找到一只多足节肢动物。接着,在竹林中散着腐臭的垃圾中,他们发现了这只虫子的卵:一大坨湿软的白色圆柱体,包裹着层层织网,状似“发霉的蛹”,身上隐约显现出胳膊腿和“尚未成形的头部”。查尔斯惊讶地发现,那五官几乎和妈妈一模一样——待其成熟,破茧而出,定会成为一只“母怪”,吞噬妈妈取而代之。更为可怕的是,还有一只小小的“查尔斯怪”正准备着将自己吃掉。
小说《父怪》并未给出任何推理或科学解释,而是让小孩凭直觉论断:这是一种“我们世界之外”的东西。一旦遭此物入侵,一个人便不再是他自己。并且,这种入侵是会传染的。
对此小说并未给出任何推理或科学解释,而是让小孩凭直觉论断:这是一种“我们世界之外”的东西。一旦遭此物入侵,一个人便不再是他自己。并且,这种入侵是会传染的。从阅读接受心理来说,正是这种无从解释的未知,滋生出了怪异的恐怖之感。
这是高段位惊悚故事常用的叙事策略,以留白来营造氛围,勾起人的不安,却没有故弄玄虚之感。试图描述、解释这种不安时,我想到弗洛伊德谈论恐怖故事时创造的概念——unheimlich,中文译作“暗怖”或“暗恐”。弗洛伊德举例说,替身、假体或仿真的机械体所唤起的不安之情,就是“暗怖”——熟悉的事物内包含着陌生。
事先张扬的外星人入侵事件
不过,这番理解,不适用于20世纪50年代的科幻读者。于他们而言,“父怪”不用解释,那当然就是外星生物。“外星生物入侵”的模式当时正成为科幻小说的一股潮流,故事的基础设定已是约定范式,成为一种“子类型”。
顺着这一线索追溯,我读了另一部长篇,美国硬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1951年发表的《傀儡主人》。海因莱因有个外号叫“科幻先生”,最擅长描写未来可能出现的事物与生活方式。《傀儡主人》写外星人入侵地球,其“入侵”方式真实可感。外星飞船明目张胆降临在美国某地,却无人见到外星人,因为它们并无正经的身体,而是一坨坨鼻涕虫样的寄生物。鼻涕虫袭击了第一个遇见的地球人,便“骑”在他背上,用他的大脑思考,用他的身体行动,通过他的嘴说话——活脱脱一个外挂大脑,吸收同化宿主脑内信息,进而将其变成傀儡。
更多的鼻涕虫“驾驭”了地球人。比如一个傀儡交警拦下车辆,要求司机到岗亭内检查,谈笑间便被“发”了一个新大脑,司机出来时已成了地球人的“叛徒”。转眼,连白宫和五角大楼内也发现了叛徒。人类被分成两大阵营。地球作战指挥部墙上挂起红绿色块地图,追踪遭“侵蚀”的动态。为辨识敌我,白宫推行了“裸背计划”,继而升级为全裸的“日光浴计划”,上自总统,下至平民,但凡穿衣服的,就是嫌疑人。政令行之有效,但却引发了猜忌和应激,假警报频频响起,有人不小心穿了衬衫,警官一紧张将其枪杀,因鼻涕虫可寄生在动物身上,导致有些地方见狗就杀。整个美国陷入“恐怖时代”,朋友杀死朋友,妻子告发丈夫,任何有关鼻涕虫的谣传都会激起民众互审与私刑。
20世纪上半叶,不少人确信外星生物存在,UFO和外星生物研究不但是流行文化的重要构成,也是政府真金白银投入的大项目。不过在现实层面,对外星人入侵的想象,更多是种释放焦虑的叙事载体,其背后藏着公众真正害怕的“东西”。
1938年万圣节的晚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突然插进一段实时新闻,说有不明飞行物降落在距新泽西州政府仅22公里的农场,并很快证明是火星人入侵地球,节目实时做了现场报道。然后,广播里传来纽约市撤离警报,播音员声称火星人已发动毒气攻击,这“可能是最后一条广播了”。在播音员的咳嗽声中,广播陷入了沉默。
虽然五分钟后播音员说明了真相,插播内容其实正是据英国小说家H.G.威尔斯《世界大战》改编的广播剧,但恐慌已通过收音机蔓延。有人着手准备逃难,有人结伴拿起武器自卫,警局也接到“证据确凿”的报案,声称外星人正在疯狂进攻,还有听天由命者,选择去教堂做最后的忏悔。次日,各大报纸不得不反复“辟谣”,节目主持人奥森·威尔斯也出来郑重道歉。
这只是因为广播编得好,主持人讲的生动吗?当然不是,当时正处在二战全面爆发前夕,美国尚未从大萧条中恢复,战争恐慌和生存危机令公众安全感尽失。这也意味着,稍有风吹草动便可唤起联想。二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这种恐慌不但没有消失,反而进一步升级。《傀儡主人》的最后,地球当然保住了,但某种恐惧却笼罩了人类社会,我们只能学会在其中生存,就好比“我们不得不学会与原子弹共存”。
这看似随意的一句,实则点题。
《傀儡主人》的最后,地球当然保住了,但某种恐惧却笼罩了人类社会,我们只能学会在其中生存,就好比“我们不得不学会与原子弹共存”。
无论叙事形式是小说、广播剧、电视电影,还是子虚乌有的传言,唤起的焦虑都是真实的。情绪体验会让人倾向于相信那些自己“愿意”相信的。个体情绪体验的集合,构成群体心理倾向,就像一场情绪的数据“大爆炸”,一触即发。
电影里的“病毒”
经典科幻故事之所以流行,因其设定虽是未来的“幻”,但其中人物处境和情节推演都关于当下,准确捕捉了群体心理的“真”。这种从一个可能性的概念出发,进而推想出故事的创作方式,在海因莱因的时代很是流行,他就曾表示,科幻小说就是一种“推想小说”,关注点并非技术本身,而是人对技术的反应。
作家杰克·芬尼1955年的科幻长篇《致命拜访》中“他者”的入侵更为贴近日常。故事发生在一个小镇上,一位医生收到几个紧张兮兮的病人,认为自己的家人变得陌生、冷漠。起初医生怀疑是个案,随后患者愈多,他的女友也发现父亲变得怪异。随后医生在女友家发现正形成人形的“豆荚”,他与作家和心理学家朋友一同研究,试图将发现报告白宫,但却无法让人相信。当他们不得不自己逃离小镇时,医生却发现,身边的朋友似乎也不再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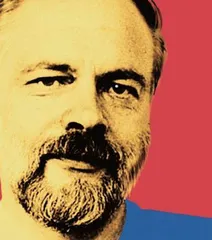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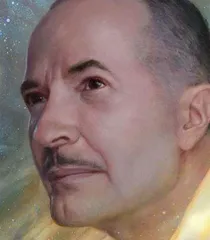

经典故事模式的心理共鸣,往往会在不同时期的相似群体情绪下再次引发共振。1978年,好莱坞再次翻拍这个故事,中文名为《人体异形》,却对结局做了修改。有评论认为,这一版试图唤起的“共鸣”,也许和当时“水门事件”引发的信任危机有关。之后的好莱坞又有了多次改编,可也正因为电影里的“病毒”过于明确,敌我对战声势过大,反而失去了小说中极具心理惊悚的两个要素:一是入侵的无形,受害者没有任何知觉,一旦外星“豆荚”成熟,只要本体睡着,便会灰飞烟灭,取而代之者唯一的差别是“眼神漠然”;二是主人公所代表的普通中产阶层,是对明天最抱有期望,也最怕稳定生活遭破坏的人群。小说非常注重心理描写,不但以内部视角描写主人公对入侵者的调查,还指向了自我怀疑:也许并未发生什么,而只是一种妄想幻觉的传染性精神恐慌?故事的转折点,主人公甚至怀疑是自己发了疯。而到了最后抵抗的时刻,又无法克制内心的服从冲动——要知道,做个不从众的人是何等艰难,而特立独行后又不得不面对可怕的孤独。
《致命拜访》《父怪》和《傀儡主人》的故事都是对“他者”入侵恐慌情绪的一种明喻,《致命拜访》的不同,正在于从心理层面摹写出了这种恐慌更为复杂的一面——这不仅是对异类的排斥,更是恐惧和欲望的合成物,害怕被洗脑,又渴望被洗脑,担心遭“他者”吞噬,又忍不住要同化异类的冲动。
另一方面,对“他者”入侵的终极焦虑指向了人的存在。早在1950至1960年代,菲利普迪克就在《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中提出假设,若一个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只是人工智能,那该怎么办?
从二战到冷战再到“9·11”,再到当今的后疫情与AI时代,世界已然不同,各个层面的共同体都日渐趋向保守排异,根植于人性的“他者”恐慌似乎再度觉醒,不但难以消除,还可能被引导和利用。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