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爱烂的写作课:贫穷的质感
作者: 郁子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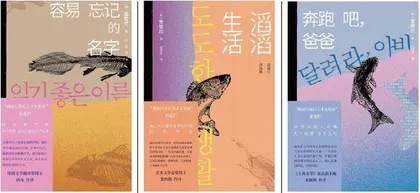
《生活滔滔》
《奔跑吧,爸爸》
金爱烂简介:
韩国作家,1980年出生于韩国仁川市。2002年凭借短篇小说《不敲门的家》获得第一届大山大学文学奖。2013年,33岁的金爱烂凭借短篇小说《沉默的未来》,拿下韩国文学的最高奖项“李箱文学奖”。金爱烂的作品兼具通俗性与文学性,深受年轻读者喜爱,多次登上畅销书排行榜。
当下的贫穷书写,走出了由物质匮乏导致的生存危机,不再写人因饥饿而作出的种种非人选择,转为关注人的精神困境,关注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消费社会里的新穷人”。韩国作家金爱烂所写的正是这类新穷人——住在首尔的韩国年轻一代,被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光鲜亮丽的消费幻象所吸引,却发现阶级跃升的通道早已收窄,最终负债累累,越努力越贫穷。新型贫穷的特质不是苦涩,而是酸楚,金爱烂的笔下,每一页都有酸楚。
贫穷的细节
金爱烂的短篇小说《角质层》是当下贫穷书写的好例子,小说里充满了贫穷的细节。主人公“我”是在首尔工作的28岁女白领,向往精致美好的中产生活,喜欢用“稍好点儿的东西”来“照顾自己的心情”。也就是“新鲜果汁”“无荧光剂的纸巾”“比普通豆腐贵几百元、更柔软的国产豆腐”“比普通卫生巾贵两倍的有机卫生巾”以及“不是普通熨斗的蒸汽熨斗”,还有贷款租下的“最宽敞最舒适”的房子……这些细节看似与贫穷无关,反倒是物质富足的表现,其实隐藏着消费社会对新穷人的陷阱。
金爱烂写贫穷,不只写单一维度的细节,还写对立冲突的细节,挖掘细节背后的隐喻。《角质层》里她写到了三组细节:
高跟鞋的“高”与地下铁的“低”。金爱烂笔下的主人公,穿了一双9厘米的高档手工高跟鞋,高跟鞋摇摇欲坠,说明主人公拥有的物质生活极为脆弱,但只写高跟鞋还不够,金爱烂又写主人公穿着高跟鞋坐地铁,高跟鞋与地下铁,构成了一组对立冲突、充满隐喻的细节。9厘米的高跟鞋象征着主人公渴望抵达的高度——“我常常盼望生活质量能再提高一拃……9厘米也好”,让她感受到“不适也是特权”的兴奋。地下铁则有着“像海螺一样朝地下无限延伸的台阶”,在远低于地平面的空间里,即使踩上9厘米的高跟鞋,也于事无补,根本触及不了地面以上的世界。小说里的富人坐在轿车里,“脱下的高跟鞋放在驾驶席旁”,“穿着看上去无比柔软的拖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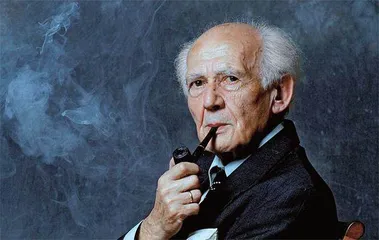
“新穷人”是指:有缺陷的消费者、失败的消费者。面对消费社会提供的各种惊人选择,这些收入水平仅够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穷人,不能购买、无法选择;不能掌控、难以从容。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定义的美甲的“光滑”与角质层的“粗糙”,是小说里的另一组重要细节。做美甲的过程每一步都是消费陷阱,但主人公依然沉溺在“被照顾”的幸福里,甚至感叹“身体是最昂贵的饰物”。两年前,农村出身的她,还对做美甲的女人“怀着隐隐的轻蔑”,觉得“美甲是极端奢侈的行为”。美甲做在手上,手是劳动的象征,角质层粗糙,能保护双手,做美甲的过程就是去除角质层的过程,但失去角质层保护的手,变得更软弱了。更深一层,这是消费社会在去除与消费无关的劳动者,角质层就是主人公自己,她除掉了她自己——消费社会里的新穷人,一切努力化为了反对他们自身的力量。
书中主人公临时起意,拉着新旅行箱去见朋友,朋友在“N首尔塔”顶层的咖啡馆打工,去那儿的路很远,主人公拿着婚礼的花束,又穿了高跟鞋,不得不打车,还被迫买了“N首尔塔”的门票,可谓“一路上净是苦难”。终于见到朋友时,却得知约定的旅行计划再度告吹,朋友家出了变故。穷人的家里总有变故,即便拥有了旅行箱,也无法拥有说走就走的自由。这段拖着无用的旅行箱,千难万苦登上塔顶的旅程,仿佛是主人公人生的写照,旅行箱自始至终都是累赘。小说结尾,主人公感慨,“我们不像是出门或者即将出门,倒像是被驱逐到远方的人。好像从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拖着如此庞大的行李箱走来走去。”
被凝视的视角
金爱烂笔下的贫穷经常伴随着羞耻感,其背后更有种“被凝视”的视角,而消费社会的一大特征便是“看与被看”,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凝视”。《角质层》的主人公“我”,时刻处于“被凝视”的状态。一方面她主动参与这种“被凝视”,渴望在众人面前展现“得体”:穿9厘米的高跟鞋,穿讲究质感和线条的衬衫短裙,精心打造美甲,把身体也变成饰品展示。比起没钱,主人公更在意自己“看起来没钱”。消费社会夺走了穷人的道德,穷人一旦无法履行消费义务,就会为自己是有缺陷的消费者而感到羞耻。

金爱烂的贫穷书写贴近现实生活,引起了年轻人的强烈共鸣,但她笔下的人物常常有点儿面目模糊,更像作家文学人格的化身,是承担着社会批判功能、“有意义的小说人物”,没有真正的“自由意识”。
另一方面,在婚礼上,当“人们充满期待的目光”齐刷刷聚集在主人公身上时,他们看到的不是她拼命展示的漂亮指甲,而是她衬衫腋窝下可笑的汗渍——作为饰品展示的身体背叛了她,让人记住的不是美丽女人,而是“流汗很多的女人”,她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但问题是,他们真的“看”到了吗?我们只知道这一幕可能被相机拍下了,金爱烂没有写婚礼客人的视角,小说自始至终只有主人公“我”的视角,“我的脑海里情不自禁浮现出相机捕捉到的我的身影”——无论现实中的“凝视”是否真的存在,光是主人公自己想象出的目光,就够她羞耻的了。
小说结尾,主人公和朋友并排而坐,一起喝罐装啤酒,尽管朋友和自己阶层相同,她仍然感受到“被凝视”的目光。她宁可用食指大力抠开啤酒罐,破坏美甲,也羞于向朋友承认自己做了美甲。消费社会下新穷人的羞耻既来自无法消费,也来自消费本身,主人公身上残存的劳动道德与消费道德,二者天然互斥。
和金爱烂的许多小说一样,《角质层》也使用了第一人称,但这里的第一人称提供的不仅是感同身受式的代入感,金爱烂用大量心理描写成功“催眠”了读者,巧妙地转换视角,将文本内的目光引向文本外的读者,“被凝视”的人从小说的主人公“我”,变成了读者自己。再者,作者创作的过程,是否也难逃“被凝视”的目光?创作贫穷但虚荣的人物,或许会让许多作者感到不适,但将贫穷与羞耻、虚荣、嫉妒等种种不堪,一起袒露在读者面前的金爱烂,显然突破了这层道德枷锁。
复杂的穷人
短篇小说《三十岁》的主人公秀茵,出身贫寒,通过复读才考上首尔某大学的法语系。尽管勤工俭学,甚至去做医院的等效性试验,仍然付不起学费和生活费,花了7年才毕业。毕业后因大龄女性和文科生的身份,找不到工作,其间父亲又成了车祸肇事者,家庭彻底衰落,此时的秀茵还欠着巨额的学生贷款。
秀茵走投无路,加入了传销组织,但金爱烂没有让她成为“无辜的受害者”。从一开始秀茵就觉得不对劲——“我进了一个奇怪的公司”“这不是传销吗”,但很快她就为自己找到了理由——“处境艰难,只要不用杀人,我什么事都愿意去尝试”。传销组织里没有看起来像“傻子”的人,充斥着和她一样的大学生,小说里用了一个有力的细节,秀茵在组织里的上级,每次都认真检查她的客户管理卡片,“像论文老师似的帮我删减”。
秀茵加入传销组织后,把身边的人际关系全部卖了,沦为了加害者的共谋。其中最过分的,是她骗了曾经信任自己的学生慧美,一个更无辜的人,导致慧美自杀未遂成了植物人。秀茵坦白“我试图不去看处于金字塔最底层的人,或者从未想过自己也会成为这样的人,或许认为只要不是我就行”。这些自白让秀茵成了一个复杂的穷人,她对自己的恶行自知、惭愧,却无法停止。
金爱烂写出了消费社会下新穷人间的人际关系,传销组织就是这个社会共谋网络的缩影,小说里传销组织以“发达国家的新概念网络营销”自诩,卖的不是物品,而是人。人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骗局,却源源不断地向内输送新鲜的无辜者,把这张网打造得越来越牢固。
《三十岁》的整篇小说是秀茵写给十年前、同住读书院隔间的姐姐的一封信,信中有自省和忏悔的一面,但更多是无奈与无力;另一篇小说《卢赞成和埃文》,年仅10岁的男孩赞成,打工攒下10万元,本来要给病重的老狗埃文做安乐死,却禁不住电子商品卖场的诱惑,说出了“三天左右,埃文应该可以等待吧”这样的话。这些人物无论年纪多小,都被困在贫穷的命运中,他们对自己的悲惨自知,却无力改变,始终没有实现对命运的超越,也没有完成对自身的救赎。
金爱烂的小说往往写至此处,便戛然而止,仿佛未完成一般,但她让现实中的读者,通过识别这种贫穷,有了逃脱的可能性——当下韩国或中国的部分年轻人,便续写了金爱烂的人物故事,他们抛弃社会主流要求,主动追求极简,降低开支,以一种低欲望的生活对抗消费社会,寻找精神生活的“富足”。又或许,终有一天,我们能超越穷和富的概念,用其他维度来评价一个人、一种生活。
(责编:常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