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里”科学家的红色人生(二)
屠呦呦:钟情科学,向医而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出自《诗经》中的《小雅·鹿鸣》。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小鹿们在野草地一边吃艾蒿一边不时发出鸣叫声的欢乐场景,这场景跨越了两千多年的时光,在宁波开明街的一户住宅内重新显现——呦呦,带着一位父亲对女儿的美好期待,而一句“蒿草青青,报之春晖”,也预示着这个女孩将和青蒿有着紧密的联系。
“我学了医,不仅可以远离病痛,还能救治更多的人,何乐而不为呢?”屠呦呦的医学理想并非从一开始就确立,这与她16岁那年的经历有关。
1946年,16岁的屠呦呦不幸感染了肺结核。当时的医疗水平较为落后,肺结核的死亡率极高。但幸运的是,经历了两年多的中药治疗,屠呦呦终于康复了,中药将屠呦呦从死神的手中拉了回来。也是在这两年多的治疗过程中,屠呦呦对中医药学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而后将自己的毕生心血都奉献给医药事业。
21岁时,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学习生药学。毕业后,她在卫生部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1959年,为响应毛泽东主席“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屠呦呦积极参加了“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并自主学习和掌握中医药专业知识。在工作培训之余,她常到药材公司学习鉴别药材的真伪和质量,学习中药的炮制方法等知识。这些经历都为她之后进行抗疟药物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疟疾,中国民间俗称“打摆子”,是疟原虫侵入人体后引发的一种恶性疾病。20世纪60年代,疟原虫对奎宁等原有抗疟疾药物产生了抗药性,抗疟新药的研发在国内外都陷入了困境,全球疟疾疫情蔓延,人类饱受疟疾之害。1967年5月23日,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的“五二三”项目正式启动。1969年1月21日,中医研究院加入“五二三”项目,时年39岁的屠呦呦临危受命,担任中医药协作课题研究组组长。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屠呦呦说:“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是组织培养了我,一定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这个决心比较大。”
设备简陋,资源匮乏,资金短缺,人手稀缺,时间紧迫……面对一道道难关,屠呦呦没有退缩,没有放弃。“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屠呦呦和她的团队对2000余个中草药方进行筛选并整理出640种抗疟药方集。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之后,屠呦呦最终在《肘后备急方》一句“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中获取了灵感,并创建了低沸点溶剂提取的方法。“山有峰顶,海有彼岸。漫漫长途,终有回转。余味苦涩,终有回甘。”1971年10月4日,对鼠疟原虫抑制率达100%的青蒿乙醚提取物被成功提取。1972年11月8日,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被分离提纯。1973年,经过海南疟区的临床试验,青蒿素被证实为抗疟的有效成分,由此人类抗疟历史步入新纪元!
在科研条件如此艰苦的情况下,屠呦呦带领着团队攻坚克难,面对失败不退缩,终于胜利完成科研任务。青蒿素问世40多年来,共使超过600万人逃离疟疾的魔掌。“在人类的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这样的机会并不常有。”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西·夏皮罗如此评价发现青蒿素的意义。

为什么屠呦呦可以在平凡岗位上大有作为?或许我们可以从她说过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一个科技工作者,是不该满足于现状的,要对党、对人民不断有新的奉献。”
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开创性地从中草药中分离出青蒿素应用于疟疾治疗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首位获诺贝尔科学奖的本土科学家。在获奖演讲中,她深情讲述了中国科学家寻找抗疟新药、发现青蒿素的过程始末。“有机会接受如此重任,我体会到了国家对我的信任,深感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决心不辱使命,努力拼搏,尽全力完成任务。”屠呦呦和她的团队用一辈子的不懈努力,成功地将中医、中药推向了世界,为中国科学界嵌上了最亮的一颗明珠。
屠呦呦曾说:“我喜欢宁静,蒿叶一样的宁静。我追求淡泊,蒿花一样的淡泊。我向往正直,蒿茎一样的正直。”她也曾说:“我希望年轻人多考虑党和国家的需求,把中国的优势、把自己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多做创新性贡献。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纵使集荣誉于一身,屠呦呦更关注“在这座科学的高峰上,我还能攀登多久”。她从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依然坚持着青年时期的医学梦想,并用过往的实践和现在的躬行,向新一代科研者表明“中西会通缘,十年磨一剑”的初心和期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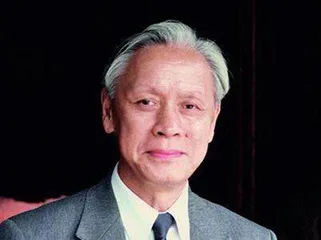
顾方舟:一颗糖丸护佑亿万儿童健康
2021年10月29日,顾方舟雕像揭幕仪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举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王辰和顾方舟的女儿顾晓曼共同为雕像揭幕。这位被称为“糖丸爷爷”的科学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重“回”协和。
顾方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长,著名的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医学教育家。他在中国首次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成功研制出首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和脊髓灰质炎糖丸疫苗,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中国脊髓灰质炎疫苗之父”。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平静地离开人世,享年93岁。同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隆重举行。顾方舟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妻子李以莞替他领回了勋章和证书。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是一种严重威胁儿童健康的急性传染病。20世纪50年代,脊髓灰质炎在我国多地流行。
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带领研究小组调查了部分地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标本后,从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且成功定型。这是我国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用病原学和血清学方法证明了Ⅰ型为主的脊灰流行,为控制脊髓灰质炎传播提供了流行病学资料。
1959年,顾方舟前往苏联考察脊灰疫苗情况时发现,“死疫苗”和“活疫苗”两派各持己见,争执不下。“死疫苗”安全、低效且价格昂贵,“活疫苗”便宜、高效,但安全性还需研究。中国究竟选择哪一条技术路线?没有人能解答。顾方舟在充分考虑国情国力后,果断提出建议:要走“活疫苗”路线。1959年12月,经卫生部批准,我国成立脊灰活疫苗研究协作组,顾方舟担任组长,开展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究工作。
早在1958年,我国就决定在云南昆明郊区建立猿猴实验站。1959年1月,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1964年,顾方舟举家迁居昆明。他下定决心,就在昆明扎根下去,为这个事业干一辈子。顾方舟曾回忆:“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没地方住,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
当时顾方舟制订了两步研究计划: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在动物试验通过后,进入了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然而,谁来第一个做人体试验呢?
顾方舟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他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后,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异常。但之后,顾方舟却要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大多数成人本身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那么,到哪里寻找学龄前儿童呢?谁又愿意拿自己的孩子做试验呢?
“我是组长,我带头。”顾方舟抱来他当时唯一的孩子。“我们家小东不到1岁,符合条件,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后来,实验室的同事里有五六个孩子都参加了这个试验,人数很快就凑齐了。
经历了漫长的一个月,孩子们的生命体征正常,Ⅰ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1960年,2000人份疫苗在北京投放。Ⅱ期临床试验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随后,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人扩大到450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型城市展开了Ⅲ期临床试验,获得成功。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很快遏制了疾病蔓延的势头。投放疫苗的城市,疫情的严重程度纷纷削减。
面对逐渐好转的疫情,顾方舟丝毫没有松懈。当时,液体减毒活疫苗需要低温保存运输,不利于大规模推广。服用时,小孩还不愿意吃。怎样才能制造出既方便运输、又能让小孩愿意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发灵感: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固体糖丸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糖丸疫苗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效力的前提下,也大大延长了保存期。
随着糖丸疫苗大规模生产,我国进入全面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的历史阶段。1975年,顾方舟的团队又开始研制三价混合型糖丸疫苗。1985年,终于探索出了最佳配比方案,三价糖丸疫苗研制成功。1986年,三价糖丸疫苗在全国推广使用,为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提供了有力武器。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郑重签名,标志着我国成为无脊髓灰质炎的国家。
这一路上艰苦奋斗,顾方舟从未居功自傲。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门口悬挂着一副挽联:“为一大事来鞠躬尽瘁,做一大事去泽被子孙”。这是顾方舟一生的写照。
一颗小小的糖丸,护佑着亿万儿童的健康。顾方舟穷毕生之力,为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在我国公共卫生史上树立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陈薇:她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冲锋在“战争”一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有一位女科学家紧急奔赴武汉,执行科研攻关和防控指导任务。在武汉抗疫的113天里,她带领团队用一项项关键成果,为最终的胜利加上了一个个决战决胜的砝码,她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生物安全专家陈薇。
陈薇是我国为数不多的女将军。她曾说过,疫情就是军情,疫区就是战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她闻令而动,驰援荆楚。
2020年1月26日,大年初二,陈薇抵达武汉,从进入疫区的那一刻起,她就开启了“忙到起飞”的模式。两天后,她与同事研制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获得医疗器械注册证书,实现了新冠病毒的快速检测,加快了确诊速度。
疫情防控的关键在于早发现、早隔离、早确诊、早治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陈薇团队仅用4天时间,就搭好了负压帐篷检测实验室,并迅速投入使用,为临床治疗提供诊断依据。她还提出许多指导抗疫的正确见解,被网友们称赞:“这才是一位院士该有的表述,专业而有远见!”
陈薇经常鼓励团队里的官兵:“在生物安全防控的战场上,我们是一线中的一线!”这个“一线”意味着要屡次冒着生命危险,与各种足以致命的病原体短兵相接,在无形的战场上拼死搏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