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可健康,也可病态
作者: 余运西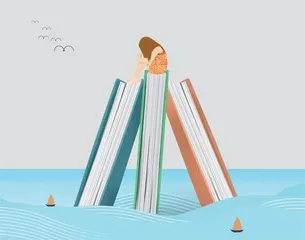
成年人的世界除了“不容易”三个字,还有“焦虑”二字。一边是工作忙得鸡飞狗跳,一边是生活依然捉襟见肘;一边期待过安稳的日子,一边总有想不到的意外来袭……“丧文化”“快乐肥宅”“自杀式单身”“空气式恋爱”“佛系社交”,这些“大火”的网络流行词汇,也从某些方面折射出中青年群体的焦虑。
作为负重的一代,中青年为工作、为家人、为生活、为婚姻而焦虑都属正常吗?焦虑水平的高低与职业身份关系大吗?化解普遍的社会焦虑,“出口”到底在哪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陈祉妍。
问:有数据显示,焦虑症的发病率在20 世纪80 年代是1% ~ 2%,现在已经步步攀升,甚至可能超过了10%。生活如此多“焦”,在全世界都是普遍现象吗?
答: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工作压力都在明显加大,民众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根据2019 年公布的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中国成人精神障碍中焦虑障碍的患病率最高,为4.98%。
去年《柳叶刀》的研究也表明,2020 年全球范围内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病例数增加了28% 和26%,生活在受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的国家的患病率大幅上升,其中女性和年轻人受到的影响最大。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多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全球心理健康。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22 年全球风险报告,心理健康问题已经进入人类前10 大风险。所以说, 生活如此多“ 焦” 确实是世界普遍现象。
从问题的普遍性、严重性,以及具备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来衡量,抑郁和焦虑障碍都位居精神障碍患病率的前三位。抑郁和焦虑障碍尽管常见也可治疗,然而在公众中存在许多认识误区,公众对抑郁症的正确识别率只有35%,焦虑症更低,只有21%。
问:去年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0)》显示,18 ~ 34岁人群最焦虑。青壮年的焦虑水平为什么要高一些呢?焦虑水平的高低与职业身份关系大吗?
答:在成年期,青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最为突出,抑郁、焦虑水平都更高一些。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个结果是比较稳定的。焦虑与压力、不确定性等有关。青年要解决职业定向、恋爱婚姻等问题,且大多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一些人处于职业选择、新入职不适应等阶段,尚未确立稳定的职业发展道路,也未建立坚定的职业自信;一些青年尚未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择偶、求偶、失恋等生活事件也会带来不少压力。
过去10 多年里,我们的研究团队针对全国范围内的科技工作者做过3次大范围调研,也发现中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焦虑水平较高,而中老年科技工作者的焦虑水平较低,50 岁及以上年龄组的焦虑得分显著低于其他年龄组。科技工作者焦虑问题的特点是轻度焦虑普遍存在,而较为严重的焦虑问题较少。
当然,不同职业的从业者,其心理健康水平存在差异,焦虑水平也确实存在差异。一般来说,当某个职业收入比较稳定、工作环境相对良好时,从业人员总体的心理健康状态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从事这一职业,如果某个人觉得比较匹配,带来更多的内在满足感,那也会抵消压力带给他的负面影响,包括焦虑。
问:青年期的心理健康问题较为多发,请问青年心理健康问题的预防与干预,需要从哪些方面发力呢?
答:我们要从两个角度去理解心理健康问题,一个是外因,一个是内因。从外因的角度,就是我们怎样为青年营造一种更适合他们发展的环境。而从内因来说,就是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一代,让他们在长大成人的时候有能力应对生活压力,调整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进取心态。
从根本上来说,这两方面是一个整体,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从孩子上幼儿园、中小学开始,就应该做好心理健康教育,打好基础,让孩子们成长为大学生、研究生直至科技工作者的时候,拥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和调适能力。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老师对孩子的成长作用巨大。父母和老师如果只注重孩子的物质需求和学习成绩,对孩子的心理需求不闻不问,就容易堵塞跟孩子建立良性沟通的渠道。
我们要引导孩子学会自我疏导,培养良好的自我意识和适应学习、生活环境的能力;学会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以积极的心态去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帮助同学、亲近社会,在与别人的交往中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素养的提升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身边有值得信赖的人,就能有力地帮助他们抗击焦虑和面对危机。一个人的社会支持系统越强大,越不容易陷入持续的焦虑之中。

问:焦虑这个问题“可大可小”,您认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关键点是什么?
答:焦虑是每个人都会体验到的正常的心理状态,适度的焦虑能够提高工作效率,让人更有效地解决问题,但过度的焦虑会让人感到痛苦,而且极具破坏性,使学习和工作受到严重影响,简单的任务也变得难以完成。所以,焦虑这个问题确实“可大可小”,也可以说“可健康,可病态”。
其实焦虑本身是人常有的一种情绪,那在什么情况下被认为是病态呢?并不是说一个人非常焦虑,那就是生病了,而应该是这个人的反应与现实状况不符。比如,一个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成绩对考试的结果有着客观的估计,但在考试前出现紧张情绪、看不进去书,甚至出现心慌、手抖、出汗等症状,但一进考场拿到试卷,还是可以正常考试——这就是正常的焦虑。但如果这个学生虽然平时学习成绩不错,但他在考试前总想着会考不好、一败涂地,还出现非常严重的身体上的不舒服,发高烧、拉肚子,最后不敢进考场,那这种情况就需要接受一些专业的引导和治疗了。
现在大家随口就说的“ 我emo了”“破防了”等,反映出的社会心态其实是一种焦虑情绪。缓解这种焦虑,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假、参与一些运动,甚至看书、唱歌、画画、跳舞,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问:除了对焦虑问题的认识,正确预防焦虑和解决焦虑情绪的现实抓手有哪些?
答:大多数焦虑障碍首发于或起源于儿童及青少年时期,因而这些年龄段的人群应该成为初级预防的重点。焦虑障碍是儿童最常见的精神病理表现形式,许多人直到青少年及成年阶段,也未能摆脱焦虑障碍的困扰。通常,加强情感顺应力、强化认知技巧和事前教育是预防焦虑发生的重要策略。
澳大利亚有个“朋友”项目(FriendsProgram),就以一个有效的焦虑治疗方案为基础,将其转化成一个模式化的预防方案,适用于7 ~ 16 岁儿童的焦虑预防,被广泛应用于学校、健康中心与医院。“朋友”会告诉孩子有效的应对焦虑的技巧,帮助其建立情感调适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与自信力。一项对照研究表明,此方案用于实验前有严重焦虑的儿童,干预6 个月后,随访发现,第一次发作并诊断为焦虑障碍的儿童比例由54% 下降到16%。对照研究还表明,当此方案用于一般学生人群及特选高危儿童与青少年组时,焦虑症状的发生率都显著下降。“朋友”干预方案在瑞典、荷兰与美国也得到采用。
问:从社会供给的角度来看,化解焦虑的“出口”目前够不够?化解普遍的社会焦虑,还需要做哪些建设?
答:本质上,焦虑是一种调动心理能量的状态。想要避免陷入病态的负面情绪,我们需要为这股能量找到积极正向的出口,将其转化为改变生活的动力。就个体而言,要提升情绪觉察、分心术、认知重评和人际支持技能,这对于降低焦虑和抑郁风险都十分必要。
针对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压力,我们要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近年来,财富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冲击着社会心理结构,致使我国社会出现了不少负面情绪,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了不确定感、不安全感,群体性焦虑尤其是年轻人的地位焦灼感、压力感十分明显。因此,要加强全社会的心理健康教育,对社会成员进行科学引导。同时,建立社会心理风险预警与应对机制,提高社会心理的危机干预和疏导能力;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心理调节机制和情绪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专业社工以及高等院校、心理咨询机构、工青妇团等群团组织在社会心理救助工作中的作用,缓解“心理弱势群体”的社会压力,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要提高全民素质,建设健康中国,就必须把各个群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