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舅
作者: 徐贵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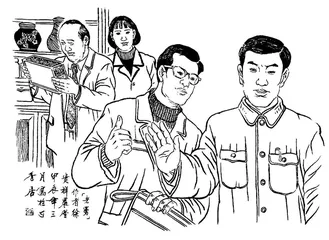
老舅走了,留给我们一堆谜,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一言难尽。在我老家约定俗成的称谓中,“老”也是“小”,老舅是我的小舅。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姥姥的家在洪集老街的中心位置,坐东朝西,最南边是两间高大的房屋,这两间房屋好像没有派上实际用处,权当门楼和杂物间,估计盖这两间房子是准备用作店面的,后来“割资本主义尾巴”,取缔私人生意,这两间大房子才被当成过道。但这两间房子,也暗示我们,姥姥家过去是比较富裕的,因为姥爷做生意。穿过两间大房子再往北,是一个玲珑小院,院子里有一个砖砌的花台,种植有月季和芍药等花卉。姥姥家的堂屋是坐东朝西的,堂屋往北,要穿过一间房子,小时候我和老姨家的两个男孩儿任家杰、任家明,都在这间房子住过。常常是夏天,我们几个孩子玩儿疯了,不回自己的家,都挤在姥姥家这间过道似的房子里,躺在一张竹席床上讲故事。姥姥把这间房屋命名为“狗窝”——老家有句俗话,外孙是姥娘家的狗,前门撵,后门走。从“狗窝”再往北,有一个神秘的房间,仅有朝北的一个木格小窗户,窗前有一棵樱桃树,那便是老舅的卧室,里面有几个装书和装衣服的箱子。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老舅的房间还有无线电零件,以及其他一些象征着科技文明的稀罕物件。
以后我听说一件事情,好像是“文革”之初,正在叶集中学读书的老舅在学校背了个“三家村”的名义——成员有许景环(罪状是“地主成分”)、朱德林(罪状是“好讲话”)、我老舅胡纯声(罪状是“不讲话”)。这个“三家村”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后果,那时候不清楚,记得听父母议论过,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年纪稍微大一点儿才知道当时北京有个“三家村”,因广播电台节目《三家村夜话》得名,成员是邓拓、吴晗、廖沫沙。老舅有幸成为当地小镇的“三家村”成员,让我们小辈既感到惶恐,又感到神秘。
学校“停课闹革命”,老舅等中学生无所事事,在老街经常三五成群,喝茶(估计是水)聊天。大约郁郁不得志,有段时间,老舅极其寡言少语,真的到了惜话如金的地步,连吃饭都要姥姥反复催促,上了桌子一言不发,吃完饭放下饭碗就走,回到他的斗室,读书或者拉二胡,以至于我的姥姥和姥爷担忧老舅得了某种精神病。
老舅当然没有精神病,他之所以少言寡语,是因为他感觉无聊,无话可说。年轻时的老舅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也很清高,他关心的都是国家大事,还有招生招工的消息,不屑于议论家长里短。后来他下放了(城镇户口转为农业户口,就地成为农民),在洪集老街西边的金银生产队开碾米机,在震耳欲聋的环境中工作了两年。
老舅很敬业,也很钻研,学到一些电工和机械知识,偶尔会跟我们讲讲。两年后,老舅被招工到龙潭粮站,成了一名恢复城镇户口的工人,凭借他的聪明才智,加上他踏实勤奋的努力,很快就转干当上分站站长,不久又升任扈胡区站站长。记得那期间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古镇春色》,讲述扈胡小镇的发展历史,文笔优美,故事生动,在六安地区广播电台播出后,让正在读初中的我为之产生很多幻想。那以后,老舅过了几年顺风顺水的日子,还同漂亮的公社副书记、上海知青郝玉兰谈了恋爱,自尊心和信心都得到了满足,话也渐渐多了起来,工作上更是大显身手,没过几年,就调到县里当了粮食局的副局长。
老舅年轻的时候,不仅高大帅气,才华横溢,而且沉稳持重,是我们兄弟姐妹心目中的偶像。我的父亲,是我姥姥家第二代人中最早从政的,他曾经预言我老舅在政治上很有前途。但是老舅后来遇到挫折,最后只当上县总工会主席,是我父亲始料不及的。事实上老舅确实有很大的抱负,他的目标至少是县委书记,给他一个支点,他就能把事情做得非常漂亮,对此我并不怀疑。怀才不遇,高远的理想同现实际遇的差距,是老舅性格变化的第一个重要原因。生长在耕读家庭,自幼受过传统教育,非常重视道德修养,也有兼济天下的情怀,但是现实环境的道德滑坡,使他不得不经常委曲求全。独善其身的为人准则和向世俗屈服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冲突,是老舅性格变化的第二个原因。如果说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家庭生活遭遇了,他曾经有一个小女儿不幸夭折,可能是导致老舅性格陡变的最重要的原因。
判断老舅的人格,应该全程分析。老舅的前半生,虽然几起几落,但总体是积极向上的。老舅争强好胜,工作能力也强,富有牺牲和奉献精神,乐善好施,热情助人,是胡家(我娘舅姓氏)的顶梁柱。姥姥和姥爷生命的最后岁月,主要是老舅和郝姨(老舅妈)照顾的。老舅的后半生,因为上述三个原因,导致精神扭曲,做了一些反常的事情,那已经是病态了。但是他即便病入膏肓,依然关注他人,帮助别人,可见血液里永远流淌着善。
回顾老舅的一生,是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固然是个人性格所致,但确实也有时代的因素。我就个人所知谈谈我对老舅的印象。
老舅比我大十一岁,他属鼠,我属猪。小时候我经常趁他外出,潜入他的斗室,翻箱倒柜。老舅的箱子,除了几件衣服,还有一些书,特别是两摞连环画,成为我多次潜入他斗室的诱因。因为姥爷和大舅都是公职人员,姥姥家的经济条件相对好一些,老舅的书里偶尔还夹着一些小面额钞票,往往成了我偷书之外的不义之财。说来有趣,不知道是因为老舅有限的藏书开启了我的文学梦,还是书中自有人民币的事实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反正在那个时期,老舅的斗室成了我的天堂。
老舅后来走了仕途,当了县粮食局副局长,成了以我姥姥为中心的全家(我家、姨家、两个舅舅家共同组成的洪集胡家)晚辈的共同楷模,我们均为老舅而自豪,并因为有这样的老舅,腰杆子都硬了许多。但是不久,老舅遭遇他人生的一次重大挫折——局长退休,他摩拳擦掌地准备接任,施政纲领都准备好了,可是新任局长却不是他,而是他的下级。老舅在我父亲和大舅、姨父面前大发雷霆,认为无论是工作能力、文化程度,还是人品,那个人都不能和他相比。我父亲安慰他说,某某当了局长,自然有他的道理,不能说这个局长就一定要由你来当,别人当未必就是一塌糊涂,不妨平静下来,支持新局长工作,等待进步。老舅一声冷笑:“让我受他领导,不可能!他凭什么领导我!”
老舅的下坡路,大概就是从这以后开始的。碍于我父亲和他新局长是故交的关系,老舅面子上过得去,新局长也很尊重他,这才相安无事,一起克制地工作了好几年。但是老舅最后还是调离了粮食局,据说,原因是老舅和另一个副局长在好几个场合公开骂了县领导,说他们一群半大橛子(小伙子)坐在主席台上不架相(撑不起台面)——这句话我也听老舅说过。后来老舅平调到县总工会当了副主席,另一个副局长下场更惨,下调到一个局里当工会副主席。
能够想象得出来,老舅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可能终于明白了胳膊拧不过大腿的道理。那个时候,我已经在文学创作上小有名气,在家乡有一些朋友。不知道老舅内心是怎么想的,反正他是屈尊了,给我打电话,让我找县领导说话,早点儿把“副”字去掉。不久,县里一位主要领导到北京,见面后我先是给他看了老舅过去写的文章,再介绍他的人品和工作业绩,再讲群众对他的反映。那位县领导有些困惑地说,这么好的干部,还是个才子,应该重用啊,他是谁啊?我说是我老舅胡纯声。这位领导没有马上表态,脸色凝重地说,这个同志啊,县领导对他看法都不太好,听说很傲慢。我说,老舅个性是强一点儿,但是工作很扎实,在群众中口碑很好,可以再考察一下。过了一些日子,这位领导给我打电话说,确实就是你讲得那样,胡纯声同志是一条汉子,工作能力很强,群众对他的反映还不错。但是也有毛病,还很致命,恃才傲物,经常骂县领导。要跟他讲,以后夹起尾巴做人,不要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更不要动不动就指手画脚。
我连连承诺。可是,这些话我怎么跟老舅讲啊,那不是找挨骂吗?就在老舅扶正当了县总工会主席之后,我和表弟任家杰还是经常同老舅发生争执,我们由老舅的跟屁虫变成对老舅敬而远之,还不时遭到他的讥讽。记得有一次我探亲回去,朋友请我一家到水门塘餐厅吃饭,被老舅撞见了,对我父亲哼了一声说,什么样子,前呼后拥,耀武扬威,有多大能耐啊?
有一次回家乡,老舅跟我说起他出差的故事,在南方开放城市,一位县领导在某种商品面前流连忘返,工会一名干事私下给老舅建议,给这位县领导买一件礼物,被老舅断然拒绝。老舅说,工会的钱是老百姓的血汗,凭什么给县领导买保健药?如果是他的意思,让他直接跟我说。我对老舅说,低头上山,昂头下山,不拿公家钱送礼是对的,但是没有必要把话说得那么冲。老舅听了我的话,勃然大怒道,混账,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你早晚要栽跟头。
老舅骂我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多岁了,师级干部,可是在老舅的眼里,我不仅还是一个半大橛子,而且成了潜在的罪犯。我遇到这样的情况忍忍也就过去了,可是我的两个表弟却难受了,他们都和老舅在一个县里工作,在老舅怨天尤人的岁月里,他们先后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和镇长,老舅在当地经常讥讽各级领导,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他们还要经常性地为老舅擦屁股,譬如老舅同某人发生冲突,他们就要及时地去赔不是,甚至还要为老舅的失误买单。
几年后我才慢慢地悟出来,老舅确实恃才傲物,因为怀才不遇,牢骚满腹,看什么都不顺眼。或许,连老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对我们这些晚辈诸多看不惯,其实还隐含着一丝嫉妒,他那么一个才华横溢、刚正不阿的人,过去一直是我们的楷模,突然之间,我们长大了,工作了,从业绩到影响力都不比他差,他甚至还要向我们这些晚辈求助了,这是他极不愿意接受的,勉强在表面上接受了,内心也是十分排斥的。甚至可以认为,我们每帮老舅一次忙,都会在他心里积累一分怨气。
老舅的晚年是扭曲的,他自己没有意识到,他已经被时代甩出了正常生活的轨道,他的思维还停留在他血气方刚的年代,他因为过于自负而成了一个让人敬而远之的人。
十多年前,老舅退休了,可是他仍然退而不休,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亲朋好友的维权顾问,他接过了我大舅胡效坤替天行道的柄杖,帮助人找工作、申请低保、申请救济、报销药费、解决土地纠纷……值得一提的是,老舅虽然习惯性地“抗上”,但是对于地位比他低、条件比他差的弱势群体,基本上有求必应,基本上两肋插刀,还基本上不顾后果。而为他的一些盲目仗义行为付出代价的,主要是我的两个表弟和我的母亲、我的姨妈,当然也包括我。记得有年探亲回去,带母亲到医院看病,老舅知道了,带领一帮穷亲戚,其中有两个长辈病号,找到我母亲住院的病房,我只好自掏腰包,代表老舅散发扶贫资金,当然,数量有限。
2018年深秋,老舅因患脑出血住进上海同济医院,我姥姥和姥爷麾下的第三代几十人赶到上海为老舅送行,望着插满管子的老舅的脸,望着他千呼万唤紧闭的双眼,不禁悲从中来。老舅,到这年年底他才满七十周岁,他刚刚从西藏回来,刚刚买了一双运动鞋,他病发的当天还跟我的小妹说他要去美国,他有那么多的事情没有做完,他有那么多的困惑没有解开,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他还有一本记录我们几家第二代、第三代所有人出生年月、工作状况、性格特征的笔记本,那是他曾经和我约定要写写《亲情分析》的第一手素材,他这么撒手走了,这个作品我还写吗?
葬礼办完了,在老舅的家里,我们第三代兄弟姐妹九个人相对而坐,默默无语。后来小妹一声哀号,我的爸爸,他是个什么人啊?我说,你的爸爸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虽然有缺点,也做过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但仍然可以定性为好人的普通人。
原载《安徽散文》2023年秋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