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花落处
作者: 王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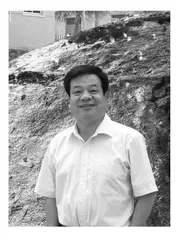
王宝存,陕西宝鸡人。作品见《诗刊》《文艺报》《延河》《飞天》等刊。获“五个一工程奖”“全国鲁藜诗歌奖”“秦岭文学奖”“宝鸡市三年文艺创作成果奖”。作品多次入选《中国年度优秀作品选》等。
一
这些年,朱家滩的好多人披着北京温暖的阳光,沿着门前宽阔的马路住到城市去了,唯有朱满才等少数人依然守在村里。用朱满才的诗描述:我热爱家乡,热爱家乡的每一寸土地,一旦离开家乡,我将无法生存……
朱满才的诗写得不错,在报刊上发表过,还出过两本诗集。但这些成绩给他并没带来多少好处,反而让他的日子潦草了许多。
朱家滩村距北京很远,离县城很近。北京的阳光雨露时常能洒满他的村子,县城里的柏油马路也通到了他家门前。这一切,只等朱满才抬腿迈脚走出去。
青年时代,朱满才在朱家滩小学当民办教师。当时,朱家滩小学有四个民办教师,男的、女的,教语文的、教数学的。后来,一个转正了,一个考上大学高飞了,还有一个扔下教鞭做生意去了,只有朱满才既没有转正,也没有考学,更没有下海做生意,而是一如既往坚守自己的岗位。
那年代,书是兴奋剂,注入神经让人着迷,抱着书如同抱着美女,既开心快乐,又飘飘欲醉。朱满才就是在这个时候爱上诗的,他白天给孩子上课,晚上在灯下读书,读着读着心里热乎了起来,模仿着书上的文字写了起来。为了诗,他顾不上回家,顾不上吃饭,一写一个通宵,一写一沓稿纸。再后来,上级一纸文件,民办教师一律清退,这样,朱满才就回家了。
二
朱满才的老婆叫王彩娥,她明明知道朱满才不喜欢自己,还是坚持给朱满才做饭、洗衣、养孩子。朱满才瘦得像个猴,手只要攥上锄头,不出半个钟头就起血泡。这时候,粉嘟嘟、肉乎乎的王彩娥就会像碌碡一样滚到朱满才的面前,先用自己的桃花眼狠狠地瞪朱满才一眼,接着就张开自己灿若丹霞的小嘴朝朱满才的血泡吹两口热气,再从兜里掏出手绢把朱满才的手裹住,然后,夺过朱满才手中的锄头说:我知道你不是干活的料,回去写你的诗吧。每听到这话,朱满才心里像灌了蜜,不由得乐了,他跳跃着弹出田地,轻飘飘地回到家里,先给自己泡一杯茶,再给嘴上点一支烟,然后,往桌前一坐,一边喝茶,一边抽烟,一边写诗。
朱满才诗写得好,但要发表并不容易。他每发表一首都要把样报或样刊带到村子的广场上给大家看,给大家读。起初,村子的人都围着看,听他读,还有的给他鼓掌、伸大拇指。可后来,看的人少了,听的人也少了,拍手的,伸拇指的人更少了。再后来,人都不看了,也不听了,见他拿着报刊都走了。还有一些没眉没眼的人骂他有病,脑子被驴踢了,不知道挣钱,尽干一些不打粮食的事。朱满才听了非常气愤,他嘲讽说,农民就是个农民,没知识、没文化,天生下就知道卖力气,一点儿都没出息。
村上的人不喜欢朱满才,朱满才也看不起村上人,朱满才干脆和村上的人不来往了,他把诗拿到县城找有文化,懂艺术的人。县文化馆的李馆长是个搞创作的出身,他对朱满才很欣赏,朱满才每次带着诗去,他都要认真地去读,并给朱满才点赞。朱满才喜欢李馆长读他诗的神情,更喜欢跟李馆长在一起,他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知音,自己的成绩终于得到了肯定。于是,到了中午,朱满才拉着李馆长去喝酒,喝到高潮后,李馆长就朗诵朱满才的诗。这个时候,朱满才感觉自己像飞起来一样,仿佛天空都是他的。
那样的时光太好了,诗终于成诗,酒终于成酒。
有一次,朱满才的诗又发表了,为了去县城和李馆长分享,很委屈地把王彩娥搂了一夜。次日早晨,精神抖擞的王彩娥不等朱满才开口,早早打开箱子取了五百元扔到朱满才面前。朱满才抓到钱往兜里一塞,乐呵呵地跨上自行车走了。细细琢磨,这一夜好像一场交易,朱满才陪王彩娥睡觉,王彩娥还得给朱满才付劳务费。
说实话,李馆长这人还是挺有良心的,朱满才请他喝酒,他一直记在心里,也一直想对朱满才有点儿回报和帮助,这不,机会终于来了。就在李馆长和朱满才认识后的第三个秋天,省作协要举办一个全省中青年作家培训班。规定一个县区一个名额,李馆长就把这个名额送到朱满才的手里。
一天上午,泡桐花在窗外摇晃着,树影婆娑,花香暗动。朱满才白手净面,照例在屋子写诗,他像一个匠人,把石头般呆板的文字一个个搬出来,用一种巧妙的方式组合成一个整体,然后,精心雕刻、细细打磨,直至这些文字放射光亮才停了下来。朱满才满意地点燃了一支,长长地吸了一口,那自豪、那神色好像稿费已经从空中飘过来了,等着他伸手去接。
晌午,王彩娥从地里回家。这一次,她从菜地里抽了一把蒜薹准备做蒜薹面。朱满才背着双手在厨房里转了一圈儿,看到王彩娥手中的蒜薹嘻嘻一笑说:“蒜薹好,蒜薹好,要是蒜薹和肉炒在一起就更好了!”王彩娥扑哧一声笑了,她撇了朱满才一眼说:“哪颗牙想吃肉了,叫我看看?”朱满才白了一眼没有吭声,转身出去了,直至王彩娥把饭做好才从太阳地里回来。
下午,朱满才接到李馆长电话,说晚上请朋友喝酒,让他来热闹热闹。朱满才非常高兴,随口答应了下来。
那晚,坐落在县城中心广场的凤凰大酒店六号包间高朋满座,欢声笑语,而朱满才陈旧的衣衫下却掩着一颗滴血的心。他想,明明是文人相聚,不谈创作、不谈作品,一个个却念发财的经。他感觉很无聊,喉咙里发出感叹的声音,他甚至想离开酒桌,找一个僻静地方一个人吃,一个人喝,哪怕吃一碗面、一盘花生米,喝几块钱的酒或者啤酒,也比这里舒服。但是,他最终坐了下来,因为,这里有李馆长,是李馆长请他来的,他就是再不舒服,也得看李馆长的面子,怎么也不能让李馆长难堪。
酒宴终于散了,朱满才迎风走在大街上,心情极为沉重,他后悔参加这样的聚会,他觉得和这些人坐在一起太乏味、太没意思了,他们哪里是文人啊,简直是一群商人,出口是钱,闭口还是钱,好像钱是他们的娘,是他们的舅一样。突然,他的手机响了,不用看也知道是王彩娥打来的。他最不爱接王彩娥的电话了,可是,处于夫妻间的义务又让他不得不接。王彩娥发话了,她很兴奋,声音也很大:“满才啊,你在哪里呀?你不是想吃蒜薹炒肉吗?我给你炒好了,赶紧回来吃吧,放凉就不好吃了。”朱满才刚张开嘴巴又僵了下来,身子像根木头桩子钉在原地半天未动,过了好长时间才恢复了原形。
三
有些日子,朱满才一首诗也写不出来。这种现象在行内叫“断电”,意思和一台手机没了电是一个道理。大部分的作家诗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也都有给自己“充电”的一套办法,有的用阅读来汲取营养,补充自己的不足;有的以游山玩水来启发灵感,扩大自己的视野。而朱满才给自己“充电”的方法和别人不一样,他既不读书也不游山玩水,而是喝酒。与朱满才喝酒的人并不固定,有同学、朋友,也有文化馆的李馆长,有时候他还去酒吧、夜总会喝上一次,顺便找个妹妹陪一陪。朱满才和朋友喝酒时话很多,牢骚也多,喝多了就哭,哭得很伤心,很难过。和酒吧的妹妹喝酒时话很少,牢骚也少,喝多了就笑,笑得很开心、很快乐。偶尔,他还会借助酒的力量拉拉妹妹的手,搂搂妹妹的腰,拉了手,搂了腰还不过瘾,就想开个房子体验生活。可是,那里的妹妹不是王彩娥,手可以拉,腰也可以搂,开房子得另当别论。
有一次,朱满才在夜总会喝了酒后,拉着一个妹妹要开房。妹妹把自己的胸部贴在朱满才的肩膀上,又把喝了鸡血一样的嘴巴凑到朱满才的耳边,笑嘻嘻地对朱满才说:“大哥,开房子可以,得给这个。”说着,岔开手指在朱满才眼前晃动。朱满才知道什么意思,他用手把妹妹的手指攥在一起低声说:“我是诗人,和诗人睡觉是你的荣耀啊,怎么还要钱呢?”妹妹一听,脸色立马变了,一把将朱满才推倒在地上,厉声说:“诗人是个屁,诗能吃还是能喝?”瘫在地上朱满才像一只被抽掉脊梁的犬,半天爬不起来。
喧黄虫叫了,朱家滩的人天不亮就起来了。有的磨镰、有的擦锄、有的给自己的小机械加油、紧固螺丝,只有朱满才躺在自家的床上扯鼾声,他身上的被子上下颠簸,一如风浪中的小船起伏不定。
晨曦将他家的院子落打回原形时,王彩娥的早饭也做好了,她知道朱满才还没起来,就从粮库里取了些袋子整理起来。这些蛇皮袋子大多是装过化肥的,化肥撒在地里,袋子就成了空的,这时候,王彩娥就一个一个地收了起来用水洗净,搭在铁丝上晾干,最后,卷起来放进仓库等着装粮食。她很细心,先把一些新的和比较新的挑出来铺在地上,用手把四角捋平,然后,再把那些烂了角的,有洞眼的放在另一边,准备用布头打个补丁。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心眼少,性子直,对家庭极度真诚,始终如一。她从不多想,也不知道啥叫委屈,和朱满才结婚二十多年,一日三餐顿顿做饭,每次做饭前她几乎都要征求朱满才的意见。朱满才说吃什么,她就做什么,朱满才不吃什么,她就不做什么。从不自行做主,更不为自己考虑,她不停地变换花样,不停地提高自己的烹饪技能。有一次,朱满才的嘴馋了,想吃羊肉饺子,王彩娥骑车子专门跑到县城里割了一次羊肉,不料,在回家的途中遇上暴雨,被浇成了落汤鸡,但她没有抱怨,只说自己的运气不好。
而朱满才对王彩娥从来没有关心过,他除了关心自己、关心诗,别的都不关心。那些被他吹得和气球一样的稿费没有一分钱用在家里,也没有花在王彩娥身上,而王彩娥却把自己种粮食、卖苹果的钱都存在家里的银行卡上。村里的好多人家搬城里住了,没有搬的也把房子翻新了,而朱满才家的房子还是二十年前的老样子,不算结婚那回,一次涂料也没刷过,一件家具也没添过,就这样,他们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迎送着岁月的朝朝暮暮。
初秋的一天,王彩娥骑着三轮车去县城卖苹果,正好遇见了县文化馆的李馆长。李馆长开玩笑说:“彩娥呀,你不要顾着挣钱、有时间也把自己打扮打扮,不然朱诗人就看不上你了。”王彩娥虽然嘿嘿笑,但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
买完苹果,王彩娥找了一家澡堂子,把自己塞进去水里泡了两个小时。她一边泡一边用手搓,经过反复泡、反复搓,王彩娥的皮肤一下子白净了许多,脸上也重新有了光亮。晚上回到家里,朱满才瞪着弹丸一样眼睛,探照灯般地把王彩娥审视了一遍,突然,眼眼睛变成了一条直线,不等王彩娥坐稳,就将她按倒在了床上。那一夜,王彩娥不明白朱满才哪来的劲儿,骑在她身上折腾了三次。更让王彩娥意外的是,第二天,朱满才竟然没问她要钱。
四
县文化馆召开“金秋诗会”,朱满才应邀参加。会上,朱满才尽管用一口醋熘普通话朗诵了自己的诗作,还是赢得了阵阵掌声。
“朱老师,您的诗写得太好了。”身旁的一位朋友竖起拇指说。
“谢谢!”朱满才说。
“像您这样有才华的人,放在咱这里太可惜了!”
“哈哈,瞧你说的,老天爷把咱生在了这里,不在这里还能到哪里去?”
“以您的水平,要是放在北京、上海、广州那些大城市早都出名了。”
“是吗?”
“是,大城市太需要像您这样的人才了,如果您去了一定会大展宏图,光芒四射。”
“不可能吧?”
“不瞒您说,我的一位同学在广州搞影视剧创作,一年要挣这个数哩。”朋友向朱满才伸出了三个指头。
“三十万?”
“不是三十万,是三百万!”
朱满才心里颤了一下。
“我读过您的诗,你的水平不在我朋友之下,只是咱们这个地方太小了,白白把你埋没了。”
“谢谢你!”朱满才心里热了起来,他挠了挠头,窘迫地问道,“咱在大城市人生地不熟,恐怕不行!”
“您想多了,大城市不是咱这个小县城,干啥都要凭关系,那地方凭的是才能,靠的是实力,只要你是人才,到处抢着要。”
朱满才豁亮了。诗会一结束,他迫不及待地回到家里,把自己想去大城市的想法给王彩娥说了一遍。
“想去就去吧。”王彩娥淡淡地说。
“这么说,你支持我?”朱满才感觉意外。
“支持咋,不支持又咋?你想干的事情我啥时候拦过你,再说了,这么多年你在家里搞创作,也没见搞出个啥名堂,天天还要让我伺候,你不在了,我还能清闲一点儿。”王彩娥说。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那天晚上,朱满才坐在朱家滩的村头,一只手夹着烟,一只手撑着自己的下巴,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忽然发现自己的村子太荒凉,太偏僻了,一点儿也不像人待的地方,更不是诗人待的地方,他怎么也想不通,他的娘怎么会把他生在这么一个穷山恶水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