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叙事视域下的《烟火漫卷》
作者: 许雨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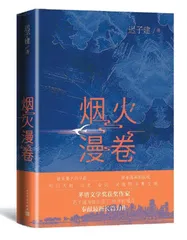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城市日渐成为作家迟子建想象和建构的对象。《烟火漫卷》是一部聚焦当下都市百姓生活的长篇小说,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景观与小说人物复杂的命运交相辉映,冰雪城市中独具的空间结构与元素不仅承担着人物活动的配景,而且还与人物情欲、权柄相互交融。本文基于龙迪勇空间叙事学理论中的故事空间、形式空间、心理空间方面相关理论,对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进行分析,力求探寻空间叙事背后文本的深层内涵及美学价值。
关键词:《烟火漫卷》;故事空间;形式空间;心理空间
20世纪初,巴赫金在其理论中提到“时空体”,这是叙事学空间转向的发轫,而后美国文学批评家约瑟夫·弗兰克在《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中打破叙事学时间的“顺序性”,这一革新引起学者对文学中空间形式的关注,这是叙事学空间转向的重要发展期。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将空间与人的主观感受联系起来考察叙事中的空间,认为空间不仅是一种客观外在现实,而且也应作为人的一种主观存在方式,无疑大大拓宽了研究范围,为叙事学空间转向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梅洛·庞蒂、詹姆斯等人也对叙事学空间转向有所发展,这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国内学者包亚明、张世君、龙迪勇是对叙事学的空间转向研究较为深入的学者,其中龙迪勇的《空间叙事学》为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空间叙事学理论专著,凡此种种皆为文本分析注入了鲜活的生命力。《烟火漫卷》为北国精灵迟子建的长篇力作,其中充实与丰盈的空间元素,可谓是对空间叙事理论的精彩演绎。
一、《烟火漫卷》中的物理空间
故事空间归于文本内容层面,更是叙事作品中具体的物理空间。龙迪勇认为:“所谓故事空间,就是叙事作品中写到的那种物理空间(如一幢老房子、一条繁华的街道、一座哥特式的城堡等),其实也就是故事发生的场所或地点。”物理空间在小说中不只是单单一个街道、一个庭院,它背后更是承载着相应的叙事功能,从而增加作品的厚重感。《烟火漫卷》中,哈尔滨是宏大的物理空间,七码头、榆樱院则是相对微观的空间,在这种大与小的叠套与对比中,展现着普通人的精神面貌与生态,诉说着普通人生存的困窘与挣扎。
具体空间是群体或个体思考活动的场所,即空间是人物的表征方式,叙事文本借此异质同构来展现叙事主题。《烟火漫卷》中对榆樱院有着大肆的描写,由三幢砖木结构的小楼合围而起,它的姿态很像一个内穿旗袍、外披斗篷的女郎,风格属于半中半西、半土半洋的。隐匿于大都市之中半新半旧的生活空间——榆樱院,它不只是哈尔滨元素的代表,更有较强的隐喻色彩,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处于乡土与都市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它似乎充当了弥合的中介,让人与城市、人与自我和人与人的关系得以缓解,但是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则是体现了“城市背后的疏离感”。在大秦和小米身上体现的正是“回不去的乡,容不下的城”,在榆樱院这一空间,虽然暂时有了他们的安置之所,但大秦和小米仍然是活在城市中的压抑者,是城市的流浪儿。他们受传统礼教的掌控,以孝为先,但是又不得不面对自身情欲,因此,他们心灵始终徘徊、犹豫。老刘居住于榆樱院是为了儿子小刘的梦想,想在二人转市场出头。小刘与胖丫这一对情侣有对传统的热爱但难抵现实的困窘,最终不得不分开。老郭头与小米婆婆的黄昏恋难敌儿女的阻挠。迟子建精心营造与构建榆樱院这一烟火气浓郁的生活空间,通过其中居住之人的生活遭遇来展现大城市背后内隐的残酷现实。
空间于普通人而言意味着匀质与广延,宗教徒则由某些空间的特殊性而赋予“圣”的意味,但在某些世俗空间中普通人也能体悟神圣空间的感召。七码头未经现代化的洗礼,包容一切的灵性,生活在此的人更是刻印上独属于七码头的特质。黄娥,美丽、淳朴,没有经受现代文明的洗礼,因此,在她的认知中带有许多“原始特性”,她本不是水性杨花的人,但是在送客途中她格外渴望男人的怀抱,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只是单纯的渴望,她所做的事情也并未瞒着她的丈夫卢木头,所以她不觉得这是丑事儿。在七码头这个灵性空间中,她所做的一切都是被包容的。而在此成长的杂拌儿更是野蛮生长的代表。黄娥对儿子杂拌儿说,在谢楚薇家里住可以看到松花江,“杂拌儿不以为然地说,他在七码头的山上,又不是没望见过水,城市的楼像一座座假山,在假山看水,哪有在真山看水好?”在七码头生活惯了的杂拌儿有着大自然一般的属性,他以水为友,以花鸟为伴。城市在杂拌儿的眼中似乎只是一个名词,他仍然深切地爱着他的七码头。虽然身在城市,但是在《烟火漫卷》中大多数人以“异乡人”存在于大都市中,他们的心灵无所依托,以至于在城市中始终是在流浪。
二、《烟火漫卷》的空间叙事结构
“文质彬彬”与“尽善尽美”是中国古典美学史上两个重要的命题,“质”与“文”的统一,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成功的小说对其内容层面是相当重视的,但叙事形式在小说中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形式空间在《空间叙事学》中是这样定义的:“叙事作品整体的结构安排(相当于绘画的构图),呈现为某种空间形式(中国套盒、圆圈、链条、橘瓣式),这是一种非线性结构的模式。”
萨特认为,“套盒式”的叙述是指作品中一个主要故事下也会派生出各种次要故事,如同大套盒里面装着小套盒一般,这个过程中各色人物逐一推向舞台的前方。[4]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说:“‘中国套盒’是一种故事里套故事——大故事里套着一个中故事,中故事里又套着一个小故事的小说结构方式,也称‘嵌套结构’或‘俄国玩偶’。”此种结构在《烟火漫卷》中有着清晰的展现。在主人公刘建国寻找自己年轻时在火车站丢失的好友的儿子铜锤这一主要故事背景下,引出了黄娥和杂拌儿,黄娥因为自己的丈夫失踪,所以带着儿子杂拌儿找刘建国认作爹,她认为刘建国缺孩子而杂拌儿缺爸爸,所以他俩该是一家;身为“爱心救护车”司机的刘建国结识了身患怪病的翁子安;妹妹刘骄华帮忙安排黄娥母子居住榆樱院,更在榆樱院各色人物中展现了在大城市下小人物的苦闷与温情。故事像套盒一样层层推进,有于大卫父母的爱情故事、妹妹刘骄华和出狱人员重建社会信誉的故事、雇主翁子安与其家庭的故事,还有刘建国犯下自己无法原谅的错误的故事、在榆樱院的黄昏恋、大哥刘光复与他的东北工业纪录片拍摄故事等。正是这种故事套故事的结构,给人以人像展览式的阅读体验,引出了黄娥、翁子安、于大卫等性格鲜明的人物,此种叙事缓解了读者阅读的疲惫感,更增添了叙事的故事感。“套盒式”叙事与“橘瓣式”叙事双重组合,推动文本形式空间的建构。
橘瓣是个形象的比喻,它表明并列的故事情节是向心的而不是离心的。龙迪勇是这样说的:“一个橘子由数目众多的瓣、水果的单个断片、薄片诸如此类的东西组成,它们都相互紧挨着(毗邻——莱辛的术语),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它们并不向外趋向于空间,而是趋向于中间,趋向于白色坚韧的茎……”《烟火漫卷》有恒久的主题,围绕“失”这一内隐的线索来叙事,让碎片情节统一融合。传统元素在《烟火漫卷》中频繁展现。刘骄华的丈夫老李是考古人员,执着于通过文物与古人对话,重焕历史容貌,对于现代文明丧葬,他有着自己的看法:“人人化为灰烬,墓穴没有随葬品,再过千万年,后人想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状况,除了从文献获取,从实物角度来讲,只能依赖房屋等其他遗址,传统的墓穴发掘所呈现给我们的灿烂文化,就此消失。”小刘酷爱二人转这一传统的表演方式,但事实是二人转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逐渐被人们遗忘。这种传统是历史遗迹的呈现,传统文明理应焕发出新的生机,但现代的快餐文化、图像阅读早已充斥人的生活空间。“德至”街的命名是为了抵抗洋名字的入侵,哈尔滨不少新开发的楼盘叫巴黎、伦敦、曼哈顿等,甚至连七码头这样偏远地方的杂货店都叫日内瓦,理发店叫波士顿,因此刘骄华的儿子小李给师大夜市命名为“德至”街。一方面是让出狱做生意的人牢记不能缺失道德,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品德与理想的追溯。主人公刘建国的“失”在文本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他的身份是“爱心救护车”的司机。走上这条道路的原因是早年他在火车站丢失了好友的孩子,而救护车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覆盖哈尔滨及周边地区,他希望通过救护别人来寻找丢失的“念想”。“人家回城是奔美好生活的,我呢是为了找孩子。说真的我年轻时,因为找铜锤无望,也没有女友,我也憎恨过小男孩,是他们让我过着备受煎熬的日子啊。”多年来,他孤身一人走在寻找铜锤的路上,失去了年轻时候的爱情,失去了稳定的工作,更甚一步他在寻找的过程中丢失了“自己”。“自于大卫告诉了他的身世遭遇,刘建国倒是彻底放下了寻找铜锤的念头,因为他活了大半辈子,竟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他对镜中的我感到陌生。”“对镜中的我感到陌生”这一细节的刻画极具象征意义。在刘建国怀疑并分裂自己主体性的这一时刻,他陷入了存在主义危机当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关系网,不知何者为我,我为何者。《烟火漫卷》在暗隐的线索之下塑造了一个“失”的空间,这种叙事方式让各个平行空间展现无法分离的巨大力量。
三、《烟火漫卷》的创作心理空间
龙迪勇在《空间叙事学》中认为:“所谓心理空间,就是作家在创作一部叙事作品时,其心理活动(如记忆、想象等)所呈现出来的某种空间特性。”作家在创作时最基本也最为重要的心理活动便是记忆,因此记忆对于文学作品的叙事会产生影响。鲁迅的笔下有他和他的鲁镇,老舍笔下有他和他的老北京,沈从文笔下有他和他的湘西,张爱玲笔下有她和她的上海,莫言笔下有他和他的高密东北乡。
作家的创作心理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创作伊始,作家的头脑中必然会有相应的文学空间场景。迟子建作为北国精灵,她的空间敏感性来源于她对家乡的记忆。迟子建在十七岁前的行迹就是围绕着连绵的大兴安岭,这片土地滋养着她的文字与审美趣味。“在埋葬着父辈眼泪的城市,我发现的是一颗露珠”,在《烟火漫卷》的后记《我们的塑胶跑道》中,迟子建如此写道,哈尔滨在她看来拥有着与父辈相关的浓厚记忆。这足以见得作家始终以故乡为其创作的始发点,《伪满洲国》《候鸟的勇敢》《额尔古纳河右岸》无一不是以其生活之地为创作的基础,在故乡这片“神圣空间”中汲取创作养料。迟子建对哈尔滨最初的认识源于父亲的讲述,最初她对于哈尔滨感觉自己更像是城市空间的一个过客,但是慢慢读城史后,她开始尝试在作品中建构它。正是对于哈尔滨的记忆,成为她创作的重要契机。《烟火漫卷》中的“爱心救护车”车主,她曾亲自做过采访,在她的故事中许多创作原型来自故土。《烟火漫卷》中也流露着独属于她的审美趣味,她偏爱格里格、西贝柳斯这些民族乐派大师,因此她塑造了有着浪漫气息的“谢普莲娜”,并借助哈尔滨独特的中西合并的音乐厅来进行演绎。《烟火漫卷》带有独属于她的故乡的空间特性,故而让这部小说在心理来源上呈现出某种空间特性。
四、结 语
叙事学的空间转向为探索小说文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途径,而作家迟子建笔下的城市转向更是一种“新乡土”的呈现方式。笔者以空间叙事学的理论分析迟子建的《烟火漫卷》,力求探寻作品中人物所内蕴的精神空间,展现时代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前途命运。这更是对现代性背景下的深刻反思,来探求新乡土叙事与传承优秀民族精神的新形式,为将来作家叙事提供新方法。
(喀什大学人文学院)
参考文献
[1] 迟子建.烟火漫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2] 熊家良.现代性视阈中的现代中国小城文学[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33-140.
[3] 达舍.公共空间[M].刘昶,何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
[4] 萨特.给青年小说家的信[M].赵德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5]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