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丝路文学之昌耀诗歌研究
作者: 李洪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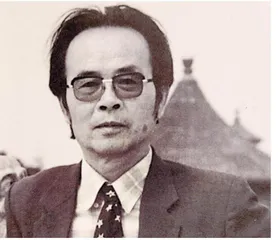
摘 要:中国当代诗人昌耀在青藏高原的地理环境下及西北丝路文化的熏陶下书写出诸多不朽诗作,文章运用文学地理学,从昌耀诗歌风格、意象谱系及“陌生化”的语言三方面解析丝路沿途文化、自然地理环境对其诗歌创作产生的影响,并结合具体诗篇,解析昌耀诗歌中的精神,力图深刻解析其诗歌特点以及成因。
关键词:丝路文学;昌耀;诗歌研究
丝绸之路是沟通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道路总称,分为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包括“西北丝绸之路”及“西南丝绸之路”。丝路文学就是以丝绸之路沿途地域文化景观为创作主体的文学作品。中国现当代西北丝路文学可根据创作主体的不同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作家生长于丝绸之路沿途地区,其作品多取材于丝路的历史及现实,如刘亮程、周涛、红柯等;第二类作家则出生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后因各种原因迁移到现代化都市,其创作兼具丝路历史记忆和现代文化洗礼的印记,如吴宓、王独清等;第三类作家生长于丝路区域以外,因多种历史原因来到西北地区并进行文学创作,如王蒙、张贤亮、昌耀等。本文以“西北丝绸之路”中国西北段为主要地域空间,以中国当代文坛著名诗人昌耀及其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昌耀的丝路文学情缘,探讨丝路沿途景观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研究其诗歌流露出的精神之美。
一、昌耀及其丝路情缘
昌耀出生于湖南桃源一旧式大家庭,新式教育的洗礼及父辈爱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使其终身保持着对国家及军队的热爱。1955年,昌耀在河北荣军学校完成高中教育后响应国家建设边疆的号召到达青海西宁。以其抵达青藏高原经受当地风物气息浸润为界,其人生大致可分为两段。在内地成长、求学及参军的经历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养料。童年时期家中大量的古典文学藏书、童谣、乡谚俚语等奠定了昌耀深厚的文学底蕴。公益性阅览室中的中外名著及在河北荣军学校系统性的学习都使其具备了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丰富的阅读经验及庞杂的知识体系都为日后昌耀进行诗歌创作提供了文学土壤,一经高原风土的浸染,其诗歌创作的灵感便迸发而出。
然而抵达西部两年后,昌耀就因诗作《林中试笛》而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荒原流放生涯。长期流放荒原的经历无意间加深了昌耀同青藏高原的血脉联系,诗人也从西部旷野的观察者转化为西部文化景观的在场者。随着昌耀对高原本地生活的融入,其诗歌意象也由原来的雄鹰、高原、群山等满足高原期待视野的普遍意象衍生为篝火、昆仑山、皮筏、哈拉库图山庄、金梧桐等更加具象化、地域性的意象群。对异域风情的切身体验是昌耀将鲜活的自然物象成功移植到诗歌创作中的关键,洪子诚也认为“昌耀诗的意象构成,一方面是高原的历史传说、神话,另一方面是实在的民俗生活事件和细节”[1]。结束流放生涯后,昌耀又以流浪诗人的身份行走于中国西北地区。沿着古丝绸之路的足迹,昌耀一路抵达新疆,于是其诗歌中便形成了“一个与青藏高原地理、历史连粘互补的亚高原系统”[2]。燎原指出,昌耀诗歌中的西部地区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其诗歌中对生活于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出使西域的汉使及敦煌歌舞的书写,都体现出了西部地区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并且极大地扩充了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异质性元素。
二、丝路沿途自然地理环境对昌耀诗歌的影响
(一)孕育昌耀诗歌的摇篮——青藏高原
自然地理环境会对文艺创作产生影响是中外文论史上一致认同的观点。法国的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就曾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可对文化艺术的发展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提出了“江山之助”的观点,他认为自然景物是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屈原认为诗歌情韵的体察也离不开自然山川的协助。由此可见,自然地理环境确实对文学创作的产生及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迈克·克朗在《文化地理学》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地理景观对民族聚居地区历史文化的传承及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及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3]昌耀曾被流放青藏高原腹地二十载,其诗歌中自然多高原风貌的书写。昌耀的流放之地属于祁连山,该地自古以来是青藏高原地区的文明发祥地。同时,河湟地区也是民族聚居的多元文化荟萃之地,是青海文化链条最完整的区域之一。汉、蒙、回、藏、土、撒拉等民族在此地有着悠久的文化发展史,因此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多元文化形态。祁连山地区因其温润的气候及山地地形而形成农牧混合区,该地区既有淳朴的农民,又有浪漫温情的牧民,属于诗人的乌托邦。
昌耀被高原风物所感染,又受到当地多民族历史文化的浸润,先后写出《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高车》《荒原》等诗篇。青海于昌耀是一个复杂情绪的集合体,一方面他因写诗而被流放青海多年,另一方面如昌耀本人所述:“青海最难能可贵的,就是给我的一生给予了许多极大的造就……青海的山河、人文地理、历史对我都有很大的影响。”[4]
(二)自然地理环境对昌耀诗歌的影响
首先,青藏高原及广大西部地区的人文、自然地理环境影响着诗人的创作风格。青海作为昌耀的第二故乡,这片土地上的历史、宗教文化因子早已浸透昌耀的骨血。高原雄浑、壮阔的自然地理景观给昌耀带来视觉的震撼及心灵的触动,祁连山、昆仑山、戈壁、雪峰、草原等意象都被诗人融入了雄浑、昂扬的情感。初到高原的昌耀因受异域景观的召唤而写出《鹰·雪·牧人》《高车》《边城》等诗作;80年代初,回归自由的诗人重新拾笔,先后写出《慈航》《山旅——对于山河、历史和人民的印象》《青藏高原的形体》等一系列对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深思的组诗;后又在重走古丝绸之路的旅程中写下《河西走廊古意》《在敦煌名胜地听驼铃寻唐梦》《旷原之野——西疆描述》等描写西部历史文化景观的不朽诗篇。总体而言,昌耀的诗歌在对广阔的丝路沿途地区进行文学书写的过程中呈现出景观的雄浑壮阔、语言的苍茫遒劲等特点,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昌耀体”。著名诗人王家新认为昌耀写作中形成的“孤绝超拔、沉雄遒劲,具有‘新古典’性质和青铜般色调的文体”[5]就是“昌耀体”。
其次,自然地理环境促成昌耀诗歌形成独特的意象谱系。意象是诗歌创作中的本体性因素,自古以来便是中外诗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于1953年开始进行诗歌创作的昌耀,其诗歌意象多选自朝鲜战场上的普通人。1955年昌耀到达青海后,其诗歌中开始出现雄浑奇崛的高原意象,如高原、冰山、黄河、牧人、少女、鹰、野羊、马刀等。在漫长的流放过程中,昌耀对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所以流放期间其诗歌意象群又进一步扩大。在出现篝火、岩原、黑河、要塞炮、红衣僧人、麦酒等自然意象的同时,还涌现出了大量的新生事物,如钢铁、土高炉、炼铁工人等。昌耀的诗歌“从更深更广处的时空交错中为高原形体造型,并更多地溶入了自己对这片神奇土地的文化历史神话传说民间世俗的深切体悟、尊敬与认同”[6]。1978年,昌耀在诗坛正式复出后,其诗歌意象开始涉及高原的民俗、历史、宗教、文化等多方面,随着诗人足迹的拓展,还出现古本尖桥、铜色河、兵马俑等历史文化意象。昌耀诗歌的意象群在其抵达青藏高原后,随着他人生经历的丰富及足迹范围的扩大也逐渐延展。昌耀终其一生用气势恢宏的笔调塑造出一个苍茫辽阔、充满原始生命力的西部大高原形象。
最后,自然地理环境孕育下的异域文化又形成了昌耀诗歌语言“陌生化”的特质。学界公认昌耀诗歌语言具有“古语化”特点,骆一禾和张玞二人最早于1985年提出这一观点。西川认为昌耀之所以偏离主流诗坛,原因有二:其一是昌耀“早年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影响;其二是“他长期以来身居西北高原的闭塞之地,没有太多机会‘追上翻译的速度’(多多语),广泛接触西方现代诗歌”[7],因此间接造成了昌耀诗歌的“古语化”。昌耀诗歌“古语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诗歌创作中吸收了青海民歌与方言,二是语言中蕴含着浓厚的民间文化气息。燎原就曾评价其诗歌语言“是一种独属于高原生态场的,杂糅着浓重异质异族色彩的语言物象……这种语言文体,承袭了高原民族艰难生活中的那种心理滞涩……以洪荒感、酷烈感、狞厉感,以及荒旷、粗悍中的风霜感,从本质上映现出他之不愿获得现代心灵安慰,也决不与世俗生存认同的精神姿态”[8]。如《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中“咕得尔咕,拉风匣,锅里煮了个羊肋巴,房上站着个尕没牙”[9]等诗句,诗人就吸收了青海方言中对羊排、老年男子的描写,其中风匣是西北农村地区烧火做饭的工具,而“土伯特”则是历史上对藏族的音译。以上元素的组合使用,体现出诗人语言深奥生涩的特点,也造成了诗歌“陌生化”的语言效果。《哈拉库图》一诗中反复出现的“憨墩墩”是西北人对小儿表示亲昵的称呼,而“深着”是带有程度副词的形容词,表达情感极为深挚。昌耀利用土著文化元素加深了其诗歌的晦涩感,又用特定的语言传达出他眼中的西部风景。
三、昌耀诗歌中的精神之美
罗马帝国时期文艺批评家朗吉弩斯在其著作《论崇高》中曾说“崇高是高尚心灵的回声”[10],创作者高尚的思想是构成崇高艺术的关键。昌耀借助诗歌,将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书写为一种崇高的艺术,进而传达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如果说沈从文的文学神庙中供奉的是人性,那么昌耀的诗歌世界中供奉的便是崇高,其一生都在追求崇高的诗歌。他认为“诗是崇高的追求……诗,可为殉道者的宗教”[11]。其诗作《高车》《慈航》《划呀,划呀,父亲们》都传达出一种对崇高精神的不懈追求。昌耀认为,人的生命历程多是充满苦难的,面对这种宿命论式的悲剧,人能做的只有勇往直前。昌耀将自我的诗作评价为“就像在同一条船上和激流搏斗一样……痛苦是绝对的,但是斗争也是绝对的(所谓斗争,是向命运的斗争)。这种精神便是一种崇高的精神”[12]。博克认为,崇高是主体在克服恐惧心理及痛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心理快感。由此可见,富含崇高美的文艺作品是创作主体遭受某种困境并从中超脱出来的精神产物。昌耀有着崇高的文学创作追求,他认为:“诗人当是以生命为文、以血之蒸馏为诗的,非如此不足以聘其文、明其志、尽其兴。”[13]正是在这种不追名逐利、不以世俗审美为标准的崇高精神驱使下,昌耀才创作出了不朽的篇章。
崇高作为一种庄严、宏大的美,往往与强大的力量、雄壮的气魄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作品中往往体现为戈壁、沙漠、雪山与大河等意象。康德认为能引起崇高感的事物首先表现为数量上的无限大。如《峨日朵雪峰之侧》中“引力无穷”意味着雪山规模的庞大,雪峰气势磅礴,而雪峰攀登者的形象是对自然的征服,也是作者面对命运捉弄进行不懈抗争的隐喻,诗歌蕴含着一种悲壮美及崇高精神。此外,引起崇高感的事物还具有力量美的特征。昌耀诗歌中反复出现雄鹰、野牛等极富力量感的意象,诗人通过这些事物传达出一种力量感。雄鹰以双翅在高空中盘旋的姿势震慑着一切事物,具有一种大气磅礴之感,从而传达出崇高美。《一百头雄牛》中,诗人从雄牛极具攻击力的犄角出发表现出其形体的威猛,也展现了雄牛身上的力量感,从而形成崇高美的意象。
昌耀诗歌的另一精神特点是英雄主义。学者路文忠指出:英雄主义是以社会为己任的英雄承担艰巨任务时,所体现出的英勇行为及献身精神。不同于集体层面英雄主义的概念,李岳峰认为,个人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同一切阻碍个人发展的力量作斗争也是英雄主义精神的表现。综观昌耀诗歌创作生涯,其诗歌从不同侧面均体现出英雄主义精神。1950-1960年,在当时文艺政策的影响下,昌耀先后创作的《轨道》《哈拉库图人与钢铁》等诗歌充分展现出自身对国家及集体建设成果的认可,诗人集中塑造出一批充满集体主义精神的英雄群像。1980年前后,历经二十年流放生活的昌耀将创作目标从外在事物转向自我精神世界。这一时期昌耀的诗歌创作中多塑造出为理想、光明而勇于献身的个人英雄形象,如《大山的囚徒》《雕塑》两首诗歌中便塑造出为寻求真相而不畏权势的囚徒形象,以及为追求人类光明而奔走的先驱者形象。由此可见,昌耀的诗歌创作一直在致力于塑造英雄主义精神,只是这一精神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
四、结 语
昌耀的诗歌作为西北丝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深受西北自然、文化地理环境影响,形成了景观描摹雄浑壮阔、语言书写苍茫遒劲的“昌耀体”。具体而言,因诗人长期受到西北风土人情的影响而形成了独特的“大高原”意象谱系,又因吸收了青藏高原本土民歌谣谚及方言俚语而产生语言的“陌生化”效果。独特的意象谱系及晦涩深奥的诗歌语言共同传达出其诗歌中蕴含的崇高精神及英雄主义精神,诗人也因此傲视中国当代诗坛。
(新疆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7.
[2] 燎原.高原精神的还原[J].诗探索,1997(1):72-84.
[3] 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4] 昌耀.昌耀诗文总集[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
[5] 同[4].
[6] 同[3].
[7] 西川.昌耀诗的相反相成和两个偏离[J].青海湖文学月刊,2010(3):43-49.
[8] 同[4].
[9] 昌耀.昌耀的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165-166.
[10] 朗吉弩斯.美学三论:论崇高·论诗学·论诗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15.
[11] 同[4].
[12] 同[4].
[13] 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