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里再录
作者: 石舒清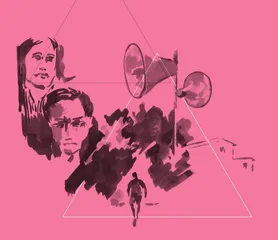
小 韩
在 公安局工作了一辈子的堂叔多年前讲过一个故事,当时听过也就听过了,毕竟是别人的事情,今日和父亲闲聊,得知堂叔退休已经大半年了。我就想起堂叔讲过的这个往事来,把它记在下面。
堂叔说,那时候,还时兴顶替制,好比一个公职人员退休了,他的子女中的一个就可以顶替他有一份工作。我岳父在县印刷厂工作,退休时我老婆才十六岁,就顶替岳父有了一份工作,所以现在岳父说老婆沾了他的光时,老婆也会说,我要不是顶替你当排字工人,现在说不定我有着更好的一份工作。这都是说不准的。生活总是它本来就有的样子,是不能假设的。堂叔说,那时候他进入公安局时间不长,公安局局长到龄要退休了,根据政策,就让他的小儿子顶替他到公安局有了一份工作。局长姓韩,韩局长,他的儿子大家都叫他小韩,当时最多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完全不像是局长家里出来的孩子,人很好,很有眼色,勤快,倒好像是穷苦人家出来的孩子。年龄大的,他喊叔;年轻些的(再年轻也年轻不过他),就叫哥。女的则不分年龄大小,一律喊姐;年纪长一些的,就在姐前面加一个“大”字,叫大姐。如此种种。大家都喜欢这小伙子。刚来的时候,小韩没有什么具体的工作,哪里有事需要人手他就到哪里,给办公室打水扫地送报刊书信等,也都干过。这样子过了大概有半年,小伙子个头又蹿了一小截,就让他背着枪去看守所站岗了。听说新局长把小韩特意叫到办公室,让他不要再打水送报刊了,专门有干这些的人呢。即使老局长让你这样,我也不能让你这样是不是?说了几样工作让小韩选,小韩就选了去看守所看守犯人,这样可以有枪背着啊。小韩见人是爱笑的,一笑显得很坦诚很有朝气。其实大家是喜欢看这小伙子笑的,小韩一笑,就好像窗帘拉开进来了一些阳光似的。就有人告诫小韩,去了看守所看守犯人,可不能就这样子笑了。这好像是不必叮嘱的,起码的分别心总是有的。小韩在看守所两年,每年都会得到局里的表扬甚至表彰。这当然和老局长的面子有关,但熟悉小韩的都知道,小韩得到大家的认同和赞誉,可以说和他有这么个父亲有关,也可以说毫无关系。最有可能的一点是,因为小韩出自这样一个家庭,还能如此低调上进,更容易被大家看在眼里,更容易让大家感慨,也更愿意把他应得的评价和荣誉给他。要是换一个家庭,小韩这样的表现,至少大家的感受没有这么强烈,评价也难得如此一致。局里的会计田凤兰,早就把小韩看在眼里了,说她的两个女儿,让小韩选,选上哪个她给哪个,只要小韩当她的女婿就行了。小韩也没有什么不良习惯,比如抽烟喝酒等,小韩都没有的。田凤兰自己就抽烟。有人就给田凤兰说,你一个丈母娘抽烟,怕是小韩看上你女儿,也看不上你这个丈母娘。田凤兰说,他娃只要当我的女婿,烟我可以多抽的少抽,少抽的不抽啊。但就是这样一个小韩,却是栽在了一个女人手里,栽在了一个女犯人手里。那时候小韩到公安局还不到三年。谁也想不到小韩会出事,直到小韩真出了事,大家还有些纳闷,觉得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需要再调查核实一番。但世上什么事不会发生呢?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那女犯人三十左右,犯的事是把她丈夫头一个老婆生的孩子杀了。所谓杀了也并不是采取了多么可怕的手段,而是趁着那孩子生病要吃药,她给喂药的时候喂错了药,这样前妻生的孩子就给药死了。她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据说这样她的丈夫就可以一心在她和丈夫生的女儿身上,不至于一颗心分作两处。大致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传言。说明这女犯人找的是一个二婚男人,从中还可以得到的信息是,二婚男人和前妻有一个孩子,男孩,和女犯人婚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就是这样的一个家庭构成。据说他们的女儿也四岁左右了,说明女犯人婚后在这个新组合的家里已经过了好几年日子了。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她却心念一动,把那个孩子除掉了。这和小韩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这女人长得好看,尤其是很有手段,她看准了小韩这小伙子可以被她俘虏过来,于是就用了心思用了手段,慢慢地和小韩有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拉小韩的手摸她,直接就把小韩吻得让他喘不过来气。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她就让小韩给她提供纸笔说她要写信,让小韩偷偷从外面给她买烧鸡巧克力等。小韩糊里糊涂就被她勾引了,就按她说的做了,把她写的信偷偷送给了女犯人的母亲。后来一次,女犯人写了厚厚一封信让小韩送给她母亲时,小韩忽然不想这么干了。小韩觉得不能这样子下去了,再这样子下去,不但自己会被弄得不成样子,他老子的一张老脸也会让他搞丢了。即使很爱笑的小韩在女犯人面前也笑不出了。女犯人说你不听我的可以,你不听我的我就把你我的事捅出去,你知法犯法,可有你好受的。小韩把那封信在自己家里藏了好几天,才心惊胆战把信送给了女犯人的母亲。小韩也和女犯人做了约定,这是最后一次送信了。这次送过,说什么也不会再送了。小韩对那女犯人提了两点要求:一、这绝对是最后一次送信,要把这一点说定说死;二、既然他答应女人这次还给她送信,那么女人就要答应,把他们两个的事烂在肚子里,无论如何也不能说出去,这一点也要说定说死。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他才可以去送信。女犯人答应了小韩,并且说我给你说着耍呢,这么长时间了,我问你姓啥叫啥了吗?我连你的姓名都不知道,我咋会把你我的事捅出去呢?女犯人说她不自量力异想天开,爱上小韩了,在小韩面前一边笑着一边泪如雨下。小韩给她说得懵懵懂懂云里雾里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去给她送了这封信吧。事情该有一个了结了。小韩打算,送过这封信后,他就到局长那里走个后门,让给他调一个工作,好离开这是非之地。但就是这封信出了问题。女犯人不知在信中说了什么,很快就传来了女犯人母亲自杀的消息。信虽然是小韩送出去的,但小韩并不知悉信的内容。一来拆人的信不好;二来小韩也多了个心眼,他只是负责送信,却不看信的内容,这样就不算是与女犯人合伙共谋了。女犯人还问过小韩看过她的信没有,而且断定小韩一定看过,而且她也允许小韩看,既然委托小韩送信,这份信任应该是有的。小韩赌咒发誓说他没有看。女犯人就踮着脚尖一场好吻,眼泪把他们两个的脸都打湿了。后来在女犯人母亲的遗体上搜出一封信来,信是女犯人的母亲写的,算是她的遗书。女犯人的母亲是上吊死的,她的遗书就在她上吊时所穿衣服的口袋里。女犯人的母亲在遗书里说,请大家行行好开开眼,那个小娃娃不是她女儿药死的,是她药死的。女儿找的这个女婿虽然是个二婚,但各方面还行。尤其去年,女婿女儿还把寡居的她接到一起过,她应该知恩图报才好。结果她昏了头,想了这么一个歪招,把女婿害了不说,还把女儿搞到了这一步。女犯人母亲的上吊和遗书,让案情变得复杂起来。
使案情大白的正是女犯人写给母亲的那几封信。出事后,女犯人的母亲自然是不能再住在女婿家了,她回到了老家的老屋。从老屋里翻出了那几封信,已经被烧毁了,但信封没有被完全烧毁,从残余信封可以看得出,这竟然是公安局的公用信封,显示出一种明显的指向和线索。就对女犯人说,你写给你母亲的几封信都在我们手里,就看你自己给不给你自己机会了。事情到这一地步,女犯人也就不再隐瞒,一切就都痛痛快快招了。原来她只是写信让母亲把外孙女从丈夫那里接过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她对丈夫已经不能放心了,就想女儿跟着丈夫,远没有跟着母亲让自己放心。但母亲读信后却有了替她顶罪的意思,让女儿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在她这个当妈的身上,这样女儿就可以出来自己带她的女儿了,这样不是更好吗?万想不到为了促成这事,做母亲的竟然会做出一个这样的选择。这都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其中种种的亲情关系和利害权衡。
堂叔说,女犯人得到自己的最终判决时,木呆呆站着,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站在她一边的小韩因渎职罪被判刑三年。和面无表情的女犯人相比,小韩显得情绪激动,流下了悔恨的泪水。
《黑三角》
我上小学的时候,小学有初小完小之分。初小就在我们自然村。所谓初小,是说我们学校只设小学一、二、三年级,读完初小,还想再读,在我们村里是读不成的,得到完小去读。所谓完小,就是完全小学,除了一二三年级,还有四五年级,我们村里是没有的,要读完小,得去大队读。大队距离我们村有六七华里远,那时候觉得这点距离是很遥远的了。有些读完初小的同学,就因为这点距离,就辍学不再读。倒不是因为娇气,而是家长借着这个理由,不让孩子再读书,让辍学挣工分或帮家里干活了。一个理由往往会产生很多个结果。只要有理由,什么结果都是会产生的。同因异果的事真是太多了。当时我村去大队小学继续读书的娃娃有七八个,女生一个也没有。每天早晨星星还没有落净,我们就出发了,之间要过一个小村庄,还要过一个海原大地震时造成的凶险的深沟,才能到张湾村,也就是大队小学所在地。相较于村里的初小,完小是大多了,排场多了。大概有近十亩大小,有操场,还有树林。学生近百人。有一个自然村系汉族村。大队有五个自然村,四个回族村,一个汉族村。汉族学生给我们的感觉是有些不很一样的,首先是口音有细微的区别,另外感觉是要更深沉些,更洋气些——说得未必准,语言是不够用的。总之就是觉得有些不一样。相较于回族学生,他们的学习也要更踏实些。有一个姓杜的女生,格外显得洋气,她做操弯腰的时候,让我看到了她是穿秋裤的,蓝色的裤子边上露出红色的秋裤颜色来,给我留下了可以记一辈子的印象。我们那时候一律是没有秋裤的,我们只有单裤或棉裤。
我在完小念了一年半的书。五年级后半年,父亲托在城里教书的堂伯父,把我转到县城一小去读书了。其实我村距离县城较大队要更近些。但县城小学那时候只招收县城里的学生,乡下学生是不招收的。虽然我村就在城外三华里处,但毕竟不在城内,也算乡下,所以我那时候是规规矩矩自自觉觉去大队小学读书,根本不曾想到县城的小学和我有什么关系。托了堂伯父的福,使我在小学阶段的最末一个学期,得以到县城一小上学。这在我村的学生里,是独一份第一个。他们多么羡慕我可想而知。然而在大队小学的一年半时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记得学校的老师有七八个。除了家在张湾的李存明老师外,其他老师都住校。校长姓赵,瘦高个,很干练,常常在我们早操后要讲几句话,直到今天他也是我心目中的大知识分子形象。唯一一个女老师姓许,也是唯一说普通话的老师。许老师外地人,我后来才知道她是安徽人,丈夫任县气象站站长。许老师个头不高,微胖,不漂亮,但是有独特的气质,就是一看就看出她是个知识分子,是个外地人。许老师当时给我们带自然课和音乐课,有一台风琴,缝纫机似的样子,也得像缝纫机那样得用脚踩动。许老师教我们什么歌子不记得了。但许老师踩着风琴弹奏风琴的样子我们是难以忘却的。那时候有一点点独特的异样的东西,就可以记一辈子。记得许老师脾气不好,打学生,说着话,就用手里的书本打一下学生的脸。大家最怕的是李存明老师,接下来就是许老师了。李存明老师和其他老师的身份不一样,他是民办老师。民办老师公办老师区别是非常大的。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这种区别,不知道这区别意味着什么。只是觉得李存明老师是全校最认真的老师,也是学生最怕的老师。李存明老师教数学,打学生,出手是很重的。我很喜欢李老师批改的作业,喜欢他写在作业后面的日期和“好”字,有时候在“好”字的右上角还写一个“+”,算是好上加好。那时候对这个“好上加好”简直是有些贪婪,好像由此带来的满足感是无法言喻不可替代的。我在张湾小学一年半,学习一直名列前茅,不然堂伯父也不会费周折把我弄到县一小去。李存明老师的家门前种着谷子麻子洋芋等,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们就去帮着李老师拔谷子拔麻子挖洋芋。记得李老师的妻子比李老师的个头要高一些,文文静静的样子,做黄米饭给我们吃。还有李老师大头大脑的儿子,那时候刚学会走路,总是显得兴冲冲的样子,跌跌撞撞往前跑,时刻都要跑空跌倒的样子。那时候有一种袋装药叫“小儿安”,李老师的儿子看起来像“小儿安”药袋上那个胖乎乎的小孩子。但是李老师的妻子早就去世了,李老师后来又续了弦。李老师的胖乎乎的儿子,据我父亲说,成年后在银川跑出租,不幸出了车祸。在银川工作的我竟然不知道这个事。这都让人感到在漫长的时间里总会发生一些事情,而且你不知道在这么多的时间里究竟会发生什么。
完小操场的边儿上有几棵杏树。我们那时候中午是不回家吃饭的,怕来不及,误了上课,学校也没有灶。我们一天实际上只能吃一顿晚饭,早晚都是吃自带着的干粮。中午,天热,我在杏树上坐着吃干粮,吃完干粮就倒吊在杏树上,看操场上的人影,看极远处的校门像在张嘴打哈欠。记得一次我倒吊在杏树上时,许老师从她的宿舍里出来倒水,看到我,喊了一声。我腰里一用力,就翻身上去藏在杏树里了。学校那时候还号召我们打苍蝇,死苍蝇要数数,这样说来应该是有任务的。我们把死苍蝇装满空火柴盒交上去。主要是在厕所里打苍蝇。记得围墙围起来的露天厕所里,天热得人要虚脱,苍蝇在强光里几乎看不清楚。在强烈的日照下,厕所里的味道熏得人昏昏沉沉的,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们打死了很多苍蝇,上交了很多火柴盒。不知那些装满死苍蝇的火柴盒后来都是怎样地处理了。我们用蝇拍拍死苍蝇。哪里来的蝇拍?应该是学校发我们的吧,记不清了。还打老鼠。也是需要上交,四个老鼠腿算一只老鼠。不用交老鼠,交老鼠腿就可以了。我们把老鼠腿四个一捆四个一捆那样交上去。记得到处都是被踩破的老鼠肚子,主要集中在教室后面的树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