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书法
作者: 顾明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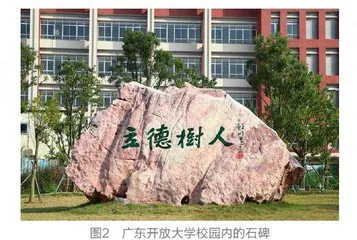
我们小时候上学以后就要开始学写毛笔字,那时钢笔是稀有的工具。学写字从描红开始,即在红色字帖的练习本上,用墨笔把红字描黑。记得练习本上最前面一行是“上大人孔乙己”几个字。鲁迅的小说《孔乙己》,主人翁的名字即取于此,是为了避免某些人用姓名对号入座,选了这三个字。此是后话。当时描红,不是把红字简单涂黑,而是学习横、竖、点、撇、钩、捺等基本笔法。在小学,每天都有书法课,都是在上学科课之前半小时。一年级描红完了,改用米字练习本,写一千“永”字,练习字的结构。后来启功先生告诉我,练习时用井字格更好。的确,写双体字,用井字格更能掌握字的结构。寒暑假的作业也要求每天写一张大楷,几行小楷。到高年级就开始临帖了。当时有两种帖,一种是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另一种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我比较喜欢柳体,清秀一些。到初中,我们根据自己的爱好,就开始选帖临帖了。当时,我们班上有好几位同学对书法有兴趣,有沈鹏、夏鹤龄、伊俊华、陈寿楠,我们经常在一起切磋讨论,评议各人的作品。这个时期可以说是书法打基础的时期。
到了高中,我们几个同学成立了曙光文艺社,办起了壁报。壁报,即把两张道林纸(报纸)拼起来,在上面编写报道文章,然后钉在墙壁上。为了编壁报,做美编,我就学起硬笔字和美术字体来。后来又办油印报纸,刻钢板蜡纸,也是要用硬笔字。毛笔书法反而练得少了。没有想到,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办起了《师大青年》板报,用上美术字体和硬笔字,还常常用艺术字体去刷宣传品。在苏联学习五年,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写书法了,但逢年过节,我们会出一些介绍中国的墙报,这个任务也常常落在我身上。
直到1962年秋天,我从北师大附中调回北师大后,每天早晨开始临帖。中学年代学的是柳体,这次改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柳体的笔法是圆笔,欧体的笔法是方笔,两者笔法不同。我临了一阵感觉自己写的字四不像了,又重新回到柳体,但现在写的字里也还有欧体的影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工作比较繁忙,就顾不上练书法了。直到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以后,有些学校希望我题几个字,重新捡起毛笔来,但觉得自己书法退步了,荒芜了。这才开始又临起帖来。这次不是临那种字帖,而是临各种版本的《兰亭序》,以及读各种字帖。
我觉得学书法不能只临一种帖,读帖很重要。读帖可以见识历代各家的书法,体悟各派书法的风格神韵,感受中国汉字之美,逐渐形成自己书法的特点。近些年,我读了一些法帖,如《淳化阁帖》《戏鱼堂帖》《米南宫十七帖》《拟山园帖》,以及《赵孟頫小楷道德经真迹》《岳少保书武侯出师二表》等。我非常喜欢《初拓墨池堂法帖》。这部法帖共五卷,收录有王羲之、王献之、黄庭坚、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赵孟頫等历代书法大师的名帖。我特别喜欢苏轼的字,豁达明快,气势恢宏。第四卷中有苏轼的《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一首、画记、陶诗二首。他不仅字写得好,而且对画有精辟的评论。画记一文中论画的观点,很适用于书法。他说,画“虽无常形,而有常理”,有些画“虽然,常形之失,止于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当,则举废之矣”。也就是说,画的内容不仅要形态相当,更要重视画的内涵意蕴;画得不太好还可原谅,没有内涵意蕴就不可取了。他还批评一些欺世盗名的人,“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于无常形者也”。这种批评很适合当今书法界的一些乱象。有些“书法家”,基本功没有打好,就写起奇奇怪怪的字体来,美其名曰创新。我认为,不论正草隶篆什么体,都需要先练好基本功,基本功扎实了才能创造书法之美。
我不是书法家,而是书法爱好者。《兰亭序》临了几十遍,总觉得写得不好,也就是没有掌握《兰亭序》的神韵。因为我是一名教师,常常读《学记》《师说》,因此,近年就用小楷抄写我国古代的两篇名著,作为书法基本功的练习。
在练习书法,特别是读帖过程中,深深感到,书法是我国独有的艺术形态,它不只是一种文字的写法,而是包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用文字美的形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最近,我读了古吴轩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晴山堂法帖》,共六册。内容是徐霞客为庆贺母亲八十大寿时,将其直系先世所得的时代书法墨宝,勒之于石,列之于晴山堂。法帖收录了明代宋广、宋克、沈度、文徵明、祝允明、董其昌、米万钟、张瑞图等八十多位书法家的作品。其中许多书法是歌颂徐本中弃功归里、施善乡里和徐母晨机日耕、养育子孙,支持徐霞客云游四海的事迹,蕴含着深厚的教育意义。《岳少保书武侯出师二表》更是充满浩气激情、爱国精神,催人奋进。读帖不仅能提高书法水平,更能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