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德树人”视域下劳动教育再审思
作者: 王莹 王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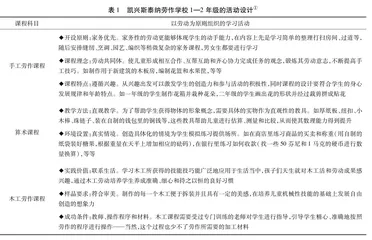
摘 要: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是在20世纪初德国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凯兴斯泰纳较早地意识到德国教育的顽疾和公民教育的薄弱,逐步形成了劳作教育思想体系。凯兴斯泰纳提倡重新发掘人的价值,通过劳作实现公民教育的目的,即要培养与“个体人”相对应的“国家人”。他认为,劳作学校的教育目的是以德为本、性格塑造,课程结构是在做中教、从做中学,教育模式是以生为本、以导为方。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理论为新兴的德国指明了一条人才培养之路——通过劳作教育塑造国家共同体意识,明确劳动教育的育人价值,可为我国完善劳动育人体系提供借鉴与思考。
关键词:劳动教育;凯兴斯泰纳;劳作学校
中图分类号:G40-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5-0080-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5.012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了劳动教育的重要意义;同年7月,教育部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该项《意见》,制定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1]。《意见》明确了构建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的重要性,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劳动的教育价值。这也是很多世界著名教育家的共同理念——倡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积极探索劳动教育的实践模式。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教育家即为凯兴斯泰纳(Georg Kerschensteiner,1854—1932)。他的劳作教育思想及其创办的“劳作学校”(Arbeitsschule)是德国教育界首次通过劳动教育来培养一代新人的尝试。凯兴斯泰纳认为,公民教育、职业教育与劳作学校之间是目的、手段与机构的关系,三者高度统一,三位一体。为了实现公民教育的目的,从小就要对公民进行职业训练,使他们具备为未来生活作准备的职业技能,而劳作学校为职业技能的训练提供了必要的场所,在共同的劳作中又培养了学生的集体意识和为国家服务的精神。凯氏的劳作教育思想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和实践遗产,在我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背景下,教育不仅要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还要密切关注通过劳动教育使人在劳动素养和精神品格上受到的陶冶。
一、劳作教育思想产生之历史背景
德国思想界人才辈出,在其近代历史发展中,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造就了一大批对人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家,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就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1.复杂的政治背景孕育劳作教育思想萌芽
德意志地区长期封建割据的状态导致近代以来国家缺乏凝聚力和向心力。18世纪,迟到已久的启蒙运动才开始在德国崭露头角。德意志启蒙运动之父克里斯蒂安·托马西乌斯开风气之先河,率先在高校中不再使用拉丁语,而改用民族语言——德语授课。此举促进了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得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德意志民族开始关注德意志地区分裂的状况,但直到1871年,经历了三次王朝战争之后,统一的德意志国家才得以建立。俾斯麦主导下的“小德意志”国家战略使新德国的民众具有强烈的民族情结,但也使德国的排外性和封闭性日益增强。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础是基于同宗同族的血缘关系,而非建立政治制度上的文化认同。到了20世纪初,“德意志”血统的光辉由于战争失败而逐渐褪去,但新的国民共同体情感的建立仍然一片渺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百废待兴的德国国情催生了强调“国家认同感”的政治教育,劳作教育思想是其关键组成部分。1918年,魏玛共和国建立,这是德国的第一次民主尝试,但新国家困难重重,内忧外患交织:一方面,要解决帝国时期所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德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遭受严重损失。此时的德国在政治上委曲求全,经济上百废待兴,而在精神和文化上尚缺乏新的统一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由于新生的共和国不仅缺乏民主体制下的国家共同体意识,还缺乏民主政治文化[2],使得这一时期的德国教育必须要重视“国家和民族”精神。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凯兴斯泰纳提出,教育要为国家服务,要对民众进行具有民族性与民主性相统一的公民教育,增强国家的共同体意识,使魏玛共和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
2.社会时代的变革为新思想发展提供契机
18世纪初,自然科学迅猛发展,将科学技术转换为生产力,使得更多的实用技术开始与经济相结合,将科学引入到工业生产领域。也正因为如此,具有专门生产技能的新型劳动者成为工业发展的亟需。但此时的德国教育界显然是滞后的,深受欧洲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德国教育体系仍然以教师、书本和课堂为主导,侧重于传统理论学科,并未将实用性的技能作为人才培养的方向,无法满足工业经济的发展需求。在经济领域,德国作为后起之秀可谓突飞猛进,从19世纪末德国完成统一之后,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次工业革命重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德国快速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才应运而生。
在思想领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开始逐渐增强,导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有效缓解矛盾,就必须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工人的公民意识,即必须热衷于国家事务,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为社会无私奉献。为了能够实现公民教育的目的,凯兴斯泰纳积极创办劳作学校,进行劳作教育实验[3],希望在日常的劳作中能够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性格陶冶中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培养其团结协作的集体精神,最终在走出学校后,能够成为性格完善、拥有良好道德、具备为国家服务的能力并且行动自由独立完整的人。
3.教育新思潮的出现为劳作教育思想奠定基础
首先,自然主义教育思潮作为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重要的教育理论之一,产生于古希腊,酝酿于文艺复兴,形成于18世纪。该思潮的主要理念是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关注儿童的天性,反对知识灌输和死记硬背,将儿童从封建教条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作为自然主义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夸美纽斯、卢梭和裴斯泰洛齐为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夸美纽斯明确提出,将教育适应自然作为一条根本性指导原则并贯穿教育的始终;卢梭强调,要正确地看待儿童,给予充分自由的空间;裴斯泰洛齐则主张心、脑、手的有机结合。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之下,德国也积极开展自然主义教育实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巴西多创办的“泛爱学校”——主张要尊重儿童的主体性。凯兴斯泰纳也批判当下的教育扼杀儿童的天性,仅仅把学生当成知识的容器,忽视了教育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主张要把知识本位的“书本学校”改造成能够体现学生动手探究能力的“劳作学校”。
其次,19世纪末,德国教育界出现了“文化教育学派”。作为一种新兴的教育流派,它不仅对当时流传至德国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起到了纠偏扶正的作用,而且随着其发展,对世界教育学派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该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他的主要观点是,构成民族精神的一般因子有共同的血统,乡土的定住地,共同的历史与传统,共同的言语及经济、学问、艺术等共同的文化产物[4]。但四分五裂的民族发展历史和长期的战争,导致德意志人的灵魂源头是多重性的,混合重叠的,难以形成统一的文化认同感。“文化教育学派”认为,要想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国家,必须要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等,通过教育“陶冶”民众的内心情感世界,“唤醒”民众的“公民意识”,使其意识到国民之间是因为共同的历史命运、语言和精神文化而结合到一起,要在相互间的潜移默化影响之下形成文化认同,从而使个体在理解、认同现有国家文化的基础上实现国家认同[5]。凯兴斯泰纳认为,建立劳作学校是实现国家认同最好的方式,通过劳作促进集体精神的发展,让学生在劳动中形成“劳动共同体”意识。
再次,20世纪初实用主义教育学从美国传入欧洲,在该思潮的影响下,欧洲教育界锐意改革,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新教育运动”。欧洲各国纷纷建立了与旧式传统学校相对立的新式学校,打破了传统教育体系,在教育目的、内容和方法上力求体现学生的主体性,主张给予儿童充分的自由,凸显个体的能动性,反对进行知识灌输。凯兴斯泰纳的劳作教育思想正是在此新思潮影响下诞生的,他主张学生在劳作中能动地、创造性地获得为职业生活作准备的技能,形成团结友爱、互帮互助的良好性格,将职业陶冶和性格陶冶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公民。
二、凯兴斯泰纳生平及劳作教育思想的形成
凯兴斯泰纳成长于欧洲的多事之秋和德国的变革时代,历任教育部门官员,博学多才,阅历丰富。同时他亦忧国忧民,锐意改革,过人的胆识与才学使他较早地意识到德国教育的顽疾和公民教育的薄弱,逐步形成了劳作教育思想体系。
1.个人生活经历对劳作教育思想的奠基
凯兴斯泰纳一生担任过中小学教师、大学教授和教育行政官员等许多角色。1871年,凯兴斯泰纳从师范预科毕业之后就从事教育工作。为了能够升入大学,他一边做家庭教师,一边自学三年的中学课程。刻苦的努力使他如愿考进工业大学学习电机工程,随后又转入慕尼黑大学从事数学和物理研究。1881年,通过数学实验考试之后担任了中学教师。凯兴斯泰纳在中小学任教的实践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同时也敏锐地洞察到德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把重点主要放在用死记硬背的方法去教的学科上,而不是放在形成性格和满足当代生活需要的学科上”[6]。所以,他更加强调要增强教育与生活之间的联系,试图将他的教育体系建立在文化哲学的更广泛的背景下。
凯兴斯泰纳还曾担任教育部门的官员,1895—1919年,先后任慕尼黑市督学长、教育局局长和政府高级顾问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主持制定了慕尼黑市职业教育制度,将国民学校(Volksschule)改为劳作学校,还为青年职工举办“补习学校”,开展技术培训。这种经历使他有机会将自己的教育理念融入到学校教育中,从而形成自己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在担任慕尼黑市教育局局长职务期间,凯兴斯泰纳敏锐地感知到“教学中充斥着呆滞、陈腐的内容,儿童的学习兴趣完全被抹杀,教育与生活脱离”[7]。在凯兴斯泰纳看来,死记硬背的、照本宣科的书本知识教学已经过时,人类教育的发展是要获得精神的满足、性格的陶冶和技能的提升,而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途径就是让学生自由地、富有创造性地参与手脑结合的劳作活动,在劳作中获得性格的陶冶,从而培养出适合国家需求的公民。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建立与传统形式相对立的劳作学校。这为凯兴斯泰纳劳作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劳作学校”理念的提出是20世纪初顺应时代需求的产物。1905年,在汉堡的一次演讲中,凯兴斯泰纳正式提出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应是国民学校的教育目标,并且是国民教育的根本目标。根据这一目标制定出学校的任务,制定出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准则和制度,并依照这些准则规定学校的组织形式——劳作学校。他提倡以实用主义态度看待学校教育,主张将文科学习与手工劳动结合起来,注重手工劳作,以此培养合格公民。
2.公民教育理论对劳作教育思想的促进
凯兴斯泰纳的公民教育理论是劳作教育思想形成的基础,而培养符合资产阶级利益需求的国家公民要通过劳作的形式来实现,它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公民教育思想与劳作教育思想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表里。劳作学校理论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同时也是公民教育理论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公民教育的目的要通过劳作学校来实现,而劳作学校的内容和形式都要以公民教育目标的实现为依据,它们之间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在《国民教育的概念》一书中,凯兴斯泰纳谈到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获得国家意识,当个体努力为自己的国家作出贡献并为之献身的时候,这种国家意识就自然而然地表露出来,产生于自己内心的、真切流露的国家情感比通过说教培养出来的国家意识更加宝贵[8]226。劳作教育能够使学生在动手实践中自然而然地展现自己的情感和需求,并通过集体劳作培养团结一致的精神,从而形成国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