瑶族结盟约 金秀民族关系谱新篇
作者: 莫金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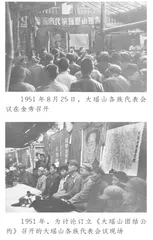
金秀瑶族自治县是全国第一个瑶族自治县。该县制的建立与《大瑶山团结公约》的订立紧密相连,后者更是前者建立的条件之一。如今,金秀瑶族自治县已走过70多年路程。70年多来的历史证明,订立《大瑶山团结公约》这一举措,有效地促进了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并极大地促进了金秀经济社会的发展,昔日贫困落后的瑶族村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景象。
团结公约产生的历史背景
金秀大瑶山瑶族有5个支系,即茶山瑶、花蓝瑶、坳瑶、盘瑶、山子瑶。其中,茶山瑶、花蓝瑶、坳瑶3个支系因有蓄发的习俗,被称为“长毛瑶”;盘瑶和山子瑶因有“迁徙游耕”的习俗,被称为“过山瑶”。
“长毛瑶”进山历史较早,几乎号占(做占领的标记)了大瑶山所有的土地、山林、河流。茶山瑶中苏、陶、全、莫等姓氏族民的祖先在南宋初期就进入荒无人烟的大瑶山,以较早居住的优势大量占有土地、山林、河流,并用石牌立规的形式来显示自己的权益,从而形成垄断自然资源的特权。“过山瑶”进入大瑶山的历史较晚,约于明代才进山,但自然资源几乎为“长毛瑶”号占,为了生存,他们只得向“长毛瑶”缴纳租金批租山地居住、耕种度日。由此,“长毛瑶”和“过山瑶”之间形成“山主”的封建土地垄断特权和“山丁”的封建隶属关系,在历史上,“山丁”与“山主”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斗争。
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广大“过山瑶”不满意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占有制,国民政府执政时期,新桂系当局认为有必要对此进行干预。1942年,国民党广西省当局派出代表召开“勘查金秀瑶区土地纠纷会议”,桂平、荔浦、平南、象州各县政府和金秀设治局以及瑶区各乡亦派出代表,共31人参加。会议列举“山丁”受“山主”苛索的种种现象,提出取缔“山主”的土地特权,由国民政府授予民众耕种,优先批给盘瑶及其他无地瑶民、汉民开垦。这个议题虽然得到会议代表通过,但是遭到“山主”们的反对,于是该议案与国民党的许多“惠民”议案一样,并未能付诸行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大瑶山剿匪”任务,消灭了国民党残余势力,解放了整个大瑶山,为解决“山主”与“山丁”这一历史问题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力量。人民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在平原地区的广大农村开展起来。“过山瑶”也强烈要求进行土地改革,分田分地,但“长毛瑶”不同意。针对当时的情况,曾担任大瑶山瑶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前身)区长的金宝生在多年后(1990年)著文回忆:“(大瑶山)不像平原地区那样表现为地主、富农对农民的剥削,如果我们照搬照套平原地区当时所进行的减租、减息的做法,显然是不能达到加强团结和发展生产的目的。”
应当看到,“长毛瑶”中绝大多数人也是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勤劳农民,他们不是过着完全的寄生生活。他们的批租收入在其经济生活中所占的成分并不大,而且难以为续,将他们划为地主、富农,并不符合政策。那么,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大瑶山特殊的历史问题呢?金秀瑶区人民政府注意到:瑶族传统社会里,利用石牌制度协商解决纠纷的办法很起作用。
所谓石牌制(也称石牌律),是大瑶山瑶族在历史上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和生产生活,将有关规范人们行为的文字刻写在石牌上、木板上,立于村口大路旁,要求人们遵守执行的习惯法。石牌制是大瑶山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产物,也是封建王法在大瑶山虚位的产物(指封建社会名义上管理,实际上没有管到,由瑶族内部自我管理)。从宋代开始,瑶族就不断迁入大瑶山。明代大藤峡瑶族起义的失败令更多的瑶民进入大瑶山居住,由于山高路陡,金秀大瑶山几乎是“王不辖,官不管”的政治死角,是一处“化外之地”。在大瑶山里,瑶族各支系之间会因争土地、山林、河流而发生纠纷冲突,即使是同一村寨的同姓人之间也常有纠纷冲突。在汉族地区,类似这些矛盾纠纷可用朝廷律法来解决,而大瑶山发生矛盾纠纷,只能由瑶族人民自己设法解决。为了处理问题,裁定纠纷,统一认识,有效地管理社会,瑶族村寨必须有自己的政治法律制度,石牌制就是在这种社会需要中产生的。
1990年5月,金秀瑶族自治县三角乡三角村村民在废弃庙地挖土时,挖出一块长90厘米、宽45厘米、厚10厘米,用青灰石板料制成的石牌。石牌上镌刻着如下文字:
立石牌,杀古(牯)牛一使(只),三两(银),煞(杀)诸(猪)一使(只),酒二夭(窑)。成二、下故都策田(长田)设立石牌,回(为)定抵照(存照)。恩回(因为)成二、五甲大兄小弟,合三相良(商量),同心心。治位(诸位)不得何人作生事。五(甲)成二把□□。古都村不得(去)金村、上秀(金秀)、平南、石水(滴水)。故叁村人不得作事,山遑(还)五(甲)成二。夫妻男女,生同生,死同水(睡)。煞(杀)诸(猪)一使(只)一办(半),二夭(窑)酒,十一胡(壶)。
崇祯四年辛未春二月十八日立石牌。
这块石牌后经鉴定为《成二、下故都等村石牌》,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二月十八日设立,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瑶族石牌。石牌所刻事件大致为:成二村(今长二村,茶山瑶)与五甲村(盘瑶)因山地而发生纠纷,下故都村(又称古都村)与叁村亦参与其中,纠纷扩大。最终,大家经过商议,达成如下共识:成二村不得霸占五甲村的土地,并在“策田”(长田)设立石牌为该事件立据,村民们杀猪宰羊、饮酒盟誓以后和睦相处、生死与共。这是茶山瑶、盘瑶和山子瑶共同设立的石牌,用协商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刻文立牌,饮酒盟誓,共同遵守,这种做法为后世用石牌律解决矛盾纠纷,树立很好的历史榜样和先例。
据统计,直至目前,人们能看到的大瑶山石牌律有39件、“料话”(头人讲话)6件,共45件。
团结公约的形成过程
1951年,当时管辖瑶区的各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共中央和广西省人民政府的指示,在整个瑶山贯彻“团结、互助、发展生产”的方针,派大批工作队深入瑶山各村寨,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瑶民解决实际问题。
1951年3月26日,象州县东北乡(今金秀瑶族自治县长垌乡)人民政府针对当时该乡各支系之间开荒引起的纠纷情况,在乡代表会议上经过协商,通过了以团结和发展生产为主要内容的6项决议:“长毛瑶”自愿将荒山的特权放弃,让盘瑶、山子瑶开荒,不收租;自由渔猎,不收租;山林内产品除香菇、木耳外,其余可共同享其利益;无主森林可以自由培植香菇,谁培谁收;水田租额按“佃七主三”处理;能植树的荒山,谁植谁有。
1951年4月,六段村、六定村一带的茶山瑶和六椅、古否等村的盘瑶因开垦山林发生纠纷,修仁县瑶区(今金秀镇辖地)人民政府在解决纠纷时借鉴了东北乡的成功经验,通过召开石牌头人(指善于言辞、办事公正、有胆识,在寨子里有一定威信的男子)和各界代表会议的办法,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双方通过协商,达成5项协议,内容包括茶山瑶同意放弃特权、准许盘瑶开荒自由、不再收租、共同保护山林等。这个协议也较好地解决了瑶族两个支系之间的团结问题,同时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上述两个决议(协议)的订立,不仅解决了当时瑶民之间发生的纠纷,达到团结和发展生产的目的;同时,它还给人们以新的启示:用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瑶民易于接受,能较好地帮助其解决现实存在的矛盾纠纷。金秀瑶区人民政府认真总结经验,认为这种做法适用于整个瑶区范围,抓住时机,趁热打铁,在同年6月19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订立了以维护自由开荒、谁种谁收和加强民族团结为主要内容的12条公约,还通过了《瑶胞爱国公约》。修仁县瑶区的做法和经验很快传遍了整个大瑶山区。各县在瑶区的区、乡人民政府纷纷组织各族群众订立乡、村团结公约,这些做法为后来订立整个大瑶山区的团结公约奠定了基础。
1951年8月20日,由金晓邨和陈岸率领的中央民族访问团来到大瑶山。广西省人民政府决定利用中央民族访问团访问瑶山之机,在金秀召开大瑶山各族代表会议,订立《大瑶山团结公约》。会议代表来自平乐、梧州、柳州3个专区,荔浦、蒙山、平南、桂平、象州5个县所辖的瑶区12个乡,共246人。其中,盘瑶代表111人,占代表总数的45%;山子瑶18人,占代表总数的7%;花蓝瑶9人,占代表总数的4%;茶山瑶59人,占代表总数的24%;坳瑶19人,占代表总数的8%;汉族30人,占代表总数的12%。
8月25日,在中央民族访问团的直接指导下,大瑶山各族代表会议在金秀开幕。会上,修仁县副县长介绍了金秀瑶区用传统的石牌形式订立团结公约的经过。8月27日下午,通过协商讨论,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由各族选出代表11人,组成大瑶山各族人民团结公约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根据各族代表的意见拟出《大瑶山团结公约草案》,经过分组讨论、修改,大会于8月28日下午表决,庄严地通过了《大瑶山团结公约》。29日,立牌仪式依照瑶族传统的石牌形式举行,各族代表在石牌前饮鸡血酒,表示遵守不渝。
1953年2月,为解决执行《大瑶山团结公约》中存在的问题,召开瑶老座谈会和区、乡干部大会,之后制定出《大瑶山团结公约补充规定》,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大瑶山团结公约》。《大瑶山团结公约》及其补充规定的制定与实施后,金秀瑶区内的汉族、壮族与瑶族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各民族及瑶族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歧视与偏见逐渐消减。
团结公约的重大意义和影响
《大瑶山团结公约》的订立和立牌,对整个金秀大瑶山社会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其一,为解决“长毛瑶”与“过山瑶”土地占有差异的矛盾提供新途径和新手段。《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后,“长毛瑶”愿意放弃过去的各种特权,将号占的荒地分给瑶区各族群众自由开垦种植,谁种谁收,不再收租,各族群众可以自由上山打猎、下河捕鱼,解决了广大“过山瑶”进山以来一直没有土地的问题,拓宽了他们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其二,提高了群众生产积极性,发展了生产。《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后,荒地可以自由开垦,谁种谁有,激发了各族人民生产的积极性。据统计,1952年大瑶山新开荒1400多万平方米土地,产量剧增,为各族人民增加两至三个月的口粮,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
其三,加强了民族团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平原地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用的是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批斗不良地主,没收地主田地分给贫雇农耕种,这是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大瑶山情况特殊,这里地主、富农很少,“山主”集团大多是自耕农和贫农,他们即使“剥削”“山丁”,也多以村寨或家族形式出现,若用阶级斗争方式来解决大瑶山的土地问题,必将人为地扩大对立面,不利于大瑶山的安定团结。由此,瑶族人民在实践中总结出用民主协商的方式来解决土地矛盾问题的经验,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导下,通过多次商议,“长毛瑶”自愿放弃特权,“不捕、不批、不斗”就解决了几百年来遗留的历史问题,解放了生产力。《大瑶山团结公约》订立之后的几年里,顺利处理各项重大民族纠纷案件1600多件,促进了汉、壮、瑶等各民族的团结和瑶族内部5个支系之间的和谐,为之后金秀瑶族自治县各民族团结发展,共同建设新瑶山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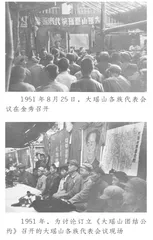
其四,为各地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广西是个多民族地区,历史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和挑唆,造成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隔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些矛盾隔阂,使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贯彻落实,让各族人民真正享受到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好处,是摆在民族工作者面前一个重要的课题。《大瑶山团结公约》的订立及其所起的作用,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成功的范例,石牌最初是维护土地私有制的权力象征,如今它却成为瓦解和消除土地私有制的武器。这给广西各地的民族工作者以新的启发:民族问题有时可以用民族文化的形式来解决。
其五,为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建立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县级)奠定了基础。《大瑶山团结公约》的订立和执行动摇了封建剥削的经济基础,贯彻了中共提倡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政策,解放了生产力,为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落实、大瑶山瑶族自治区(县级)的成立,奠定了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