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头上的国家级“非遗”
作者: 庞晓华2021年,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瑶族石牌习俗”以规约习俗类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是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积极参与挖掘、保护、传承的成果。这一项刻在石头上的国家级“非遗”,仿佛在向世人诉说着大瑶山瑶族人民与石牌制度在金秀70多年沧桑巨变中难忘的历程。
刻在石头上的“法度”
说到瑶族文化,必须了解“石牌制”。金秀瑶族自治县下辖10个乡镇81个村(社区),以山为界,有“山内”“山外”之说。金秀、三角、长垌、大樟、六巷、罗香、忠良等乡(镇)称为“山内”,桐木、头排、三江等乡(镇)称为“山外”。“山内”以瑶族聚居多,瑶族中有茶山瑶、花蓝瑶、坳瑶、盘瑶和山子瑶5个支系;“山外”属瑶族、壮族、汉族杂居地区。“山内”很多瑶寨的村规民约都刻在石碑上,且立在寨子里最显眼的位置。长垌乡古占瑶寨是金秀远近闻名的旅游村,该瑶寨游客服务中心前就立着一块石碑,石碑上刻着有关村规民约的内容,对村民日常的行为进行约束,且与时俱进,为保护游客消费权益也有规定禁止村民宰客之类的条款。
村规民约为何要刻在石碑上呢?这就要从金秀大瑶山的“石牌制”说起。石牌制(也称石牌律、石牌公约、石牌习俗等)是金秀瑶族在封建社会里特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它是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具有长期稳定不变的特点,它的律文条款是经过参加石牌组织的瑶民一致通过确定的,其内容、范围、权利和义务都列举得十分清楚明白。不同的村寨制定不同的石牌,也有几个村寨联合制定的石牌。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瑶族石牌是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所立的《成二、下故都等村石牌》(国家一级文物),类似这样的石碑,在金秀瑶族村寨中发现了45件。
以现如今发现的石牌数量及其内容分析推论,瑶族石牌习俗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发轫时期——明朝初年至清朝嘉庆年间,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瑶族石牌是于明崇祯四年(1631年)所立的《成二、下故都等村石牌》,当时石牌主要用于解决山林、土地纠纷;发展时期——清道光二年(1822年)至清咸丰三年(1853年),发现的石牌有9块,此时社会动荡,建立的石牌用于联村互保;低潮时期——清咸丰四年(1854年)至清光绪八年(1882年),瑶山发现的石牌有1块,内容涉及面广,石牌组织力量明显增强;复兴时期——清光绪九年(1883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这时期的石牌有9块,除了石牌管辖范围越来越大,各村寨还根据各自面临的问题针对性地制定条规;鼎盛时期——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至1930年,瑶山出现了7块石牌,由于这时期匪盗猖獗,石牌主要用于平息匪盗;瓦解时期——1931年至1940年,这一时期,国民党广西当局设立金秀警备区署以治民事,石牌进入衰落瓦解时期。但是由于石牌制在瑶族社会中沿袭了几百年,由此长期形成的牢固的原始民主色彩的影响并没有完全从瑶族人民心中消失,瑶族人民仍一直自觉地以石牌条规来制约自己的行动,使大瑶山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秩序渗透着石牌的精神。

瑶民们依照石牌条规来规范自我行为和社会秩序,石牌条规是通过石牌组织内的成员一致商讨确定的,石牌组织的成立则是通过会议仪式而形成的,过程极其隆重,和现在村委组织全村群众召开大会商讨村规民约有些相似。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期,石牌制度的作用和特点是各不相同的。从类型上看,大体上可分为血缘石牌、姻亲石牌、支系石牌、地缘石牌。最初的血缘石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平息内争,惩治盗贼和共御外侮;金秀瑶族有5个支系,除了茶山瑶有族内婚现象,其他4个支系都禁止族内婚,但也都是支系内联姻为多,由此形成了姻亲石牌;支系石牌只能维护一个支系内的利益,确保同支系的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近代以来,各支系之间土地、山林、河流的争夺纠纷不断激化,且时有械斗发生,兵匪也经常入山骚扰,支系石牌组织无力担负抵抗之责,因此便设立了同族的地缘石牌来约束事端,发动全族共同抵御外敌。
瑶族石牌习俗作为金秀瑶族在封建社会里特有的社会组织制度,它是一个地域内的瑶族为维护生产、社会秩序而共同订立的规约,镌刻在石碑上或抄写在纸上、木板上,供大家共同遵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具有“法”的权威,担负起对内保护农村农副业生产和维持社会秩序,对外抵御强敌的重要作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为维护大瑶山社会秩序起到了比较广泛的积极作用。
刻在石头上的民族团结“丰碑”
金秀瑶族自治县委大院主楼右侧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大瑶山团结公约》的全文内容。该公约见证了金秀瑶族自治县的成立和发展,瑶山人不能忘记,它的魂早已镌刻在每个瑶山儿女心里,是大瑶山上民族团结的丰碑。
72年前,中共中央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来到大瑶山,促成《大瑶山团结公约》的订立。大瑶山人民将此公约勒于石碑,饮鸡血酒盟誓遵守不渝。1953年2月,金秀召开瑶老座谈会和区、乡干部大会,制定出《大瑶山团结公约补充规定》。《大瑶山团结公约》和《大瑶山团结公约补充规定》的制定与实施,废除了“山主”的土地特权,实行谁种谁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解决瑶族内部各支系之间关于土地山林问题的有效方案,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改善了瑶族内部及各支系之间的关系,消除了民族隔阂,使得金秀汉族、壮族与瑶族之间的交往与日俱增,各民族及瑶族内部各集团之间的歧视与偏见迅速消减,促进了瑶、壮、汉等各民族的团结和瑶族内部5个支系之间的和谐,为之后金秀大瑶山70多年的团结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石牌习俗、《大瑶山团结公约》、村规民约的基础上,1989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七届人大常委会批准,《金秀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正式施行。各地在《金秀瑶族自治县自治条例》法律框架下还以石牌形式订立了大批村规民约,以传统石牌精神规范居民行为,对于促进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2年是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以及来宾市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县城新建了体育场,解决了多年来县城没有综合性大型体育场的问题;全面完成山水瑶城综合提升工程,县城更加亮丽;新建了县教育园区和县人民医院桐木分院,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贺州至巴马高速公路(金秀段)建成通车,结束了大瑶山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金秀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强。在2022年11月28日的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上,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自治区和来宾市分别发来贺电。自治区代表团向金秀赠送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金秀高质量发展”贺匾。2023年1月,金秀又成功创建第十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民族团结的旗帜在圣堂之巅高高飘扬。
刻在石头上的国家级“非遗”
2007年是金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县文化馆设立了金秀瑶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分中心,文化馆的演员从此又多了“非遗”保护工作人员这一重身份,金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随之被提上议事日程。时逢第一批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那段时间,整个文化馆弥漫着一股低沉的空气,非遗申报工作将这些专业的演员难住了,身上的十八般武艺都使不上劲,究竟什么是“非遗”,什么是金秀最具有竞争力的“非遗”项目,问题还没想明白,但时间不等人,离提交申报材料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就在大家都没有找到思路的时候,当时担任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庞晓华在一次下村调研时,看到某村头刻在石碑上的村规民约,灵光一闪,石牌——就是它了。
庞晓华兴奋地将这个想法告诉文化馆馆长肖茂兴,二人一拍即合,金秀的“非遗”项目就决定申报瑶族石牌习俗。在肖茂兴馆长的带领下,文化馆组成两组人马,一组人负责在全县开展对瑶族石牌现存情况的深入摸底,考察出有价值的石牌实物30块(处),后来,有11块展示于县瑶族博物馆瑶族石牌习俗主题展厅,2块捐赠给广西民族博物馆。另一组人撰写申遗项目申报书、拍摄申报视频和收集整理申报图片。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瑶族石牌习俗”于2007年11月被列入广西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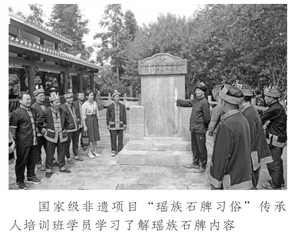
“瑶族石牌习俗”在成功申请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后,文化馆的同志们热情高涨,决定趁热打铁,将“瑶族石牌习俗”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但“申遗”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资料收集不全,申报文本的撰写水平有限等原因,直至2019年,金秀瑶族自治县文化馆组织了“瑶族服饰”“瑶族度戒”“瑶族医药”“瑶族石牌习俗”等具有代表性的区级“非遗”项目,向自治区推荐申报国家预备项目,最终经过各级专家评选,仅有“瑶族石牌习俗”入选广西申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0项预备名录之一。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从2019年至2021年,金秀走过了不懈努力的申报之路。为了还原“瑶族石牌习俗”的真实场景,文化馆组织了400名群众两次参加恢复还原大型启誓活动,将黄泥鼓舞继承人兰扶明申报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瑶族石牌习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组织该习俗传承人参加“非遗”集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瑶族盘王节活动,举办瑶族习俗培训班,组织演艺团队排演《石牌谣》大型剧目,撰写《白马姑娘》文学剧本等。有志者事竟成,2021年,“瑶族石牌习俗”以规约习俗类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也是广西在30项预备名录中获认定的18项之一。从此,刻在石头上的国家“非遗”——石牌习俗成为大瑶山的一张闪亮名片。
石牌制在研究瑶族历史变迁,挖掘文学内涵及探讨为发展和完善我国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促进基层民主建设,服务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
一是历史价值。瑶族石牌习俗历史悠久,是瑶族人民为适应社会的变化,实施自我保护的重要举措,不仅记录了本民族的制度历史,也曲折地反映出不同时期的历史状况。
二是文学价值。石牌条规一般都简洁、严肃;宣讲“料话”则讲究语言整齐、气势连贯、音韵和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风趣的描述使瑶民大众了解石牌、遵守石牌,使本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宗教等内容“个个进心、人人入耳”,代代相传。
三是社会价值。石牌习俗是瑶族人民在历史上为求得生存发展和社会安定而建立的,是瑶族进行自主管理、自我教育的方式,符合民族精神价值取向。石牌习俗重视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是认识瑶族社会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资料。
四是当代价值。利益表达是瑶族石牌习俗的基础,石牌习俗通过加强瑶族村寨的利益表达与利益集合来促进民众自觉参与和遵守,研究瑶族石牌习俗,能为发展和完善我国民族地区的村民自治、促进基层民主建设、服务新时代乡村振兴提供有益借鉴。文
(庞晓华:金秀瑶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