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王信之乱军事地理考
作者: 周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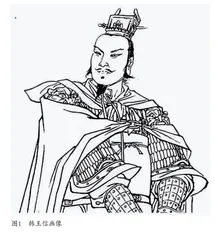
汉军击韩王信与对匈防御战是初建的汉帝国与日益崛起的匈奴政权的第一次交锋,也是整个汉匈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在此次战役中,汉帝国运用南北夹击的方式,成功击溃了叛军与匈奴联军,但高祖却在匈奴诱敌深入的战术欺骗下轻敌冒进,酿成平城之围。最终匈奴在包围汉军七日后未敢发动进攻只能撤围而去,汉军则成功收复了失地。文章主要围绕这场战争,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探讨此次战役的空间进程以及双方战术手段的运用。
汉高祖六年春,高祖以韩王信“材武”,“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都晋阳”。初王代地的韩王信颇欲有一番作为,面对匈奴对代地的频繁侵扰,主动上书高祖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将都城迁往句注山以北的马邑,以便就近防御匈奴入侵。同年秋,匈奴攻代,进围马邑,此时韩王信才意识到难敌匈奴铁骑,“数使使胡求和解”。高祖恐韩王信有二心,多次派人责让韩王信。次年,韩王信在被高祖猜忌的恐惧与匈奴围困的压力之下投降匈奴,于是匈奴得以深入汉地,逾句注山南下。此次动乱波及云中、雁门、代郡、太原、上党五郡。由于韩王信的叛乱得到了匈奴的直接支援,故而这次战争具有平叛与御边的双重性质,也是新生的汉政权与正在崛起的匈奴政权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为应对入侵,汉军分南北两路攻击叛军及匈奴部队,而后在上党铜鞮汇合,夹击韩王信,之后下晋阳,至平城。起初,汉军进展极为顺利,然而却先胜后败,最终酿成了“白登之围。”此外,本次入侵匈奴方面是由冒顿单于指挥,左、右贤王均参与了这次战役。战役初期,匈奴并未投入全部兵力,直至平城之战时匈奴才将40万精骑全部投入战场。而汉朝的指挥者是高祖、周勃等,总兵力为三十二万,且以步兵为主。
韩王信南下与汉军北征
根据《史记·韩信卢绾列传》记载,韩王信在投降匈奴后侵汉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击太原”,由此可知虽然高祖“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然而只有马邑附近的地区与韩王信一同反叛。因此韩王信自马邑南下后才得以基本略取了其封地太原郡,又南下上党,兵锋直指铜鞮,遭到高祖亲率的汉军主力要击而败(如图1所示)。
这里要重点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高祖击韩王信的出兵路线为何。《中国历代战争史》的作者认为:“高帝乃自将灌婴、靳歙等北击韩信;同时又令樊哙、周勃、夏侯婴等率骑兵自代越霍人至云中。”《中国军事通史·西汉军事史》(以下简称《西汉军事史》)基本承袭了这一观点,还明确指出,汉高祖是自洛阳北上。杨丽则完全沿袭了《西汉军事史》的观点(如图2所示)。
史书中多有汉军在云中郡与胡骑交手的记载。如《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载:以将军从高帝击反韩王信于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击胡骑,破之武泉北。
《史记·樊哙列传》《史记·夏侯婴列传》《史记·灌婴列传》均有类似记载。上述将领所“从高祖”进攻代地是指参与了这场高祖指挥的扫平代地的战争,并不意味着其军队必须完全跟从高祖行动。而这些将领未随高祖大军进攻上党之铜鞮,而是直接抄袭叛军后路,先攻占雁门之马邑、葰人(霍人),而后进攻云中郡的武泉县、云中县一带。灌婴部亦在其中,并非如《中国历代战争史》所言随从高祖大军。
高祖五年,“天下大定。高祖都雒阳,诸侯皆臣属。”同年五月,高祖在娄敬的劝说下,“入都关中”。这一时期,周勃也奉命“还守雒阳、栎阳”,其驻守的地点亦随着汉帝国迁都而从洛阳迁往关中的栎阳。故高祖六年、七年匈奴入侵马邑及韩王信叛乱之时汉军当从关中地区派周勃等人率军至代地平叛。若从关中至马邑、霍人,其路线当为东至蒲坂津或汾阴津渡黄河后北上,或北至君子津渡黄河后东下,而绕至代郡,进兵路线过于迂远,不符合“兵之情主速”的常理。上述诸家以为从代郡进兵,很可能是受到了《史记》中多次提及的“击反韩王信于代”“攻反韩王信于代”等记载的影响,不过这里的“代”应指代地而非指代郡。
那么,周勃等人所率的汉军当从汾阴津、蒲坂津、君子津之中的哪个渡口渡河进攻呢?假如汉军从汾阴津、蒲坂津渡河北上,比较便捷的路线是经太原盆地、忻定盆地越句注山至马邑,然而这也是南下击太原至铜鞮的韩王信军的最为便捷的路线,故汉军很可能会正面遭遇韩王信大军,如此,韩王信就难以越过汉军阻拦进至铜鞮,至少史书中会记载双方的战斗。
事实是,韩王信军成功进至上党,与后来赶到的高祖大军展开对峙,史书未有周勃等将领所率汉军与韩王信主力交战的记载,说明了这支汉军应未取此道。那么就只剩下君子津,由君子津渡河后可直扑马邑,既保证了进攻的突然性,也避开了韩王信的大军,故汉军当从此道攻马邑。这支部队可以称之为北线汉军。
而高祖亲率的南线汉军应当是自洛阳至荥阳间集结后北上。根据《史记·灌婴列传》的记载,在灌婴与高祖汇合后曾“受诏并将燕、赵、齐、梁、楚车骑,击破胡骑于硰石”,也即高祖的部队得到了山东五国王国兵的支援。荥阳位居汉郡与各诸侯国之间的中心位置,有敖仓之粟,在与项羽及东方诸侯国的战事中经常作为汉军及诸侯国兵力的集结地点,且地处上党、太原之南。故而在北线汉军向叛军后方迂回之时,刘邦应当是在洛阳至荥阳一带集结大军,亲自北上铜鞮堵截叛军南下。
而南线汉军发兵的时间应当大大晚于北线汉军,这是因为洛阳—荥阳一带至铜鞮并不遥远,高祖自洛阳—荥阳附近发兵后很快即可至铜鞮与韩王信军对峙。而关中距马邑、云中悬远,且根据记载,北路汉军进至马邑、云中后又要南下铜鞮,一路转战,所费时日必多,若两军同时出兵,如此漫长的时间刘邦的主力部队依然不能击破当面之敌,还需等待北线汉军合击,是不太可能的。而北线军先期出发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高祖需要在洛阳—荥阳一带等待山东诸侯国的援军,另一方面根据前引《史记·韩信卢绾列传》的记载,在韩王信投降匈奴之前,“汉发兵救之”,北线汉军当本是汉廷支援韩王信的援军,只是援军未至韩王信已叛,于是援军就成为平叛的大军。
平叛诸战与白登之围
由于韩王信的主力业已南下“击太原”,北线汉军比较轻松地占领了马邑,此即《灌婴列传》中的“以车骑将军从击反韩王信于代,至马邑”。在占领马邑后,一方面,灌婴受命分兵收降楼烦以北六县,所谓“楼烦以北六县”可能即为马邑附近的楼烦、埓县、汪陶、剧阳、醇县、繁畤六县,控制此六县即控制了句注山以北管涔山以东的大同盆地南缘地带,不仅保障马邑的安全,同时控制了经楼烦谷口及句注山南下太原郡的两条道路的北口。另一方面周勃率大军自楼烦县阴馆地区逾句注追击南下的韩王信军。南下后,周勃、樊哙又东攻霍人(即葰人),完全控制了句注山南麓地区。汉军攻下霍人后周勃等人本应向南追剿叛军,然而此时云中郡又受到匈奴入侵。各列传中特意强调周勃、灌婴、夏侯婴等多位汉军将领在武泉北击破胡骑的功绩,既体现了汉军在此地的战果较大,也说明了前来侵扰云中郡的匈奴部队规模确实不小,因此,周勃与樊哙所部不得不北上救援。于是,周勃与樊哙,汇合了句注山北已经略定楼烦以北六县的灌婴部一同北上云中郡。在收复云中郡的过程中,北线汉军首先进攻武泉县之敌,从而切断匈奴由此经白道出塞的退路,此战汉军大胜,重新夺回了武泉西北白道的控制权,而后汉军乘胜直下云中县,收复了云中郡的失地。北线汉军的整个经过即《樊哙列传》中所谓“自霍人以往至云中,与绛侯等共定之。”消灭云中郡的匈奴部队后,周勃等人则兼程南下驰援高祖(如图3、图4所示)。
从叛军的角度来看,在周勃北上云中后,叛军暂无后顾之忧,故而基本占领了忻定盆地与太原盆地之各县,又继续南下上党,有向南窥伺河内及洛阳之势。在到达铜鞮县后为高祖大军所阻。
北线汉军南下铜鞮最为方便的道路即为循叛军南下路线,再度翻越句注山,经由忻定盆地、太原盆地至上党郡,不过依据史书记载,北线汉军克复云中郡之后直至铜鞮之战前均无战斗的记录。此外,《绛侯周勃世家》中周勃“转攻韩信军铜鞮”后才有“击韩信胡骑晋阳下,破之,下晋阳”的记载,而晋阳是由此道南下的必经之路,若经此道就不会在铜鞮之战后才攻下晋阳。
故而北线汉军应当是考虑到上述道路需要一路与叛军交战,延误南下速度,故而取道楼烦谷口,经汾水谷地南下汾阳、离石县绕至晋阳以南后再趋铜鞮。
在南北汉军的夹击下,大破韩王信军,还斩其大将王喜,韩王信逃入匈奴。汉军乘胜“降太原六城”,完全收复了太原以南的失地,而后回攻晋阳。曼丘臣、王黄则收拢韩信败军,并立赵利为王,并在匈奴左右贤王万余骑的支援下屯驻于广武,并前出至晋阳救援被汉军包围的晋阳守军。汉军与叛军及匈奴联军在晋阳城下展开激战并大破之,攻下晋阳城。此后,高祖留守晋阳,派遣汉军开始追击叛军与匈奴的败兵。
在这里我们需要厘清的是本节的第二个重点问题,即叛军撤退与汉军追击的路线为何。
《周勃世家》与《灌婴列传》均记载汉军追击至硰石,然而《韩信卢绾列传》却记载汉军“追至于离石”。离石县地在晋阳以南,从晋阳至离石有两条道路,一是自晋阳北上汾水谷地,至汾阳县后西行再折而南下至离石县;二是自晋阳向南至兹氏县,后西北至离石县。且不论此时这两条道路均在汉军的控制之中,叛军能否通行。即便叛军能够撤至离石,然而其不向北撤退,却向更南处的汉境腹地进军亦是不合常理的。故离石当是硰石之误。
那么硰石又在何处呢?《正义》云:“在楼烦县西北”。《韩信卢绾列传》载:“汉军汉大破之,追至于离石,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西北,汉令车骑击破匈奴。既然此离石乃是硰石,就是说汉军在硰石击破匈奴与叛军,匈奴军后撤后又重新在楼烦西北聚集部队。而《周勃世家》的记载中,汉军在硰石击破敌军后“追北八十里”,那么匈奴与叛军在硰石被击败后,其阵线当较硰石至少后撤八十里才在楼烦西北重新聚集。故而硰石不当在楼烦县西北,而是楼烦县东南部,考虑到叛军当从娄烦县东部的阴馆地区北撤(下文详论),那么硰石可能即是阴馆附近的累头山。
叛军从晋阳撤至楼烦有两条道路,一是经汾水谷地至楼烦,二是逾句注山至娄烦县阴馆地区。阴馆在景帝以后虽然独立设县,但在高帝时期还是楼烦所辖的一个乡。《汉志》载:“句注山在阴馆……阴馆,楼烦乡。景帝后三年置。”王念孙曰:“楼烦上当有故字,言阴馆县乃故娄烦乡,景帝后三年始置县也。志文若是者多矣。”由于匈奴与叛军此前曾屯兵广武以南,因而叛军北撤之时应当沿晋阳至广武沿途收拢部队,而后翻越广武以北的句注山经娄烦县阴馆地区北撤。
是故汉军自晋阳追击叛军的进程应当如下:叛军自晋阳取道广武逾句注山北撤。汉军的车骑部队则紧随其后进行追击,并在楼烦东部阴馆地区的硰石一带击破敌军。而后,匈奴与叛军在楼烦西北收拢残兵,再度为汉军所破,汉军则乘胜全取楼烦三城。在此阶段中“匈奴常败走,汉乘胜追北”,汉军连战告捷不仅重创了韩王信及赵利的叛军还接连击败匈奴部队,成功收复了句注山以南的失地。
汉军的捷报频传为白登之围的失败埋下伏笔,产生轻敌情绪的高祖决心与匈奴单于的主力进行会战,听闻单于居于代谷,于是亲率大军至平城,出白登迎击单于。《韩信卢绾列传》载:闻冒顿居代谷,高皇帝居晋阳,使人视冒顿,还报曰“可击”。上遂至平城。上出白登,匈奴骑围上。
靳生禾指出,汉代的白登是山名,当今大同市东北50余里的采凉山。代谷,说法不一,《正义》云:“今妫州”,中国历史地图集则将其定于汉朝代县(今蔚县)附近。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边,闻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击之……。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围。
刘邦“北至于代谷”后遭遇平城之围,说明了代谷当在平城与白登附近,也即今大同一带,并不在代县。结合“匈奴聚于代谷之外”的记载,代谷应当为由平城向北越过白登山、采凉山等平城以北诸山出塞的山谷。
急于至代谷与匈奴决战的高祖在“步兵未尽到”的情况下就“先至平城”,被冒顿单于纵兵四十万围困于白登山七日。不过,一方面,汉军贿赂单于阏氏,阏氏以汉地对逐水草而居的匈奴没有价值为理由说服冒顿单于,另一方面与匈奴相约共同攻汉的王黄、赵利军迟迟不至,使得冒顿单于怀疑二人已经倒向汉军,甚至可能与汉军共同设伏;此外,考虑到未至的步兵听闻高祖被围也会星夜驰援,冒顿单于有陷入汉军反包围的可能,故而匈奴最终解围而去。战后刘邦“令樊哙止定代地。立兄刘仲为代王。”至此,虽然汉军被困于白登,但收复了平城以南的全部失地,得以重新册封代王。高祖十一年春,“故韩王信复与胡骑入居参合”,策应陈豨叛乱,“柴将军屠参合,斩韩王信。”至此韩王信之乱彻底平定。
汉匈双方的攻防特点
在西汉初期的汉匈攻防战中,匈奴明显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依靠其来去如风的战略优势可以集中兵力打击汉帝国边防线上的任意地区。不过这种优势只是相对的而并非绝对的。在韩王信之乱中,匈奴虽然侵入内地,但面临汉军大兵团反击,也只能避免与汉军进行主力会战而退至塞外。即便白登之围时匈奴以优势兵力将汉军团团包围,却依然不敢发动进攻,最终只能是撤围而去。从军事技术及战术技巧的角度分析,这是因为“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的匈奴骑兵以骑射见长不擅肉搏;在战斗中“利则进,不利则退”,缺乏良好的纪律;且没有马镫,难以进行骑兵冲击,在正面对阵训练有素的汉军车骑部队和步兵军团时未必尽占上风。李硕即指出:“匈奴等草原民族采用单兵骑射战术,几乎从不与敌军进行近距的冲击肉搏战”。
因而匈奴在这一时期对汉王朝入侵的主要目标并非吞并汉王朝,而是削弱汉王朝实力,劫掠汉边。为了贯彻这一目标,匈奴运用得最为出色的战术手段即为示弱、欺骗与诱敌深入。《孙子兵法·计篇》云:“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匈奴单于可能并不通晓《孙子兵法》,但其“善为诱兵以冒敌”,则为这一思想的最好体现。在刘邦击韩王信的最后一个阶段——平城之战中,冒顿单于“详败走,诱汉兵”,并且在汉军派遣使者赴匈奴窥探虚实之际“匿其壮士肥牛马,但见老弱及羸畜”。通过佯败与示弱的方式将汉军调离汉雁门与太原郡的腹地,引诱汉军至平城一带的汉匈边境——这个有利于匈奴作战的地带,在汉军车骑部队与主力步兵脱节后一举将高祖包围。
《孙子兵法·势篇》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在平定韩王信叛乱与匈奴入侵时,汉军南北夹击,这种战术手段体现了“奇正相生”的军事思想。高祖自上党铜鞮与韩王信大军正面对峙,防止其向内地深入,是为正兵;周勃则为奇兵,直扑马邑,收复云中、雁门,而后与高帝大军南北夹击铜鞮的韩王信与匈奴联军,从而将其击溃,才使得汉军乘胜直下晋阳并追北至平城。
汉军击韩王信与对匈作战,是汉帝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和匈奴的大规模交锋,也是汉匈战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交锋,即使不计算韩王信的叛军部队,汉匈双方投入的总兵力也在七十万以上。在这场大交锋中,汉帝国采用了分进合击的战术手段,为南北两线,北线部队由周勃等人率领,出长安趋马邑,战云中,南线部队则由高祖率领,出洛阳—荥阳至铜鞮,而后南北两支部队合击铜鞮、直下晋阳,虽然最终遭遇了白登之围,但亦成功击退了叛军与匈奴联军,收复了失地。而匈奴在本次入侵中亦运用了诸如示弱、欺骗与诱敌深入等战术手段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成功将汉军由内地调至有利于匈奴作战的代北平城一带,进而一举包围汉军。但谨慎的匈奴单于未敢与汉军决战,最终撤围而去,汉匈双方第一次大规模交锋至此结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