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花人物纹瓷笔筒赏析
作者: 盛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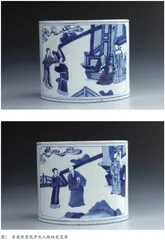
青花瓷,作为中国瓷器艺术的瑰宝,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世界陶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青花人物故事纹笔筒更是其中的精品之作,它们以精湛的工艺、丰富的题材和深刻的文化寓意,展现了清代瓷器艺术的高超成就。
文章以无锡博物院的两件清代的藏品为例,深入分析笔筒的造型艺术、纹饰布局、人物形象,特别是对“佛殿奇遇”和“十八学士图”这两个经典题材进行详细的探讨,旨在揭示清代人物故事纹瓷器与文学、绘画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清代瓷器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深远影响。
概述
笔筒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内涵。笔筒是中国古代除笔、墨、纸、砚以外最重要的文房用具,自明朝中晚期起一直长盛不衰。明朝文震亨在《长物志》中描述了书斋的具体布置:“天然几一,设于室中左偏东向,不可迫近窗槛以逼风日。几上置旧砚一,笔筒一,笔觇一,水中丞一,砚山一。”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由此可见,笔筒成为文人墨客书案上不可或缺的美器。笔筒产生的历史年代已不可考,从史料和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来看,最初的形式多为竹制或木制,简约实用。例如,宋代《致虚杂俎》中记载:“羲之有巧石笔架,名‘扈’;献之有斑竹笔筒,名‘裘钟’,皆世无其匹。”无锡博物院藏有一件明代的“东山报捷”笔筒,也是采用竹刻的工艺。随着时间的推移,笔筒的材质逐渐丰富,出现了陶瓷、玉石、象牙等多种材质。《长物志》有云:“湘竹、棕榈者佳,毛竹以古铜镶者为雅,紫檀、乌木、花梨亦间可用,陶者有古白定节者,最贵;青冬磁细花及宣窑者,俱可用。”至明代天启、崇祯时期,瓷质笔筒的生产量已达到一定规模,其基本形制为直口、平底、腰微束,且以青花为主,纹饰有植物、动物、人物等,呈色淡雅,绘工精细。清顺治时的瓷笔筒保留了前朝的特征,仍然以青花为主,但器型品种较多,有直口直壁式、束腰侈口式等。清康熙年间是瓷笔筒生产的鼎盛时期,品种极为丰富,有青花、五彩、斗彩、釉里三彩及各种颜色釉。器型有直口直壁形、束腰侈口形、方形、竹节形等。高度一般在12~15厘米左右,这种大小也比较适合陈设于书斋案几。文人雅士们案几上精美的瓷质笔筒不仅承载着日常书写工具收纳的需求,同时,通过笔筒上的纹饰图案,体现出文人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味,也表达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艺术的追求。
清代青花人物故事纹笔筒的特点与价值。清代制瓷业非常繁荣,康熙时期生产了大量绘有人物故事纹的瓷质笔筒,以青花和粉彩的较为常见。无锡博物院的两件清代的青花笔筒,在造型上,都采用了端庄典雅的传统风格,线条流畅、造型优美。同时,工匠们还注重细节的处理,使得笔筒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和谐统一的美感。在纹饰方面,都以人物故事为题材,一件取材于《西厢记》的经典情节“佛殿奇遇”,讲述了平民书生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初次在佛殿相遇的故事情节。另一件取材于《十八学士图》,描绘了唐代文学馆中十八位学士聚会的场景。绘瓷者通过精细的线条和青花浓淡的运用,将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出来。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还融入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历史背景,使得笔筒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人物故事题材的青花瓷笔筒,不仅展现了清代文人对文学艺术的深厚情感和崇高追求;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为我们了解清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佛殿奇遇”与“十八学士图”纹饰分析
清康熙青花开光人物纹瓷笔筒。该笔筒口径约18.5厘米,底径约18.2厘米,高度15.3厘米,为国家二级文物,现藏于无锡博物院。
该笔筒在造型上继承了传统端庄典雅风格,同时注重细节的处理。在制作过程中,工匠们选用优质的青花料,经过精心调配,使得笔筒的釉色呈现出一种深邃的蓝色,宛如夜空中的星辰。同时,釉面光滑细腻,均匀无瑕,给人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无锡博物院的这件青花人物纹笔筒,就是以《西厢记》为创作题材的经典之作。《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代表作之一。讲述了平民书生张生与相国小姐崔莺莺的爱情故事。该剧情节曲折动人,人物形象鲜明,被誉为中国古代戏曲的巅峰之作。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古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西厢记》中才子佳人的故事,刚好满足了这种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愿望。底层民众欣赏《西厢记》曲词的通俗本色之美,而文人饱读诗书,接受的是其典雅抒情的优美风格,正因为《西厢记》可以满足不同阶层的审美趣味和心理需求,才能够风靡明清两代。社会各阶层的民众对《西厢记》的热捧直接影响到当时瓷器的生产。
无锡博物院的这件笔筒所绘的是《西厢记》中的一个经典情节“佛殿奇遇”。故事发生在男主人公张生赴京赶考途中。一日,张生游览普救寺时,偶遇正在佛殿上香祷告的女主人公崔莺莺,由此,牵引出了一段千古流传的风月佳话。正如槃薖硕人在眉批中所云:“《西厢》一部命脉,俱在此一遇引起。”
整件器物的纹饰画面由两个“开光”组成,画面一,张生正站在佛殿前凝视着崔莺莺;惊见莺莺,张生“目定魂摄,不能遽语”,其目光紧紧追随佳人身影;莺莺对此有所察觉,左手执扇掩面,一边听着红娘的诉说,一边将目光转向英俊的张生。张生与莺莺两人目光交汇,仿佛有千言万语在其中传递。法聪和尚见此情形,正从旁提醒张生。画面二,大家闺秀莺莺已先行回避,只留下红娘与法聪交谈。张生与另一僧人仍站立于殿前,久未离去。画面中张生和崔莺莺的形象栩栩如生,他们的动作、表情和服饰都经过精心设计和描绘,与佛殿、云雾、栏杆、山石等背景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场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同时,绘制者还巧妙地运用了透视法和比例关系,使得画面更加立体和逼真。
在这件藏品中,瓷器工艺与文学艺术完美结合,通过精美的纹饰和生动的画面展现了《西厢记》中的经典故事情节。这种跨界的艺术形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别样的《西厢记》世界,不仅反映了清代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体现了清代文人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使得这一文学作品所倡导的追求自由精神得以以另一种形式传承和发扬。
清“大明嘉靖年制”款青花人物纹瓷笔筒。该笔筒口径约19厘米,底径约18.5厘米,高度16.5厘米,现藏于无锡博物院。
该笔筒的造型周正,线条简洁大方,釉色润白,青花成色鲜艳,以浓淡色阶区分表现物件之光影变化,使画面仅着一色,但仍具极强的表现效果。该笔筒的纹饰取材于《十八学士图》。其外壁以青花通景描绘了学士们在幽静的庭院中聚会的场景。画面中的学士们身着长袍、头戴冠帽、神态自若,仿佛正在进行一场高雅的文化交流。这些学士或围坐听琴、或观赏画作、或下棋对弈,一派恬淡的世外情怀。
这件笔筒与上一件的不同之处是,除了绘画外,在空白处还以楷书题七言诗四句:“台阁峥嵘透碧空,登瀛学士久遗踪,丹青想出忠良手,不画当年许敬宗。”此诗出自清代《坚瓠首集卷之一十八学士图解》,讲述了唐代初年,秦王李世民设立“文学馆”,揽天下英才,杜如晦、房玄龄、于志甯、苏世长、姚思廉、薛收、褚亮、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十八人入选为“文学馆”学士,时称“登瀛洲”,秦王命画师阎立本绘《十八学士写真图》。后来因为十八学士中的许敬宗支持武后,陷害忠良,故其后以十八学士为题材的作品皆不绘许敬宗,十八学士图仅见十七人而已,此笔筒亦然。
秦府十八学士的故事,自古以来就给艺术家们提供了丰富的灵感。阎立本之后,宋徽宗、李公麟、刘松年、仇英等历代著名画家都曾以此题材进行绘画创作。这个故事原本是为了赞扬那些帮助皇帝治理国家,具有聪明才智的有识之士,有很强的教育意义。最初的图案也是以功臣肖像画为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创作以“十八学士”为主题的作品时,不仅仅局限于表现他们的功绩,还加入了更多的艺术元素,创作者开始更多地关注文人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经分析在古代绘画作品和瓷器纹饰中目前“十八学士”的雅集图案以两种形式出现:第一种是园林聚会形式,一群学者在花园里聚会,饮酒作诗,享受文人的快乐时光。比如南宋洪适的《跋登瀛洲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徽宗《文会图》。第二种是艺术活动的形式,学者们正在进行弹琴、下棋、书法和绘画等文艺活动,体现了他们对美的追求和自身修养。正如明末的张丑所说,历史上各种绘画主题不断创新和发展。从最初的功臣肖像,到后来的丰富多彩的文人聚会画,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和审美趣味。
清代康熙时期,推崇文治的康熙皇帝效仿唐太宗设南书房,召集儒士参与国事。这一时期,“十八学士图”瓷器成为当时的流行趋势。无锡博物院的这件青花笔筒在构图上采用分组的方式,每组人物以对称或均衡的构图方式呈现,使得画面更加稳定和谐。这些学士形象各异,或坐或立,或抚琴或对弈……姿态各异,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同时,通过屏风、太湖石、芭蕉树等周围景物的衬托,营造出画面的层次感和空间感。
无锡博物院作为一座集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其中包括文中提及的这两件清代青花人物故事纹笔筒。“佛殿奇遇”与“十八学士图”作为清代青花人物故事纹笔筒上的两个重要题材,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它们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和绘画的艺术魅力,还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我们对青花人物纹笔筒进行深入赏析,不仅可以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绘画和工艺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还能从中汲取创作灵感。这些珍贵的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现代艺术家学习和借鉴的宝贵资源,推动着中国陶瓷艺术不断创新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