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觉醒文化”的名与实
作者: 黄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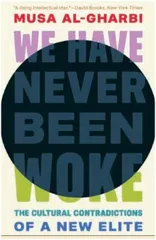
《我们从未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
作者:[美]穆萨·加尔比(Musaal-Gharbi)
出版社: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出版时间:2024年10月
定价:35美元
本书从符号资本家的角度分析了美国觉醒文化的起因,指出觉醒文化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名不副实。
穆萨·加尔比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特朗普的第二届政府甫一上台,就抡起了砍向“觉醒文化”的战斧,其举措包括计划解散联邦教育部(理由是教育部向年轻人灌输“不适当的种族、性和政治内容”),解散并禁止联邦政府及其承包商的“多元、平等和宽容”(Diversity,equity,andinclusion,DEI)计划和部门,取消向学术机构提供对涉及性别、种族等课题的研究资助经费,等等。反对觉醒文化本来就是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对其支持者的承诺。觉醒文化何去何从,正在成为当今美国社会与政治的头等大事之一。
什么是觉醒文化?“觉醒”的英文原词“woke”源自黑人英语,是通用英语单词awake的同义词。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保持警醒”(staywoke)是一句提醒黑人提防白人的警示语。1930年代以后,woke被用来表示美国黑人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觉醒意识。
2014年8月,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弗格森小镇,黑人青年布朗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遭白人警察拦截搜查并被开枪打死。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BLM)运动的活动家开始广泛使用woke一词来提高公众的关注度。白人群体也随之逐渐用它来表示对BLM运动的支持。该词汇逐渐流行,并扩展到种族问题之外的其他议题,例如性别认同与边缘群体权益。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左翼在多个议题上的立场趋于激进,涌现出了一组与woke相关的理念,诸如:美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白人享有白人特权,有色人种长期遭受系统性的种族歧视,尤其是执法机构存在严重种族歧视;女性遭受系统性的性别歧视;个人应该有权认同任何性别,或是不认同任何性别。这些理念就相当于中文所说的觉醒文化。
进入2019年之后,woke逐渐被右翼和部分中间派人士讽刺性地用作贬义词,用以批评左翼。在这种贬义的用法里,该词汇被赋予了如下含义:一种容不下不同观点且充满道德优越感的意识形态,一种僵化的充满审查意味的政治正确。此后,woke-washing和wokecapitalism等词汇相继出现,意指某些企业借助与觉醒文化相关的社会正义议题营销并牟取商业利益,这类行为也被称为“表演式激进主义”。
是怎样的社会背景和社会互动,导致了美国觉醒文化的兴起,以及它在后续发展中的饱受非议?对于这个问题,美国社会学家加尔比的《我们从未觉醒:新精英的文化矛盾》一书,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给出了显得有些偏激的结论:当今美国社会的觉醒文化,只是美国过去近百年中4次堪称“大觉醒”(GreatAwokenings)的左翼文化运动之一。每一次大觉醒运动的肇因都并非被压迫者自下而上的反抗,而是由一类争取在体制中上位的精英人群所推动的。
在加尔比看来,每当经济进入衰退周期,威胁到高学历年轻人的社会地位,在精英体系中处于边缘的成员为了巩固或提升自己的地位,会利用正义和平等的价值理念来对抗精英体系内部的主导阶层。这些挑战者自称代表被压迫者,并以他们的名义为自己争取权力和利益。不同历史时期的被压迫者身份各异,可能是无产阶级和女性,也可能是黑人或性少数群体。
加尔比从精英和普通民众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一种美国社会的历史模式:当普通民众处于困境而精英地位稳固之时,精英可以方便地动员大众站队,支持某一派别;当普通民众处境不错之时,精英需要通过耐心游说来赢得支持;而当精英和普通民众都陷入困境时,就会发生大觉醒运动。在这种情境下,精英会向普通民众发出号召,强调大家都处于困境,并提出解决方案争取支持,而这类解决方案实际上只是帮助处于边缘的精英人群挑战处于主导地位的精英阶层。
加尔比指出,这类向普通民众发出号召的精英人群,其社会身份属于“符号资本家”,即拥有符号并从符号生产中获利的人。换言之,符号资本家从事的不是体力劳动或与实体商品有关的服务,而是数据、修辞、社会认知与关系、组织结构与运营、艺术与娱乐、传统与创新等方面的生产与操控。教育、科学、技术、金融、媒体、法律、咨询、行政管理和公共政策等领域的从业者,大部分都属于符号资本家。因此,每次大觉醒运动最激烈的地方往往是学术界、教育界、法律界、医疗行业、媒体、出版业、非营利组织和娱乐业。
借助这种模式,加尔比剖析了美国近百年来的4次大觉醒运动的起因。
第一次是在19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许多原本认为自己稳居精英阶层、从事高薪体面职业的人,突然发现自己面临极其不确定的未来。这促使他们投入社会运动,以捍卫自己的利益。
第二次是在1960年代后期,美国爆发了声势浩大席卷全国的社会运动,但是与通常的看法不同,加尔比并不认为民权运动、女性解放运动等是促成大规模激进行动的主要因素,而“越战”早已持续多年,也不曾引发大规模抗议。加尔比认为,真正的转折点是美国政府决定从大学生中征兵,当时的白人中产阶级的子女原本计划通过上大学来逃避征兵,让少数族裔和穷人去前线作战。当这一策略开始失效时,大学生们才突然大规模投入反战运动。他们同时将黑人民权、女性主义、后殖民斗争、性少数群体权利和环保主义等都纳入运动的诉求。
第三次是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经济衰退对高学历人群造成冲击从而引发抗议。这一次的运动规模较小,持续时间较短,但是“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这个术语被重新定义并广泛传播,为第四次大觉醒—也就是觉醒文化—奠定了基础。
第四次是从2010年代兴起后持续至今的觉醒文化,它包括了涉及经济议题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涉及种族议题的BLM运动、涉及女权议题的“MeToo”运动等。
对于觉醒文化的发生机制,加尔比从俄裔美国学者图尔钦(PeterTurchin)的“精英过度生产”理论出发,提出了如下见解: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培养了太多受过高等教育、充满抱负的年轻人,但高薪体面的工作岗位远远不足,导致这些受挫的符号资本家指责这个未能容纳他们的体制以及体制内的成功精英,他们试图通过与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结盟,来重新分配社会资源和权力。
加尔比指出,符号资本家群体每次都在大觉醒运动中发动了对体制和特权的激进批判,但是一旦危机解除,这些人便会转身加入他们之前口诛笔伐的体制。这些运动表面宣称帮助弱势群体,实际上并不曾真正改善弱势群体的处境。
例如,面对1960年代后期的社会运动大潮,尼克松在1968年上台后逐步取消征兵制,这一政策直接削弱了大学生参与运动的动力。进入1970年代之后,大学生对政治和激进主义的兴趣急剧下降,这一次大觉醒运动也随之偃旗息鼓。
那么,加尔比的主题思想是不是贬损觉醒文化,以及挞伐符号资本家的虚伪呢?答案其实是否定的。
作为一位在美国属于边缘人群的黑人穆斯林,加尔比并不反对觉醒文化的理念本身;他也并不认为符号资本家的信念是虚伪的,而是认为这些信念仅仅是信念,与任何严肃的行动计划没有实质联系,这些人并未践行自己所倡导的价值观。
加尔比指出,作为精英人群符号资本家所宣称的价值观与实际行为之间的差距,会对许多人产生重大现实影响,尤其是对社会中真正的边缘化和弱势群体。而投身觉醒文化的符号资本家出于自身的真正信念,无法意识到下述事实:他们的行动往往会加剧社会问题,并且引发对他们所倡导的“社会正义”事业的反弹。他们常常会真诚地追求他们所认定的社会正义,但这同时也是在借助社会正义的话语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们始终坚信,自己是“正义”的一方,问题出在那些在种族、性别、性取向等问题上持有“错误”想法和言论的人身上,而后者大部分是社会地位低于甚至远低于符号资本家的普通人。
比如,在美国,黑人的生活境遇整体上确实比白人差,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电视上大谈“白人特权”问题的黑人评论员的生活状况会不如那些坐在家里看电视的普通白人。相反,在美国的贫困人口中,人数最多的其实是白人,但是他们却被觉醒文化塑造成了拥有白人特权的人群,从而被社会削弱甚至否定了获得援助的正当性。这种立场对精英来说非常方便,他们不用为那些白人的贫困承担任何责任。
又比如,在觉醒文化的浪潮中出现了以下现象:大公司花费巨资聘请DEI专家,却对改善穷人生活一毛不拔;以警察暴力执法为理由呼吁削减警察经费的人,大多住在低犯罪率的社区;BLM运动的一些抗议活动演变为抢劫、纵火和蓄意破坏;轻罪不受惩罚,导致盗窃和逃票行为激增。
由此也呈现出了一个深层次矛盾:投身觉醒文化的符号资本家实际上是利用“社会正义”的话语,将责任和成本转嫁给那些实际上从体制中获益较少的人,虽然他们并不是主观故意要这样做的。归根结底,一个群体符号化的姿态或者内心信念,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远远比不上他们的行为模式、人际关系、资源分配等因素。一个人是否把自己塑造成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的支持者,与他是否在现实生活中剥削他人或是维持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也完全是两码事。
概言之,觉醒文化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名不副实,正如本书书名所表达的:“我们从未觉醒”。
本书是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揭晓的一个月之前出版的,当时作者无法预见大选结果,更无法预见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对于觉醒文化的铁腕打压。例如,特朗普政府的教育部宣布只保留调查学校中涉及残疾人的歧视事件,不再像以往那样调查涉及种族、性等其他因素的歧视事件,这等于为学校里与种族和性有关的歧视行为开了绿灯。
悖论在于,特朗普政府对于觉醒文化的打压,恰好为美国社会更具星火燎原之势的大觉醒运动创造了条件。如果加尔比所言非虚,当精英和普通民众都陷入困境时,就会发生大觉醒运动,那么,特朗普政府的解散DEI等措施会让一批原本已经进入体制的精英再度面临不确定的未来;另一方面,纵容乃至鼓励对于女性、有色人种、性少数群体的歧视,令这些群体步履维艰,苦不堪言—下一步必然是重演精英向普通民众发出号召,强调大家都处于困境,并提出解决方案争取支持的剧本。觉醒文化原本注定会逐渐消沉,特朗普政府却正在以洪荒之力促成它的复兴。
解读/延伸阅读

《二等公民:精英阶层如何背叛美国的劳动男女》
作者:[美] 巴蒂亚·温加尔·萨尔贡(Batya Ungar-Sargon)
出版社:Encounter Books
本书剖析了当今美国的阶级鸿沟,以及改善美国劳工阶层处境的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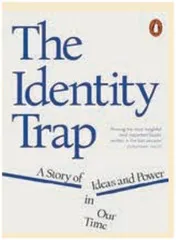
《身份陷阱:我们时代的思想与权力的故事》
作者:[美] 亚沙·蒙克(Yascha Mounk)
出版社:Penguin Press
本书指出,在当今美国,左派对于身份认同的非理性痴迷已经成为一道陷阱,使他们无意中成为MAGA运动的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