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乘》——在日本出版的山西清代期刊
作者: 王泽周《晋乘》是山西留日学生、同盟会成员为了继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八日(1907年9月15日)在日本东京创办的又一份期刊,既是山西同盟会成员在海外创办的最后一份重要革命刊物,也是山西新闻报业出版最早的期刊之一。
《晋乘》的创办情况
《晋乘》的创办经过,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景定成在其代表著作《罪案》一书中是这样记述的:“因《第一晋话报》出到第9期,同乡会分裂不能续出。于是我又邀集几个同志,商议另组织一种杂志。大家想名目,我以浙江有《浙江潮》杂志,湖南有《洞庭波》杂志,陕西有《夏声》,四川有《鹃声》,皆就地理、历史立名,想到了《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这《晋乘》与《春秋》并列,亦是一部光荣历史,何妨用这个名称组织起来,大家很赞成……大家凑了些钱,出了三期,因为经济缺乏停刊。”这在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十四日(1908年2月15日)出版的第二号《晋乘》中可得到印证。在这期《晋乘》中有一页“夏声杂志出版预告”,提到“第一期已脱稿,不日出版。”《夏声》第一期出版于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1908年2月26日)。
该刊的刊名,为何取用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史书书名,创办人之一的景耀月以“大招”为笔名,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万余字的论述文章《晋乘说》,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就古人对乘字的解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联系晋文公尚武立国,建立霸业的功绩,对乘字当初的含义以及晋史为何叫做“晋乘”作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乘字原本是“兵车之义”,所谓晋乘,说的就是晋国的军队,国家的历史。刊名取名《晋乘》,在此有怀古之意,目的是为了激发读者“爱国爱种的热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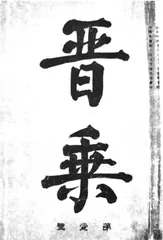
《晋乘》为大32开本,规定“本杂志月出一号”,实为不定期出版。第一号用小字印刷,后为读者阅读方便,自第二号起改用大字印刷。刊物大多采用白话,文字通俗易懂。设有图画、论著、晋语、文艺、杂俎、附录等多个栏目。其中,图画部分包含有山西省地图及重要人物的画像;论著部分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议题,旨在发扬国粹,提倡自治,奖励实业,收复路矿等。试图通过这份报刊来唤醒民众,共同拯救国家和民族,通过传播革命思想和新文化,为推翻清廷、建立共和贡献力量,体现了创办者对山西乃至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积极探索。该刊与《第一晋话报》一样,为了学习生活需要及保护撰稿人,刊发文章多使用笔名,如大招、晋仍、古唐、易淊、SR生、莫愁、猛蹴、秋心、梦周、垂钓翁、磨锋等。
《晋乘》虽然只出版了3期,仅存在了9个月,却在山西新闻报业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晋乘》创刊号,山西民间藏有完整的三期《晋乘》。创刊号由山西省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副会长曹保珠先生收藏,第二号由山西省报业协会集报分会顾问郭华荣先生收藏,第三号则由山西省报业协会集报分会常务副会长王海勇先生收藏。《晋乘》作为山西同盟会成员在日本创办的最后一份重要的革命刊物,它反映了当时山西留日学生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对山西乃至全国的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者,还记录了山西早期的新闻、报业发展。《晋乘》既是山西革命历史中的重要刊物,也是山西早期新闻报业的代表之一,对于研究清末民初山西乃至全国的革命史、文化史、新闻报业出版史等具有参考价值。
《晋乘》主创人员
《晋乘》的创办人员基本是《第一晋话报》的原班人马,有景定成、景耀月、王用宾、谷思慎、荣福桐等。但从《晋乘》办刊的实际情况来看,景耀月似乎起的作用更大些。在《晋乘》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中可看到,通信联系人是景耀月。封二的《社告》指出:“来函即邮寄日本东京神田区西小川町一丁一目一番地山西同乡会事务所交景耀月收。”封底的《本社通信所》指出:“凡海内外通函本社或来稿及订报,诸君请迳函日本东京神田区中猿乐町五番地胜村方内景耀月处。”纵观第一号的稿件,景耀月的文章数量多,占比大,分量也重。如论著有《发刊词》《晋乘说》《晋语》,文艺栏目的诗词《犬狼吟》,李烈士(李培仁)《祭文》等署名皆为景耀月的别名大招。附录栏目还有署名景耀月的《斥晋报记者程淯之缪妄》一文。该期正文共82页,景耀月的文章占到了40页之多。本文仅对景耀月生平作一介绍。
景耀月(1881—1944),字瑞星、秋陆,号太景耀月昭,别署大招、帝召、秋绿,笔名迷阳庐主、太原公子等,中国近代教育家、革命家,追随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奔波海内外宣传发动革命,是推翻封建帝制的民主革命元老。
1902年景耀月就学于山西大学堂。1904年公派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律。1905年与同仁创办《第一晋话报》。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为同盟会山西支部负责人之一。1907年9月与同仁又创办《晋乘》杂志,并任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编辑、记者,倡言革命。1908年2月,与赵世钰在东京创办《夏声》杂志,宣传革命,并与于右任等发起晋豫陇学会。1909年任留日学生中国财政研究会会长。同年获法学学士学位回国,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参与编辑于右任创办的《民呼报》,主办《民吁日报》,并与柳亚子等参与发起成立“南社”,进行革命活动。《民吁日报》被查封后,流亡国外,辗转赴越南,在西贡、河内等地组建同盟会分支机构,嗣复渡日本,与孙中山、黄兴等筹划举义。

辛亥革命爆发后,景耀月以山西军政府代表身份参加各省代表联合会议,被选为议长。1912年1月1日,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中外记者聚集在总统府,都想尽快向外界报道中华民国成立这一重大新闻。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未曾准备妥当。情急之下,大家责成负责文秘工作的秘书长林森草拟。林森草拟的两稿均未获得代表通过。随后,在场诸同志提议:“还是请瑞星(景耀月字)赶紧写一篇”,以应开国大典之急用。景耀月来到一间侧室,挥毫疾书,文不加点,一挥而就。此为中华民国成立之第一号重要文告。在场同志传阅后,心中佩服,均表示赞同,孙中山也表嘉纳。此后,一连三月,景耀月与其他革命同志主持并操办了当时的革命和开国诸事宜。他起草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这两部法律是创建民主共和政体的最早宪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具有里程碑意义,由此奠定了景耀月在我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民国初创,他被任命为教育次长和代总长。在主持教育部工作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师范教育令》《国民教育令》等法律法规。1917年在山西、河南组织靖国讨逆军,反对“辫子军”张勋复辟,被推任为总司令。1926年北伐之后,景耀月离开政界,致力于学术研究,担任过北平天主教机关报《益世报》的编辑。后执教于上海中国公学、北平大学法学院、东北大学等院校,专心著述,为国育才,弟子遍布南北。
景耀月在学术上,亦有高深造诣。鲁迅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曾称他是:“当代古典文学的最佳作者”。景耀月与国学大师章太炎有“南章北景”之誉,与同盟会元老景定成有“山西二景”,和著名学者黄倪亦有“南黄北景”之称,谓“黄以辞夸,景以气行”。景耀月一生写作,不下数千万言,其中包括许多我国革命历史上的重大文献。而其古典诗词,亦为近代名家,约二万多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景耀月一家困于沦陷后的北平,日本人企图强其出掌伪华北政权,遭景耀月拒绝,并暗中与学人创立夏学会,进行抗日活动。1944年4月28日,遭日本人迫害在北京逝世,终年62岁。中共中央在重庆公开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曾发表景耀月逝世的消息。
宣传民主革命思想
《晋乘》作为辛亥革命时期的舆论阵地,在山西出版革命报刊确有很大困难。从该刊的诸多文章可以看出,山西同盟会员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积极与山西省的革命运动和革命党人保持密切联系,播撒革命火种,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在政治上,《晋乘》的作者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民的民族自觉力和竞争力,认为清政府已是“亡中国者”的政府,主张推翻清朝统治。而要使国家富强,还必须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当时,全国范围的收回利权运动正如火如荼,《晋乘》态度鲜明地支持山西的保矿运动,对山西人民在“争回矿权”斗争中显示出来的团结战斗精神给予了热情赞扬。对于如何提高国民的民族自觉力和竞争力,《晋乘》在第一号的《发刊词》中提出要“开启民智”,“教我邦伯叔兄诸姑姊妹,一个个晓得爱国、晓得好学、晓得尚武,”就是要“激发人们爱国的热情,开浚人们的知识,增强人们的体质,养成人们独立之精神、合群之性质、自主之品质、进取之能力、协图公利之思想、不受外界抑制之气魄。”
《晋乘》还对当时的立宪予以了否定与抨击。如第三号的“笑话集”栏目中,莫愁(景定成)在《释宪》一文里写到:“有几个人,在一处闲谈时务。一人道:现在人都好谈立宪,有许多宪政令,有许多立宪党人,到底都是什么宗旨?一人道:孔子宪章文武,怕是学圣人的。又一人道:诗云宪宪令德,怕是学贤人的罢。一人独摇头道:都不是,诸君不通《小学》故耳。憲(宪的繁体字)字本是个象形兼会意字。众问何解,他道:宝盖头像红顶,丰像花翎,四为横目,心即心,合而言之,就是心儿、眼儿都用在红顶花翎上。”这段看似笑话却对当时的“立宪”给予讽刺。
在经济上,《晋乘》的创办者因受日本的影响,主张实业救国,使国家富强以利于抵抗列强的侵略,挽救危亡。如第一号笔名SR生的文章《实业与山西之关系》中,就认为“实业两个字,为现今世界生存的一个大要素,不研究实业的国家,万不能独立,不研究实业的人民,万不能生活。”如果实业不能发展,国家的路权、矿权、专卖权、制造权就会丧失,这样“国家不能独立”,人民也要做“外人的奴隶。”

那么,如何抵抗外来的经济侵略呢?在第二号笔名垂钓翁的文章《社会概论》中说到,“中国现在是危到十分十厘了”。愿大家赶紧“合而设立工厂”“广置机器”,外国人“有何物,我即仿造何物”,外国人“有何能,我即仿学何能”“直到我们的货物,能抵住洋货之来方可”。但是光有此仍不够,在第一号笔名古唐的文章《设铁道必先讲经费备人才说》里,作者还认为,还必须发展实业教育,培养自己的技术和管理人才。针对山西的情况,则认为,“我们同蒲铁路若要兴筑,不可不急急地先设一铁道学堂,养成一班管理人员,”对于铁道学院的毕业生“量其程度授职业”,做到“所用即其所学”,认为这些人是自己培养的,有一定专长,有爱国思想,经营铁道“不用问这营业情况,一天是比一天发达的。”这些“实业救国”的主张,显然是受了日本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对当时爱国的学生心理影响很大。像日本那样发展实业从而富强起来,成了当时不少留日学生的共识。
在文化上,《晋乘》创办者以“发扬国粹”为宗旨,宣称“发扬国粹”之意,是与章太炎“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相同的。在第三号大招(景耀月)的《复古社序》一文中,作者认为“今日者,国家丧乱,种性式微,不有怀旧之德,其何以振励国人?”“夫中原文献所以相禅迄今者,皆赖一代抱残守厥之士之死靡他,所谓史家广其事,儒家守其典者。今者去古未远,故家流风,犹有存者尚遂不讲,他日故老雕零,残经蠹败,时迁代异,谁复识有中州文献者?”这些同盟会成员,他们在民族危亡之际,除希望从西方学得知识外,还设想从中国的传统中去寻找思想武器。如在第三号《晋乘》上,就有一则景定成、景耀月等六人发起的成立“复古社”的广告,宣称:“本社同人,闵国粹之陵夷,古典之不振,组为此社,广延同志,专研究古学,以与新说相融会。”可见,他们对中西文化的态度,遵循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
《晋乘》和《晋报》

1902年,开创了近代山西新闻报业出版之先河的《晋报》创刊。而《晋乘》的创办,直接导致了出版五年之久、有“三晋第一报”之称的《晋报》停刊。《晋乘》导致《晋报》停刊的原因,始于《晋报》的创办者兼主笔程淯,东游日本进行考察。
1906年,程淯奉山西巡抚恩寿之命,为创办山西劝工陈列所和医学堂,而赴日本考察工艺、医学。《晋报》与程淯由此进入了山西留日学生的视野。程淯在日本考察期间,散播对山西留日学生不实言论。山西留日学生认为程淯主办的《晋报》内容乏善可陈,百姓不爱看,没有遵循《晋报》“开通风气,速开民智,启佑民聪”的创办初衷,而且报纸价格昂贵,官方摊派。因此,山西留日学生认为该报为“升官发财之计”,无“国民分内应尽之责任”,成为程淯获利的工具。再加上程淯作为主笔,在《晋报》上反映出来的政治观点与山西同盟会成员有所不同,因而双方产生了多次论战。针对程淯在《晋报》上发表的《正告欲与本馆为难者》《山西学界之怪谬》等文章,山西留日同盟会成员纷纷发表文章予以驳斥,如景耀月的《斥晋报记者程淯之谬妄》,王用宾的《与程淯书》《正<山西学界怪状>之谬》,解荣辂的《解庶常致晋报馆主笔程淯书》,晋仍的《晋报宜改为山西政教官报说》,以及《日华新报》上发表的《程淯之丑历史》等。山西同盟会成员与程淯论战的文章,均刊登在了1907年9月15日出版的《晋乘》创刊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