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丝挽成岁月的花
作者: 张孝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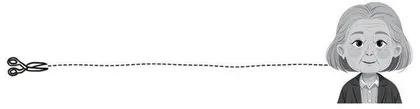
在我读初中的那三年,母亲一直担任着家庭理发师的角色。每当她拎着工具包,站在院子里中气十足地吆喝:“剪头发了!”我们的“家庭美发馆”便准时“开业”。
父亲一直留板寸,妹妹年龄还小,只需要简单修剪,正值青春期,审美觉醒中的我则是个“刺头”。当时流行的齐刘海、厚鬓角,即后来被定义为“非主流”的发型,其实非常考验理发师的技术。刘海的长度要刚好,过长会被老师批评,过短则显得傻气,还需要适当地留出层次。这可难坏了母亲,她不会剪时兴的发型,于是,我的刘海不是短了就是歪了。
剪完头发的第二天,同学们总会笑盈盈地打趣我:“阿姨又给你剪头发了?”我只好红着脸将刘海全部别起来,露出光溜溜的额头,在齐刘海群中十分扎眼,就像我身上的老式翻领衬衫,在青春洋溢的女孩子里格格不入。
于是我和母亲的争吵愈加激烈。我嫌弃她蹩脚的手艺,她则坚持认为露额头更好看。后来,争执不下的两人陷入冷战。我刻意避开“家庭美发馆”的“营业时间”,等到刘海终于盖住眼睛,揣着午饭省下的二十元钱去镇上的理发店。当我终于拥有了潮流发型之后,连脚步都轻快许多,只是在我面对母亲时,仍不免有些心虚。好在她只是瞥了一眼,便转过身继续忙碌,消瘦的背影微微有些佝偻。
那时我的生活费并不宽裕,爱美的代价是“消失的午餐”。饥饿像无数只蚂蚁,啃噬着我的胃、胸腔和大脑。好不容易熬过头脑混沌的一天,我冲回家端起饭碗风卷残云。
母亲看我这样,啪地摔了筷子,问:“你非得剪这个头发吗?”我嘴里塞满饭粒,喉咙却像被堵住了,怎么也咽不下去,终于哇地哭出声来:“别人都能剪,别人都能穿新衣服,为什么我不行?”饭粒随着我的声声控诉四散奔逃。
这场争吵以我摔门躲进卧室收尾。后来,我在半梦半醒间听见母亲的抽泣,父亲踮着脚尖进来,在黑暗中摸索着打开我的书包,轻声叹气,又轻声关上了门。
第二天,我从书包的夹层里翻出来二十元钱,皱巴巴的,边缘起毛,无声地宣告着它的来之不易。我紧紧攥着那张纸币,直到手心冒汗,指甲深深嵌进手心。
我和妹妹逐渐长大,祖父母却日渐病弱,一家人的生计皆系于父亲外出务工的微薄收入,原本艰难的家计更加窘迫,因此必须尽量节省开支,头发只能自己剪,衣服时常穿到泛白抽丝。青春期的敏感疯狂滋长了我内心的自卑和虚荣,直到母亲的哭泣和父亲的叹息刺痛心脏,我才彻底清醒。
我终于放弃了齐刘海,几天后经过理发店时却看见三婶带着堂妹在剪刘海,母亲正和她们聊天,眼睛却一直盯着理发师翻飞的剪刀。我瞠目,她这是在偷师学艺吗?
那天母亲傍晚才回家,双手揉搓着衣角问我:“再试一下剪刘海可以吗?”像是担心我拒绝,随即又提高音量:“你放心,我今天学会了。”半个小时后,看着镜中“鲨鱼牙齿”刘海,母女同时陷入沉默。半晌,我咳嗽两声,说:“挺好的。”
母亲十分懊恼,晚饭都没吃几口,她找出那件被我说土气的衬衫,在衣领上各绣上一朵小花。很多旧衣服就是这样经过她的巧手改造焕然一新的,陪我和妹妹度过数年时光。白炽灯明晃晃的,映得母亲发丝发白,我恍惚看到遥远的未来:我和妹妹长大,父母老去,他们满头青丝在数年的悉心哺育中耗尽神采。
这一刻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了。在贫瘠的物质环境中,父母依然用爱和巧思编织出七彩鲜花,点缀着单调的岁月。这份爱会滋养我们的人生,终有一天幼苗会长成大树,自有一方天地,也能庇护扎根的土壤,再不受风雨侵蚀。
编辑|龙轲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