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面事
作者: 惠文将上面这首打油诗打在公屏上后,梁章就下播了。
接下来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善后:收拾面摊垃圾、放干净煮面水、将上万元的直播设备送给翘首等待的陌生人,以及注销自己48万粉丝的直播账号。
做完这一切后,他打心底高兴。
生活就像发酵的面团
这里常下雨,但雨势从不大。
淅淅沥沥的雨落在日益稀少的红瓦屋檐上,发出轻微的响声。这时,有人会拿出一个搪瓷盆,接屋檐流下的雨水。8岁的小鱼不明白为何这样做,他只记得在雨声中,梁章看他丢石头,他看父亲揉面。
日子虽忙碌,但梁章很知足。他的手擀面虽无师从,但严选了当地头茬小麦,手工揉捏千百遍,不放任何香料和味精。汤底则是用鸡架骨、猪筒骨等加上几十种香料熬制。一碗面满是小麦的清香和汤底的醇厚,劲道、量足、回味无穷。

梁章为人低调,面对常人的调侃或抱怨,他都像面团一样轻松揉开,然后憨厚地一笑,露出整齐的牙齿。
这个面摊用二十年时间“长”成了小城里的“早餐大树”。
早晨摸黑出摊,卖到下午2点多,随着最后一碗面被端上桌,梁章的一天三四百元的生意便打烊了。他关了火,把面摊往那一搁,自有隔壁卖菜的老板帮忙照看。
随后,他骑上“小电驴”,慢悠悠地拐到小鱼的小学门口,接儿子去钓鱼、打水漂、编蚂蚱,小日子被他精心“揉”得温暖如火。
东溪的水面上浮着个月亮,月是碎的。小鱼赤脚蹚过河,梁章在帮他捉萤火虫。人们说梁章这辈子像截木桩被雷劈成了两半—前半截埋在地里,后半截落进面盆。面盆里揉的是他和小鱼的现在和未来。
人们常说梁章没啥大志向。梁章心想,啥是志向?每天把生意和家庭照顾好,不蝇营狗苟、不求人,不挺好吗?如果真有买卖给他,他还怕无福消受。
这天,市场里来了位“直播客”,把补光灯戳进餐桌上的裂缝里,用手机对准他揉面的手。案板的裂纹在屏幕里放大得像条河沟……
“老板很实在啊”“一看老板就揉得一手好面”“香味从屏幕里飘过来了”“这位大叔真干净,在这种小市场真难得”……几个网友插科打诨地夸梁章,直播间里热闹了起来,在线人数眼看着从几十个增加到3 250个。
直播客的喜悦溢于言表,兴奋得连面前的面条都顾不上嗦。他仿佛中了彩票,眼睛紧紧盯着梁章,就像盯着一台正在开奖的机器,满心期待着即将揭晓的结果。
谁能想到,梁章开了直播后,生意就像开了锅的沸水,热闹非凡。外地顾客驱车几十公里赶来,就为了吃一碗5元的面,然后拍照发朋友圈。面团砸在案板上的闷响,渐渐被直播间里打赏的“飞机”声淹没。
后来,穿紧身裤跳舞的人来了,胸口碎大石的人也来了,甚至有人开着红色卡车,带着烟花停在后半夜的面摊旁。人们举着自拍杆,大口吃着面,筷子在镜头里上下翻飞,像是耍红缨枪的把式。
梁章的命运被推入了大买卖的旋涡。他忙得不可开交,每天要醒的面是之前的3倍,还要提前3个小时准备熬汤、备菜,一直忙到天黑,送走最后一拨打卡的客人。白天和黑夜在他手下被揉成了半透明的面筋。
小鱼记不得这是第几次自己一个人放学回家。他更想告诉梁章的是,现在他每天早上不用闹钟就能自然醒,能在酸臭的抹布味中煎鸡蛋,还能对着手机核对课后作业。但梁章完全没有意识到小鱼的变化,他没时间。他也没注意到隔壁商铺老板的白眼、越来越少的老主顾,以及即将到来的掌声、西装和红绸带……
他一门心思地在研究怎么直播,如何更快地揉面1 305下。身边的一切都在他疯狂揉擀的面团中,在沉默,在发酵……
荣耀与刺挠
穿着西服坐在台上,梁章浑身刺挠。
为了大力推动当地网红经济,他被推选为典型人物,在一场名为“大力发展特色经济,提振全域高质量发展”的专题报告会上,坐在主席台中央分享经验。
接过“高质量发展经济标杆”的荣誉证书时,他心里清楚:种麦子自己是一把好手,但至于老天爷啥时候下雨,自己可猜不到。尽管如此,他还是硬着头皮完成了这场半小时“干货满满”的讲座。
小城的市场是真的大变样了。被商贩反映多次没有解决的路基坑洼问题,一夜之间铺上了平整的柏油,建了一个大型的停车场;移动的5G信号车24小时值守,提供上门流量服务;沿街的门面被要求统一样式、统一字体重新设计;所有摊贩被强制要求卫生检疫,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所有商户还领了一项考核指标,接受大众监督,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不能有差评。
重装后的市场,井然有序。梁章的摊位被邀请到了C位,大红条幅一拉,北风吹过,哗啦啦像一条唱歌的经幡。桌椅板凳焕然一新,被码得整整齐齐。
毫不夸张地说,此时在上面加个顶盖,那就是有模有样的大饭店了。
梁章的生意更红火了。他和几个网红组成了传播矩阵,按流量和成交业绩分成。他还接受了快消品专家的建议,推出了“面条哥”调料包、咸菜包、卤牛肉等产品,线上线下同步销售。
然而,小城热闹后,小城里的人难受了。外地人蜂拥而至,原本平静祥和的市场被外地车辆挤满,扎堆地吆喝网红产品。原本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曾经雷打不动的早餐面条,也避之不及地让给了外地人。梁章迎来了新客人,却失去了老主顾。就连一直顺手帮忙的隔壁摊主,也受不了网红们的侵扰,丢下一句“你现在发达了”,另寻出路去了。

小城生意变好后,平静也被打扰了。蜂拥而至的游客和外地商户,带来了税收、流量和新鲜的商机,让小城原本自给自足的平衡体系却被打破了。那些靠手艺养家糊口的小本生意人,像撒在地面的面粉一样,被洪水一样的流量一冲而散。人人都想成为“面条哥”,但现实却是高不可攀,生活每况愈下。
梁章接受了“网红”身份的变化,但接受不了身份的“灼烧”:从一个专注于手艺的工匠,变成了八面玲珑的生意人。
生活和生意的辩证法,成了小城发展的哲学命题。
如果当时
梁章第一次意识到,周围的一切正在失控地滑向深渊,生意也出现了新的问题。尽管每天的营业额不断攀升,但他发现每月的利润却没有明显增长。原来,他合作的几个网红专门找了一批“演员”,每天只排队、不吃面,伪造流量和业绩,这让梁章感到被欺骗。
他与合伙人也产生了分歧。合伙人认为梁章的品牌效应已经起来了,所以想把面做成标品,对外以“面条哥”的名义开放加盟,并许诺“1年利润翻10倍,3年上市”的资本计划。做标品的第一步是涨价;第二步是建中央厨房,把和面这个程序机械化。这下好像戳到了梁章的心尖,生疼。
是的,梁章觉得自己像是一个装满了各种欲望的面粉口袋,想装进去新东西,就必须拿出来旧东西。那些珍贵的旧时光,正一点点流失。
做直播的这几年,他像是穿着一身珠光宝气的袈裟奔跑。那些串成珠光宝气的珍珠、玛瑙、翡翠,是自己的朋友、老主顾,和自己的本分、务实。而现在自己跑得太快,宝石一件件地被抖落,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已形单影只。
他获得了荣誉,失去了安宁;得到了金钱,失去了情谊。或者说,他熟悉的梁章已经“不存在”了。
梁章第一次停业一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认真盘点这几年的得失。他之所以能走到今天,除了运气,靠的还是二十多年本分地揉面、抻面,从不掺假,用手艺赢得顾客的信任。他能凭手感判断面是否揉到位,凭顾客的穿着判断他们喜欢的面的粗细和口感。这些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生意经。
顾客在他这里吃的是一份信任。人不可能一辈子走路捡到钱,但人需要一辈子走路。认真做面就是秦章一辈子要走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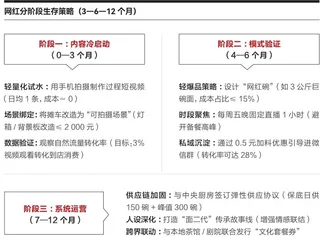
他又想起日本的那些手艺人,有人靠做简单的饭团成为世界名吃,有人靠做凳子传承几代人。对他们来说,时间不是静止,而是停驻。他们不是拒绝变化,而是守持初心。
流量就像酵母,让他的生意如面团般快速发酵,但他的生意从来不是靠“快”赢得口碑。他的生意就跟脚下的小城一样,需要慢慢生长,一起成长。面摊虽小,经营它,就是经营人心。
再回首
梁章决定关掉直播,送掉设备,这只是他改变的开始。他辞去了当地给他的各种荣誉,为儿子请了假,又买了两张飞往欧洲阿姆斯特丹的机票。
他曾刷到过一段视频,视频里阿姆斯特丹的街头,人们骑着二八大杠自行车,穿梭在粗糙的石板路上,衣着朴素却面带微笑。沿街的商铺没有喧嚣的喇叭声,也没有夸张的招牌,顾客们或安静看书,或轻声交谈,生活仿佛被按下了减速键。
那是他向往的生活—在静止的时光里,重新与儿子沟通,找回那个迷失的自己。
回顾这几年的直播生涯,梁章觉得自己仿佛活出了另一段人生。如今回头再看,这段经历无比有意义。他想好了,还是继续在小城做面,把这两年学会的科学化流程和营养概念,融入自己的生意中。至于直播嘛,他想了想还是算了,都是熟人,见面一声招呼,不比镜头里“搔首弄姿”更自在?
然而,新鲜事物随着直播业态的接入接踵而至,小城还是流动起来了。
还能回得去吗?梁章在问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