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存在主义视角下《无声告白》的解读
作者: 胡群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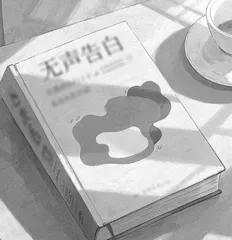
《无声告白》是美籍华裔作家伍绮诗发表于2014年的长篇小说。小说围绕莉迪亚之死展开,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个跨族裔家庭在美国主流社会中的生存状况和困境,探讨了身份危机、种族、家庭以及个人道路等问题。
小说的主人公詹姆斯是美籍华裔,一直渴望于融入美国社会,在大学任教期间与追求与众不同的白人女孩玛丽琳相爱、结婚并育有三个孩子,其中二女儿莉迪亚因为长相酷似玛丽琳而备受夫妻二人的关注,他们将自我个体实现的愿望都重压在莉迪亚身上,最终摧毁了莉迪亚的心理防线,以致她不幸溺水而死。故事的结尾,家中所有人也因莉迪亚死亡最终领会到存在主义是解决生存困境的钥匙—人的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
萨特存在主义哲学主要包含了三个基本原则:一是“存在先于本质”;二是“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三是“自由选择”。《无声告白》中对于个体存在问题的关注,对主体超越性的书写,对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以及族裔关系的哲学式思考,都反映出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明显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特征。本文将从萨特存在主义的角度出发,探讨《无声告白》中体现的荒诞的世界、自我选择、超越性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并具体分析书中人物的困境,以及他们在经历痛苦后作出遵从内心的自我选择和主体超越,以期为广大读者的人生选择提供一些借鉴与参考。
一、荒诞的世界
萨特存在主义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是痛苦的。在他看来,“主观性林立”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必然存在冲突、抗争与残酷,充满了丑恶和罪行,一切都是荒谬的。而人只是这个荒谬、冷酷处境中的一个痛苦的人,世界给人的只能是无尽的苦闷、失望、悲观消极,人生是痛苦的。他的这一观点在《无声告白》中多次被表现出来。
(一)社会中的荒诞
1.种族歧视
在白人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华裔长期遭受种族歧视,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处于边缘地位。种族矛盾在美国一直存在,直到1943年才废除《排华法案》。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詹姆斯始终自卑敏感。华裔身份给他带来的危机与焦虑一直都存在于他的生活中,甚至传递到下一代人身上。
2.女性困境
20世纪70年代正值世界范围内女性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当时更多美国女性争取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虽然女性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她们仍然无法脱离传统社会思想所赋予的贤妻良母角色。在女性争取平等的道路上,传统思想和家庭牵绊往往是其无法成功的主要原因。《无声告白》中的玛丽琳便是当时女性的典型例子,她虽然成绩优异、能力出众,但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潜移默化着玛丽琳,她最终还是向现实妥协,不仅回归了家庭,同样原谅了出轨的詹姆斯。
(二)无法抗争的宿命
在《无声告白》中,作者伍绮诗隐隐约约流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宿命观,特别是在小说人物命运的安排上,伍绮诗赋予小说人物悲惨的境况,将人物的命运设置为在既定的格局里面不断挣扎,这种挣扎在伍绮诗的宿命书写中是无果的,具有浓厚的悲剧意识,作品中每个人物都逃不掉命运的手掌心。
1.挣扎无果的宿命
《无声告白》中的詹姆斯虽然出生在美国本土,“但他从不觉得自己属于这里”。从小到大,他的一副中国面孔总是招来他人猎奇审视的目光。他的父母身份卑微,工作艰苦。他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考上了哈佛大学,却因为华裔身份而不能留校任教。当白人玛丽琳向他张开手臂时,他以为美利坚终于向他敞开了怀抱,然而到头来仍是一场空。即便获得高校终身教职,学术成就的光环依然未能驱散他在异国土地上的疏离感。
《无声告白》中的玛丽琳是一位聪明美丽的白人女性,她凭借自己优秀的学业成绩进入哈佛大学,并努力成为一名医生。她一直追求着与众不同,她不顾母亲的反对嫁给了詹姆斯,甚至不惜与母亲决裂。然而,琐碎的婚后生活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她从独立自强的少女变成了顾家的妻子。她也曾抛开一切,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可是终究无法逃脱命运的魔爪—孩子的牵绊,使她再一次回归家庭,彻底地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2.轮回的宿命
伍绮诗不仅安排詹姆斯和玛丽琳的悲剧,就连她们的孩子也逃脱不了命运的宿命,他们的人生充满了宿命感。可以说,《无声告白》中的一家人都被神秘的宿命所操纵,他们在荒谬的社会里不断挣扎,与命运不断抗争,从而构成一个绝望的世界。
莉迪亚的悲剧命运是宿命观的一种强烈表达。詹姆斯和玛丽琳的悲剧是直接导致莉迪亚悲剧的一个关键点。莉迪亚遗传了母亲的蓝眼睛和父亲的黑头发,使她成为父母最喜欢的孩子。詹姆斯在歧视与孤独中长大,所以渴望莉迪亚能够拥有朋友,融入美国社会。玛丽琳则将因家庭牵绊而没有实现的医学梦寄托到了莉迪亚身上。然而,莉迪亚对母亲的“医学梦”并不感兴趣,同样,她虽然拥有蓝眼睛,但是在周围的小伙伴看来,她还是“异类”。她不断地挣扎,父母的期望与她实际情况之间的矛盾使她不堪重负,最终沉入湖底。
内斯是詹姆斯和玛丽琳的大儿子。作为一个华裔,内斯很难确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他在社会中被边缘化,即使在家里,他也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因为他的父母似乎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莉迪亚。他试图通过逃到哈佛大学来抛下所有人和事,包括莉迪亚,然而莉迪亚的死亡把他拉回现实。他不断抗争,却仍摆脱不了轮回的命运。
二、自由选择与承担责任
“存在先于本质”是萨特存在主义的核心命题。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将“存在”分为两种:“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自在的存在”是一个物体同其本身等同的存在,这是物的存在方式;“自为的存在”同意识一起扩展,而意识的实质就在于它永远是自身,这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个人意识,有能力作出选择。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实现自身的存在与价值,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尽管詹姆斯一家处于荒诞的世界,但他们仍然选择勇于反抗他们的命运,最终在自我选择中找寻到了自己的价值。
(一)詹姆斯的自我肯定
对于华裔詹姆斯来说,他一生中做了两个重要选择:一是极力融入美国群体;二是“过度的爱”。詹姆斯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了自己孩子身上,殊不知这“过度的爱”却使莉迪亚受到了伤害。到最后,莉迪亚的死亡引发了严重的家庭危机。玛丽琳愤怒的话语让詹姆斯回到了过去的痛苦与迷茫之中,他开始选择出轨来麻醉自己,欺骗妻子来安慰她,然而当妻子发现这一切后,他逐渐开始醒悟,意识到家庭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曾经是一个自卑敏感的人,然而经过这次事故后,他终于人生中第一次审视自我价值,不是白人眼中的黄种人,不是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而是家庭当中的顶梁柱,是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
(二)玛丽琳的自我觉醒
受单亲家庭及母亲的影响,玛丽琳不愿意再重蹈覆辙母亲的人生,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是她一生的梦想,玛丽琳为此不懈的奋斗。即使在与詹姆斯结婚后,玛丽琳仍未放弃追求医学梦想,试图通过事业摆脱生活的平庸。她曾短暂安顿好家庭事务后选择离家进修,重新投入医学学习,却因意外怀孕再次中断了个人理想。在无奈放弃职业生涯后,她将自己未竟的梦想寄托到了莉迪亚身上。然而,这种以爱为名的沉重期待压垮了莉迪亚,最终导致莉迪亚在重压下走向悲剧。伴随着莉迪亚的死亡真相的揭示,玛丽琳终于明白了爱是什么—爱不是控制,而是理解与宽容。玛丽琳的自我觉醒也表明她也终于正视自己与家庭,选择继续和全家人生活在一起。
(三)内斯的自我寻路
内斯是一个勇敢的人,面对不公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他迷茫过、自卑过、痛苦过,但依旧勇敢地和世界对抗。玛丽琳离家的那段时间,内斯爱上了宇航员这个职业。即使被父亲打,内斯也没有放弃研究宇航员。同时,相较于莉迪亚和詹姆斯,他并没有因为玛丽琳的离开放弃生活。他也会因杰克说母亲不要他时咬牙切齿地让杰克闭嘴,这和詹姆斯面对邻居艾伦夫人调侃时的躲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玛丽琳回来后,家里的重心向莉迪亚倾斜。内斯被母亲忽视的不平衡让他把莉迪亚推入了水里。但是,内斯很快就意识到,这不是莉迪亚的错,他把她拉上了岸,并且一直照顾着她,守着她的秘密。总之,内斯并没有因为家人的偏心而自暴自弃,没有觉得自己是“东方人”就应该忍气吞声,他积极地面对命运的挑战,寻找自己的出路。父母强烈的期待与过度的爱成为他沉重的负担,因此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自己的未来上,于是他选择离开家庭,在自己的梦想里遨游。
三、主体超越性
对于萨特来说,自由最重要的是意识对存在的超越,如果没有这种超越,它可能就不会有为自己而存在和在自己之中的区别,也不可能定义责任、荣誉、价值和意义。那么,什么是超越性?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指出,自为存在通过内在的、能动的否定性实现对自在的超越,并将这一过程称为“超越性”。他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文主义》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这种构成人的超越性(不是如上帝是超越的那样理解,而是作为超越自己的理解)和主观性(指人不是关闭在自身以内而是永远处在人的宇宙里)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叫作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这意味着在某些方面,超越性与上帝没有联系,它来源于自我。他认为自我属于为自己而存在,所以自我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存在的一个范畴,这就是为什么超越性不是关于上帝,而是自我。在《无声告白》中,超越性在莉迪亚身上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在《无声告白》中,同时肩负父母梦想的生活让莉迪亚喘不过气来,在这时,成为杰克的朋友使她学会了正确看待他人对于自己的看法与评价。莉迪亚开始思考,这一切为什么完全错了。责备妹妹是她意识觉醒和解放的象征,当看到妹妹带着父亲所送的所谓“人气”的项链,莉迪亚告诉妹妹:“如果你不愿意笑,就别笑。”午夜的时候,莉迪亚来到了湖边,上了船。“还不算太晚。莉迪亚在码头上许下新的承诺,这一次,是对她自己许的。她将重新开始……她再也不会假装成另一个人了。从现在开始,她要做她想做的事情。”在正视这一切的时候,莉迪亚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她学会了说“不”,她不会像她的父亲与哥哥一样选择逃离困境,决定开始战斗,这意味着莉迪亚完成了自我追求与自我救赎,实现了自我超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莉迪亚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在萨特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他/她实现了“走向死亡的存在”之后,才能回到他/她的真实性:只有在良心的召唤下,“我”以坚定的决定向“我”自己最特殊的可能性出发,“我”才会成为“我”自己的真实性。在这个时刻,“我”在真实性中向自己展示自己,并与自己一起提高他人的真实性。最后,莉迪亚试图找回自己的内心,她带着死的决心,走进了湖里,实现了自我重生。
《无声告白》中既有对个体存在的哲学思考,又有对当下我们如何生活的思想启迪。萨特的存在主义既是悲观的,但同时在悲观中暗含积极意味—虽然世界是荒诞的,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会感到痛苦和失望,但人是自由的,人们可以通过自我选择和行动,找到真正的自我,重拾丢失的内心,找到人生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