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堂、流言、闺阁、鸽子
作者: 黄欣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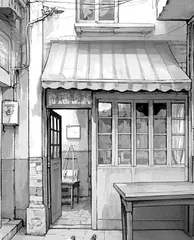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用一支细腻而绚烂的笔书写了“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四十年的曲折情爱史,向世人演绎了一场哀婉动人的上海旧时繁华梦。这部小说不仅成为20世纪90年代上海怀旧文学浪潮中的翘楚,还于2000年获得茅盾文学奖。这部小说的成功,有着诸多因素。但毫无疑问,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全新且诗意的再现,是小说脱颖而出的关键之一。本文试图运用“陌生化”理论,解读王安忆如何构建老上海,进而帮助读者理解作者的匠心独运及其作用效果。
一、“陌生化”理论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概念,对现代文学批评影响深远。俄国文学批评家什克洛夫斯基在其著作《作为手法的艺术》中指出,“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艺术的目的是提供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是事物的‘陌生化’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与时间的手法,既然艺术的领悟过程是以自身为目的的,它就理应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创造成功的东西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由此可见,所谓“陌生化”是通过施展各种创造性手段,延长时间和感受难度,打破人们对日常事物的“前在性”认识,以追求或增强艺术审美快感的创作技巧。“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可以体现在情节安排、语言风格、篇章结构、叙事视角等方面。
小说《长恨歌》开篇即用了整整四节篇幅,向读者全景展示由弄堂、流言、闺阁、鸽子组成的上海城市样貌。本文认为其中运用了“陌生化”手法,具体表现在上海视角的新变、语言形式的独特和篇章结构的巧妙等三个方面。这对全方位打造王安忆式的老上海功不可没,进而为整部小说增光添彩。
二、上海视角的新变
在上海怀旧浪潮中,不论是张爱玲的《传奇》、程乃珊的《上海FASHION》,还是电视剧《上海滩》等,都不厌其烦地致力于重构东方巴黎的热闹和风光,把老上海塑造成消费时代最出色的代言城市,并且也成功迎合了大众,特别是外地人对上海的期待和想象。在这一系列话语主导下,人们只要一提起上海,脑子里极有可能闪现灯红酒绿、奢靡繁华的十里洋场景象。外滩边的万国大厦、淮海路上的高级百货、街道上带花园的西式洋房以及大大小小的商铺和歌舞厅等,无疑成为许多人心中名副其实的上海标志和象征。然而,王安忆并不满足于千人一面的上海印象。人们最乐意看到的那一面也许无法代表上海的街道、气氛和上海的思想、精神。从创作《长恨歌》起,王安忆开始了对上海的重新寻找,并且成功实现了这一目标。
“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分别是小说前四节的标题。王安忆首先介绍的是被高楼和大厦掩盖,隐藏在霓虹灯后面“大片大片的暗”—地上的“弄堂”;接着,她描绘了蔓延在各式弄堂里无处不在的低空“流言”;再是上海弄堂里流言四散、变了种的“闺阁”;最后登场的则是弄堂高空中能看清“最深藏不露的罪与罚,祸与福”的“鸽子”。这四种景观基本上组成了小说的故事背景:“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在弄堂出生、成长,在流言里变得聒噪、成熟,在闺阁里寻春、求爱,在鸽子下惆怅、孤独,最终在鸽子的“俯视”下于弄堂里不幸死去。
总之,王琦瑶四十年的曲折情爱史就是在这四种上海景象中上演并戛然而止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构成了上海世俗的一面,却是王安忆式老上海的典型代表。这让读者领略到了当时上海普通市民的主要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以及共有的精神特质。弄堂才是上海壮观的城市背景,“这东方巴黎的璀璨,是以那暗(弄堂)作底铺陈开”;真假难辨又不成大器却无处不在的流言是“上海弄堂的精神性质的东西”和“这城市的浪漫之一”……这与大众以及其他怀旧文学作家对上海的感知有所不同。王安忆的另辟蹊径,不仅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对上海审美疲劳的心灵,还冲破了人们对上海的“前在性”认识,重新唤起人们感知不一样的上海本色。可以说,王安忆丰富了上海怀旧视角的多样性,让常见的上海变成人们眼中的“新上海”,使得《长恨歌》不流于俗。
三、语言形式的独特
什克洛夫斯基认为,语言陌生化是实现艺术陌生化的重要手段。通过文本阅读,我们可以发现《长恨歌》前四节的语言陌生化主要表现在描写方式、语义(修辞)和语法(句式)等方面。
(一)描写方式的陌生化
不同的作家对事物的描写方式各有不同:有的喜欢勾勒式,似简笔素描;有的则注重细节描写,把小说写成“油画小说”。王安忆属于后者,她将女性独有的细腻注入《长恨歌》,特别是在刻画上海样貌时将细节描写发挥得淋漓尽致。
小说开篇,王安忆带领读者“站一个制高点看上海”,开始对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进行把玩式的导览。在此,本文以“弄堂”和“闺阁”为例作分析。作者除了介绍石库门弄堂(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长恨歌》中为“石窟门弄堂”)、新式里弄、公寓弄堂和棚户杂弄等四类弄堂之外,还不放过各个时刻各式弄堂里各个角落的情状。连清晨雾气弥漫与雾气消散前后,细微处的各种颜色变化都被作者注意到了:“雾终被阳光驱散了,什么都加重了颜色,绿苔原来是黑的,窗框的木头也是发黑的,阳台的黑铁栏杆却是生了黄锈,山墙的裂缝里倒长出绿色的草,飞在天空里的白鸽成了灰鸽。”闺阁也同样被敞开了作全景式展示,笔墨从墙纸上的百合花一路写到被面上的金丝草花案,并且顾及燃了一半的卫生香、被翻开书页上的字等细节。此外,作者还着墨甚多地告诉读者,上海的闺阁不仅有着少女闺阁共有的寂寞安静和忧愁等待,还是“变种”的闺阁。这种“变种”主要表现为突出的矛盾性、两面性。“它是白手起家和拿来主义的。贞女传和好莱坞情话并存,阴丹士林蓝旗袍下是高跟鞋,又古又摩登。‘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也念,‘打给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唱。它也讲男女大防,也讲女性解放。出走的娜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长恨歌》中为“娜娜”)是她们的精神领袖,心里要的却是《西厢记》里的莺莺,折腾一阵子还是郎心似铁,终身有靠。”在这一段精彩的描写过后,作者还用了相当一大段文字从不同对立面阐释上海闺阁有多么杂糅。
可以看到,王安忆似乎拿着放大镜在观察上海,采取地毯式的挖掘采风,极尽地描写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她仿佛同许多读者一般,是第一次看见它们,在每一个图景的细节上都耽搁许久并加以描摹。这样的细腻入微成功地使上海陌生化,增加了读者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感受时间和难度,让读者了解到以往未知的或被忽视的上海细节。
(二)语义(修辞)的陌生化
语言学中的语义包括词汇意义、语法意义、修辞意义、逻辑意义等。张艳玲在《浅谈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中指出,“有些修辞打破修辞格的固定模式,对其进行变形,这种修辞的运用就是对常规性的、习惯性语言的扭曲和超越,而伴随这种超越而来的就是陌生化”。王安忆是运用修辞手法的文学高手,小说前四节最突出的是修辞的陌生化,使得世俗的上海生活情景(细节描写)更加艺术化、陌生化。
“流言”一节有这样一段:“流言总是带着阴沉之气。这阴沉气有时是东西厢房的薰衣草气味,有时是樟脑丸气味,还有时是肉砧板上的气味。它不是那种板烟和雪茄的气味,也不是六六粉和敌敌畏的气味。它不是那种阳刚凛冽的气味,而是带有阴柔委婉的,是女人家的气味。是闺阁和厨房的混淆的气味,有点脂粉香,有点油烟味,还有点汗气的。流言还都有些云遮雾罩,影影绰绰,是哈了气的窗玻璃,也是蒙了灰尘的窗玻璃。”流言,原是摸不着抓不到的无形物,但在通感手法的运用下变得生动有形,仿佛嗅得着。还是写“流言”,作者把在上海空中弥漫的流言比喻成“一群没有家的不拘形骸的浪人”,是上海的浪漫之一;想象成珍珠沙粒般的芯子,是东方巴黎的芯子。在这样非比寻常的比喻下,流言似乎也变得可爱亲切。“弄堂”一节,则是把再平常不过的上海典型居民楼拎出来介绍。在拟人修辞的运用下,弄堂也成了一个富含意味的存在:“上海的弄堂是性感的,有一股肌肤之亲似的。它有着触手的凉和暖,是可感可知的,有一些私心的……那沟壑般的弄底,有的是水泥铺的,有的是石卵拼的。水泥铺的到底有些隔心隔肺,石卵路则手心手背都是肉的感觉。两种弄底的脚步声也是两种,前种是清脆响亮的,后种却是吃进去,闷在肚子里;前种说的是客套,后种是肺腑之言,两种都不是官面文章,都是每日里免不了要说的家常话。”这样的比拟使平凡的弄堂甚至连不同路面发出的脚步声都带上了艺术化气息,让读者切实感受弄堂里的市井生活氛围,颇有文学魅力。而有关“鸽子”的专门描写,更让读者始料未及。王安忆把鸽子同麻雀甚至人类作比较,认为鸽子“是这无神论的城市里神一般的东西”。鸽子竟然成了如同上帝一般的存在,做着天地间的主人,在高空中看尽地面上的悲欢离合,抚慰着城市的心灵。这颠覆了读者对鸽子的认识—原来看似平凡的小小的鸽子也有灵性,甚至展现出超越人类桎梏的生命自由。这种神话化的鸽子让人类也渴望和它们一样神气,实在是奇思妙想。
由此可见,通感、比喻、拟人和对比等修辞手法的巧妙使用,高度体现了王安忆语言的散文性和诗意性。在审美的语言表达下,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全是可观、可听、可闻的,塑造出独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气质。这也使得《长恨歌》成为十分经典的上海叙事。
(三)语法(句式)的陌生化
《长恨歌》中不时出现“……是……的”和“……是……的……”句式,特别是在小说前四节出现的次数更多,如“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那屋披上的瓦是细工细排的”“窗台上花盆里的月季花也是细心细养的”。很多生动形象的细节描写、划水无痕的修辞手法,几乎都使用了这类句式。南帆在《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中认为作者大量使用判断句式,像是“一种经验的命名”,是对“城市图像意义解读的某种诱导,甚至是某种强制的锁定。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句式暗示了文学对城市的陌生”。本文认为,这类句式不乏演绎和归纳的思维,有学术考察的意味。作者的写作姿态似乎始终与叙事客体—上海,保持一定距离,似乎是在重新定义、建构上海。大量使用这类句式,看似刻板生硬,却化腐朽为神奇:达到了陌生化效果,有着极强的感染力、说服力。
总之,在判断句式与艺术语言的双重加持下,一个全新且诗意的上海跃然眼前。这是属于王安忆式的语言特色和魅力,做到了让城市图景进入文学世界,再经由文学世界转介给大众,推动城市图景成为富有诗意的固定意象。
四、篇章结构的巧妙
乍一读《长恨歌》,我们会为王安忆的妙笔生花所折服,但继续阅读下去才发现小说前四节其实只是小说故事的背景。因此,可能会有读者认为小说前四节内容过长,甚至有累赘之感。“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占用了整整四节篇幅,小说女主人公及其四十年的情爱故事反而“姗姗来迟”。故事背景似乎有“小题大做”的意思。少数读者要是不够耐心,可能会直接跳过前四节,直奔王琦瑶的情爱故事。然而,本文认为这样的写法看似“小题大做”,实则是作者在篇章结构上的巧妙安排。英国文学评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学理论导论》指出,“小说采用‘阻碍’或‘延迟’方法,是为了吸引我们的注意力”。《长恨歌》就是如此。作者对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进行层层铺叙,建构起自下而上、完完整整的老上海城市空间。接着,女主人公才闪亮登场,推迟了与读者见面的时间。这不仅有利于把全新且诗意的老上海推向读者,而且有利于吊足读者胃口,促使读者更加期待小说故事的发生、展开。
综上所述,《长恨歌》集中前置展示弄堂、流言、闺阁、鸽子,是比较独特的上海取景视角和巧妙的篇章结构安排。在此基础上,王安忆运用了细节描写、修辞手法、判断句式等陌生化表达,增加了阅读难度,拉长了审美过程,使其笔下的上海极具陌生感,突破了上海认知的“前在性”,让人耳目一新。本文认为,全新且诗意的上海与细腻且曲折的情爱故事相结合,使得《长恨歌》在众多上海怀旧文学作品中显得与众不同、清新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