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四库全书总目》评《山海经》为“小说之最古者”之因
作者: 宋宝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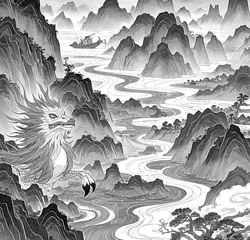
《山海经》一书在中国古代有不同的定位,在《汉书·艺文志》中列在数术略中的形法家之首,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艺文志》《新唐书·艺文志》《群斋读书志》《百川书志》《国史经籍志》等官私书目中入史部地理类,在刘知几的《史通》中被称为“偏记小说”。以上书目对于《山海经》的定位都具有特定时代的合理性。然而到明代胡应麟时,他将《山海经》作为小说的起源,从史部地理类提取出来。谈及这里,就需先厘清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源流变迁。
“小说”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其后《荀子·正名篇》记载:“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这些言论都与“小说”观念的产生密切相关。到了汉代,刘向、刘歆、班固都沿着庄子和荀子的思路为小说家及其作品下定义,《汉书·艺文志》写道:“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刍荛狂夫之议也。”这番言论触及了对小说作者、本体、价值和功用的认识。《隋书·经籍志》提到“小说者,街说巷语之说也”,删除了《汉书·艺文志》小说家“盖出于稗官”之语,这是由于小说作者范围的扩大,也可见隋唐时期的“小说”观念继承汉代而来并有所发展。《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著录了一大批前代官修目录著录在史部杂传类的作品,使小说的故事性和虚构性得以凸显出来。至此,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内涵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到《四库全书总目》编撰时,四库馆臣对小说作者的看法是“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遂将《山海经》《穆天子传》《明皇杂录》等改录进了子部小说家类,使小说的虚构性和故事性更加凸显。《四库全书总目》将小说分为三类: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仍对以前的“小说”观念有所保留。尤其是《四库全书总目》对《山海经》的评价,“书中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竞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实实在在地叙述了《山海经》所具有的虚构性以及“语怪”的特点。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中也说过:“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他也认为小说呈现的特质是“怪”“诡怪”,正可对应四库馆臣的观点,遂可将《山海经》归入小说类。
至于“最古者”一说,可从文化影响的角度谈起。《山海经》根源于历史,其前身多位研究者认为是《山海图》,反映的是中国图腾时代的社会情况,经秦巫祝将图之信息用文字书写至竹简上才有《山海经》的诞生,因此可以说《山海经》是一部上古文化的百科全书。《山海图》专言鬼神之事,具有神秘色彩。《山海经》继续书写图腾时代的神秘色彩,因此《山海经》具有双重价值,既记录了上古历史,又保留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宁宗一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学通论》一书中也说道:“在古代人类的思维中,神话并不是一种文学样式,而是人类原始心理的综合表现和世界观体系的自然流露。因此,在古老的神话之中,蕴含着民族的哲学、艺术、宗教、风俗、习惯以及整个价值体系的源泉。神话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化之源,自然也是中国文学和小说之源。”《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为后世的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神话素材,而且它所开创的事件模式以及它所构造的浪漫世界观对后世小说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素材宝库
西汉刘歆在其《上〈山海经〉表》中曾说:“《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从上述引文中可见,《山海经》对各方位的地理环境都进行了描述,这一地有什么山,那一地有什么水,进而对该处的物产进行介绍,包括该地的草木、动物以及矿物等,最重要的是记录了极多的珍奇怪异之物,这些都为古代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环境描写方面的素材。其次,《山海经》中记载了成百上千的神话人物和大量的神话传说,如神农氏之女精卫溺于东海的故事、神话英雄夸父的故事、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人鱼的神话传说等,这些神话故事虽然古拙朴素,却为中国古代小说家进行创作提供了极好的素材。例如,在流传下来的六朝志怪小说中,以东晋干宝所著的《搜神记》较为著名,干宝《搜神记》的开篇便是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载的“神农尝百草”的神话传说,在《搜神记》中涉及的《山海经》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和地名还有西王母、黄帝、颛顼、昆仑山、峨眉山等。在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过程中,唐传奇虽然沿着六朝志怪小说的脉络而来,但是它与六朝志怪小说的粗陈梗概大有不同。唐传奇多数篇章叙述婉转,文辞华丽,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唐传奇是“始有意为小说”。所以,《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在唐传奇中被运用到另一种高度,如唐传奇名篇《柳毅传》虽然取材于《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但是也在原神话传说的基础上脱胎换骨,让神话传说为自己的小说情节和人物情感发展变化服务。《柳毅传》中的龙女、洞庭君、钱塘君,他们可从龙身化而为人身,这样奇异的故事若要追本溯源,便可追溯至《山海经》,在《山海经·海内东经》中记载着传说中的人鱼:“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记载着氐人国的传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记载着互人国的传说:“有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小说的三要素是人物、情节、环境。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山海经》对后世志怪、神魔小说同样有重要影响,如孙悟空的形象融合了书中的“铜头铁额”的蚩尤、“石中生人”的夏启、淮涡水怪无支祈,以及“与帝争神”的刑天的共同形象;再如本是天蓬元帅的猪八戒因调戏嫦娥被罚下人间,错投猪胎,成为猪首人身的半猪人,关于半猪人的传说,也可追溯至《山海经》,如《海内南经》中记载着“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而且《山海经》记载了黄帝的后代韩流也是“人面豕喙”的半猪人。
二、《山海经》中的事件模式对后世志怪、神魔小说创作的影响
首先,《山海经》是中国古代神话宝藏,也是中国古代地理方志之祖,书中记载了众多的部落和方国,描绘了许多的奇人逸事。清代文人李汝珍写作的长篇小说《镜花缘》的前四十回几乎是全部取材于《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镜花缘》一书中描写的奇闻逸事以及四十一个神话国度可以说是《山海经》里“海内经”以及“海外经”中远人异国的改写,比如《镜花缘》中的女儿国、毛脸国、君子国、无肠国分别改写自《山海经》中的女子国、毛民国、君子国、无肠国。再如《玄怪录·古元之》篇中对于“和神国”进行了大篇幅的刻画,在里面居住的人“不蚕不丝,不稼不穑”,这与《山海经·海外南经》中记载的许多“国”性质相似,皆是自然给予其衣食。
其次,人与神的婚姻、人与精怪的婚姻在《山海经》中是合理的,这种事件模式为后世志怪小说以及明清神魔小说提供了借鉴。人神、人鬼、人妖恋爱在志怪小说中非常多,如南朝梁吴均所撰的《续齐谐记》富于浪漫气息,内容多涉及人鬼恋爱的故事。唐传奇名篇《异梦录》《秦梦记》《湘中怨解》等,其小说主题也都是写人神婚姻恋爱,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描述这几篇作品“皆以华艳之笔,叙恍忽之情,而好言仙鬼复死,尤与同时文人异趣”。再如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将《聊斋志异》归入“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一类中,《聊斋志异》拟的就是唐传奇,所以也可以把它归入明清神魔小说一类,这部作品最大的艺术特色就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蒲松龄在《山海经》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撰写奇异的故事,《聊斋志异》中的神、仙、狐、鬼、花妖等形象都是他在神话传说的基础上加入了体现他个人心灵的创造,每个神异的形象都有所寄托和寓意。其中的名篇,如《聂小倩》《婴宁》《青蛙神》等都包含了跨越种族的情感纠葛。《聂小倩》中的女主人公聂小倩虽为女鬼,但是最后却可以与活人宁采臣生活在一起,并且还为宁采臣诞下子嗣:“先是,宁妻病废,母劬不可堪,自得女,逸甚,心德之。日渐稔,亲爱如己出,竟忘其为鬼,不忍晚令去,留与同卧起。女初来未尝食饮,半年渐啜稀。母子皆溺爱之,讳言其鬼,人亦不之辨也。无何,宁妻亡,母阴有纳女意,然恐于子不利。女微窥之,乘间告母曰:‘居年馀,当知儿肝鬲。为不欲祸行人,故从郎君来。区区无他意,止以公子光明磊落,为天人所钦瞩,实欲依赞三数年,借博封诰,以光泉壤。’母亦知无恶,惧不能延宗嗣。女曰:‘子女惟天所授。郎君注福籍,有亢宗子三,不以鬼妻而遂夺也。’母信之,与子议。宁喜,因列筵告戚党。或请觌新妇,女慨然华妆出,一堂尽眙,反不疑其鬼,疑为仙……后数年,宁果登进士。女举一男。纳妾后,又各生一男,皆仕进有声。”
三、《山海经》浪漫的世界观对后世志怪、神魔小说创作的影响
《五藏山经》各山神灵形象纷繁复杂,这种充斥着精灵的世界对后世志怪、神魔小说世界观的构造有重要影响。《山海经》中的世界仿佛是一个超人的世界,卷六《海外南经》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地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海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神灵所生,其物异形,或夭或寿,唯圣人能通其道。”由此可见,《山海经》中描绘的上帝之都可以说是后世神魔小说中天宫的雏形。例如,《西游记》作为明清神魔小说取得极高成就的代表作之一,其作者吴承恩通过幻化之笔写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神异奇幻的世界,他以极度的夸张、诡异的想象,突破神、人、物三者之间的界限,并且突破生死、突破时空,将一系列奇境、奇人、奇事融合在一起,由此构建了一个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展现出一种奇幻的美。
中国古代志怪、神魔小说所展现的浪漫的世界观源远流长,《山海经》搭建上帝之都,《列子》中描写了早期仙境的神秘和超脱,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后有了想象的空间,这些都为志怪、神魔小说以奇幻之笔塑造书中世界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久而久之,这种浪漫的世界观成了中华民族共有的东西。
综上,笔者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撰写者评《山海经》为“小说之最古者”的原因是:《山海经》主要为后世志怪、神魔小说创作提供文化内核,与后世志怪、神魔小说之间有着血肉联系,包括此书为后世志怪、神魔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好的想象素材、事件模式以及浪漫的世界观。因此,当《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结束它的历史使命转而成为一种历史的积淀时,神话传说的延续便和古小说的创作有了一种契合,神话与古小说几乎是一体的两面,或许神话传说本身会被大众渐渐所忘记,然而它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却获得了无限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