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的文学张力
作者: 孟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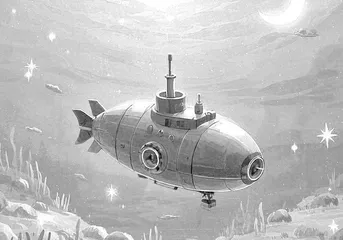
陈春成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首次出版于2020年9月,并于2021年获得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这部小说集一出版就获得了众多专业人士的好评。余华认为,陈春成最厉害的一点就在于他的作品在写作上既飘逸又扎实,小说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转换和衔接都做得非常好,堪称一位前途无量的作家。
《夜晚的潜水艇》这部短篇小说集一共包含了九个故事。在这九个故事里,作家用他丰富的想象力为读者构建了一个个现实与想象交织的光怪陆离的世界,既有对中国传统古典元素的应用,又有对个体与宇宙世界关系的独特思考。陈春成以他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了他对宇宙与人生的哲学理解及对现实的批判,体现着文学的独特魅力。本文将从三个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分析,即传统古典元素与浪漫想象的融合、隐喻手法与批判精神的结合,以及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进而揭示其独特的艺术张力。
一、传统古典元素与浪漫想象的巧妙融合
陈春成的小说世界是一个又一个的想象世界的奇妙书写。这些故事游走于旧山河与未知宇宙之间,以超凡的想象力探知人类心灵的幽深角落。陈春成以其独特的文学笔触,在现实与幻境之间开辟出一条条秘密通道,让读者在静谧中感受想象的魔力。阅读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的九个故事,读者很难不被作家奇幻的想象力折服。
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以“1966年一个寒夜,博尔赫斯站在轮船甲板上,往海中丢了一枚硬币。硬币带着他手指的一点余温,跌进黑色的涛声里”开篇,引出一个富商的荒唐决定—他要造一艘潜水艇去找到这枚硬币。之后的若干年,在脑子里总是充满想象的陈透纳的幻想中“原本并无交集的两艘船,就在冥冥之中相遇了”(陈劲松《语言、想象及思想:考察陈春成小说的三个维度》)。《裁云记》中的“我”是云彩管理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去裁剪“违法云”,让这些云彩保持着那个世界所规定的合法形状;在《传彩笔》中,富有写作才华的叶书华在梦里得到了一支传彩笔,但他写出的作品却再也无法被世人所见到,最后他又在梦境中交还了这支笔;《〈红楼梦〉弥撒》则是讲述在遥远的未来世界—第一次星球大战之后,《红楼梦》处于消逝的边缘,通过过去、现在、未来世界的联结讲述人与宇宙关系的哲学命题;《尺波》是三个梦境的相互关联,通过对主编张焕、铸剑师以及国王之间的梦境展现,在最后张焕与“我”的谈话中产生了充满意味的想法:“大地的另一面,也许有人正梦见云中的缆车,梦到了这场谈话……而那柄穿透一切,令一切化为乌有的剑,正在黑暗中以不可知的速度行进着,日日夜夜向我们奔来。”无论是漫游在深海的少年、遗落在深山的古碑,还是弥散于万物之中的文字、梦幻的云彩修剪站,这些情节都充满了超乎寻常的想象力。陈春成通过他丰富的想象将读者带入一个个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幻想世界,让人在惊叹之余也不禁沉醉其中。
此外,陈春成自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陈春成引用了大量古典诗词,这些诗词不仅为小说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表达。《〈红楼梦〉弥撒》对人物名字的设计也是来源于中国传统典故中山酒的传说。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的《秋山晚翠图》到《溪山行旅图》,这些古典山水画不仅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设定,也通过视觉呈现的方式传递出一种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审美效果。在《竹峰寺》中,竹峰寺的禅院、藏经阁、钟鼓楼等建筑以及《法华经》等材料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充满禅意的精神空间,而主人公在寻找藏匿钥匙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找到属于自己的“藏心”之地;《传彩笔》则是对江郎才尽典故的别样解读下的书写;在《尺波》中,铸剑师的故事也隐隐带有眉间尺的影子。这些对传统古典元素的运用赋予了小说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厚重感。
将这种奇妙的想象与传统古典元素完美融合在一起,得益于陈春成小说的语言表达。陈春成的小说语言典雅,充满诗意,正是这种诗意的表达使得小说的浪漫想象与传统古典元素之间达到了叙述的和谐统一。汪曾祺曾写道:“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的积淀。你看一篇小说,要测定一个作家文化素养的高低,首先是看他的语言怎么样,他在语言上是不是让人感觉到有比较丰富的文化积淀。”(《汪曾祺的写作课》)
在陈春成的小说中,读者很容易可以感受到作家语言的古典雅致和文化积淀。在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小说的语言呈现出一种散文化的倾向。《竹峰寺》中的“我”面对老屋的拆除时“一阵恍惚,不知身在何世。我想,那些消逝之物,都曾经确切地存在过,如今都成了缥缈的回忆;一些细节已开始弥散,难以辨识。而我此刻的情绪、此刻所睹所闻的一切,眼下都确凿无疑,总有一天,也都会漫漶不清。我们所有人的当下,都只是行走在未来的飘忽不定的记忆中罢了。什么会留下,什么是注定飘逝的,无人能预料,唯有接受而已”;在《酿酒师》中,酿酒师在酿酒时,瓮的声音“起初瓮声瓮气,像埙;后来清亮如笛声,有时淅沥如急雨;夜里像某种动物的哀啸”;《裁云记》中的风景是“满山草木松脆,凉风中有稻香浮动。田野金灿灿的,耀人眼目。水稻并非一种植物,而是从泥土中生长出的光。天蓝得像一个秘密。大地起伏,山丘凝碧”。作家无论是展现人物的心境,抑或对景物的描绘,他的语言都是充满着诗意的。这种诗意的、散文化的表达出现在小说的创作之中就给小说的文本带来了更加抒情、典雅的气质,让小说的想象以一种诗意的方式与传统古典元素相融合,达到自然和谐的境界。
二、隐喻之语与批判之声
正如王德威在《隐秀与潜藏—读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中所说:“陈春成的书写不无对现实的批判,甚至隐隐触动敏感政治神经。”在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作家不单单是对奇幻想象的大力展现,同时也暗含了作家对现实的批判与思考。
学者陈劲松在《语言、想象及思想:考察陈春成小说的三个维度》中认为:陈春成通过隐喻与象征来揭露现实,进而体现了他的思想力。“唯有读出隐喻和象征背后的现实性与思想力,才能说真正读懂了陈春成的小说。”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首先,我们认为‘象征’具有重复与持续的意义。一个‘意象’可以一次被转换成一个隐喻,但如果它作为呈现与再现不断重复,那就变成了一个象征,甚至是一个象征(或者神话)系统的一部分。”而意象简单来说就是作家对客观事物融入了主观性意旨,使得客观之物在意义上得到了升华。作为客观之物的潜水艇、洞穴、匿园等被融入了作家的主观情志,使其变为了富有深层含义的意象,经由文本的转换具有了隐喻功能。潜水艇是藏起想象力的地方,也是陈透纳绽放想象的地方,洞穴是供“我”沉溺毕生事业的地方,这些客观之物成为小说中的主人公们进行自我疗愈的圣地。
其次,小说的背景也不乏隐喻意味。在《竹峰寺》中,为了保护文物蛱蝶碑在那个特殊时期不被毁坏,慧灯和他的师兄师弟们一起将它藏了起来。但是到了和平时期,慧航问慧灯将蛱蝶碑藏在何处时,慧灯却无论如何都不愿说出口。这是因为“老和尚对当年的承诺看得很重,是打算守一辈子的。另一层意思,他有点惊弓之鸟,总担心从前的事会再来一遍。碑还是藏着好,谁也砸不了”。慧灯的这种“惊弓之鸟”的心理状态,正是在特殊时期造成的精神创伤,慧灯的这种心态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经历过那个特殊时期的一代人的精神创伤。陈春成对慧灯的心理世界的展现,诉说的是特殊时期给人的精神所造成的难以愈合的伤痛,也是对那一段历史的思考。除此之外,“我”重回竹峰寺的背景原因也具有值得审视的价值。阔别家乡六年的“我”回乡后发现,自幼生长于其间的老屋已被拆除,周围也变得焕然一新,与“我”幼时的记忆完全不同。不仅如此,“我”发现变的不仅是“我”的老屋,整个县城也在飞速变化,这让“我”生出一种风景皆殊,一切非“我”所有的凄凉与孤独。“我”虽已适应了城市的快速变化的节奏,但回乡后面对旧物的变化仍是让“我”难以接受。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那些“我”原以为不会变的东西却在烟消云散,这种难以言状的感觉也是无数离乡奋斗之人的共同感受。在《裁云记》中,“我”是云彩管理局的一名云彩“修理工”。云彩管理局是因为什么而设立的呢?这源自多年前,在元首的一次城市视察中,元首随口说的一句“今天天上这个云,怎么破破烂烂的”的玩笑,就让天上的云彩全都遭了殃,因此设立了这个带有荒唐意味的云彩管理局。这种对官场形式主义的展现颇具对现实的讽刺意味。
陈春成对历史的批判,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思考以及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怀都体现在了他的文学创作之中。陈春成的小说创作不仅仅是想象的大力展现,更是他对现实生活的认知与理解。
三、“藏”的人生哲学
在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中,“藏”的书写是其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次出现了与“藏”有关的内容。藏于潜水艇之中的幻想、藏在青苔之下的老屋的钥匙、藏在知识洞穴中的“我”、藏于匿园的记忆、藏于记忆中的《红楼梦》,以及只能藏于幻想之中的音乐都在小说之中具有独特的意义。藏匿的是何物?又为何藏匿?对这些问题的答案才是作家想要传达给读者的真正内容,这也使得陈春成所书写的“藏”具有了哲学意味。
从表层上看,“藏”表现了一种内心与外在的对比,是他们与现实生活的相处的一种方式。在小说中,许多人物都拥有外在的平静与内在的波澜。他们表面看似平静无奇,内心却充满了激情与挣扎。这种内在与外在的对比不仅丰富了人物的性格与情感,也展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深度。陈透纳在放弃幻想之后他的外在是平静的,但是内心深处仍旧不断在自我挣扎,他将他的想象力藏于整个潜水艇之中,但之后也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我的火焰,在十六岁那年就熄灭了,我余生成就的所谓事业,不过是火焰熄灭后升起的几缕青烟罢了。”但是,藏匿他的想象力是陈透纳成为一个“正常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选择。在《竹峰寺》里,“我”归来又离去,想要得到的是在这不断变化的地方找到可以藏匿老屋钥匙的安全之地。“我”每日在竹峰寺中看似在享受着难得的假期,实则内心深处有着难以言说的烦闷。回到家乡发现老屋被拆掉,虽然心里已有设想,但周围的一切都像是消失了,这让“我”生出一种一切皆非“我”所有的孤独之感,同时“我”却对这一切又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将对这一切的记忆“储存”于钥匙之中,和石碑一起藏匿于这世间的角落。在《音乐家》中,古廖夫将自己的对音乐的创作才华藏匿在大脑与想象之中。古廖夫表面上顺从于当前的高压控制,但他内心对这种控制仍旧是反叛的,现实的高压与内心对音乐自由的向往,让他只能在幻想中演奏。只有正式了解人物所藏匿的事实,读者才能深刻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别样感受。
但是从深层次来讲,故事中的主人公们的藏匿事实上是对自我与现实关系的一种精神疗愈,是一种回归自我的哲学思考。人的生命的有限与宇宙的无限,在时间的推移之下任何事物终究是会弥散的。《红楼梦》弥散后,陈玄石对宇宙的领悟、古廖夫在演奏后化为灰烬,以及“我”最后找到的藏匿钥匙的地点都恰恰说明了这一点。面对这种现实的种种无力感,陈春成提出了他的解决之法:找一个藏匿之处,进行自我疗愈。《竹峰寺》中的“我”找到了一个藏匿钥匙的地方来抵御世事无常,《裁云记》中的“我”在洞穴中沉溺于毕生的事业,《音乐家》中的古廖夫也在幻想中完成了自己的梦想。寻找藏匿之地进行自我的精神疗愈并非消极的接受,而是源于对个人与现实之间的辩证认识。“如果柏拉图的洞穴象征着人类最初的幻象与枉然,那么在现代性进程之下,陈春成的洞穴正是最后的遮蔽与最终的抵抗,不管藏匿的是故事还是记忆,收容的是幻想还是欲念,洞穴都默认了藏匿与消弭、虚无与永恒的辩证法。”(樊迎春《在黄昏与黑夜的缝隙中藏匿—陈春成的文艺奇幻与现代洞穴》)通过“藏”的哲学思考,陈春成不仅展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深度,也表达了个体存在与宇宙关系的深刻思考。正如王德威所说的那样,“陈春成写‘藏’作为一种生存方法,甚至由此发展出一套思维方式”(《隐秀与潜藏—读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
作为一名“90后”青年作家,陈春成创作的作品并不多,但他的这部短篇小说集《夜晚的潜水艇》展现了他惊人的创作才华,既有对古典与浪漫并存的幻想世界的奇妙展现,也有对现实生活的哲学感悟和批判性思考。正如第四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的颁奖词所说:“《夜晚的潜水艇》独辟蹊径,把知识与生活、感性与理性、想象力和准确性结合为一体,具有通透缠绵的气质和强烈的幻想性。小说以一种典雅迷人的语言为我们展现了当代小说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