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人的意志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珲 郦毅)
选择,提交。两个动作完成公民对民意调查的参与,这显然是新浪网让网民感到最简易也最富主动精神的一个行为。近期的投票再次与《婚姻法》的修订有关。据新浪网新闻频道的魏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根据网友们讨论最多的热点新闻出题目,“每期调查都有将近三四万人参与。”
与新浪合作的媒体也更看重这些投票者的声音。不过7月所做的“姻亲结婚(即公公与儿媳、婆婆与女婿)法律是否应视其为非法”的调查,却着实让人会错意,这个调查的最终答案是赞同票占上峰。可见事关每个人的“婚姻”立法,情势复杂。
各自以调查数据为支持的两派意见,正在《婚姻法》的几大细节上喋喋不休。巫昌祯借用全国妇联从北京、广东、四川等十个省市区采集的大量数据举例:“分别有90%以上的男性和94%以上的女性赞成新的《婚姻法》‘处罚第三者和婚外恋’,而在对通奸、搞婚外恋和重婚纳妾的惩处上,广东一地有54.8%的人选择了‘追究刑事责任’。”巫昌祯喜气洋洋地说,“这证明我们的草案符合民意。”
反对者也在网上“传诵”着另一组数据:十余天,7852人参与,只有17.9%的被调查者同意巫昌祯们帮弱势人群设立的惩罚,剩下的82﹪说,“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即使当初最慎重考虑的婚姻,也不能保证不发生变异,因此不应将其归为非法之列”。
值得注意的是,两种以不同方式采集的数据也来自不同人群。前者分出了农村卷、城市卷,后者以47.3%的白领为主。反对者以一种独立姿态表达这样的意愿:“并不是法学家或立法者认为‘不道德’的所有行为,都应该或可以用法律规定为‘非法’。法律道德主义和惩罚婚外恋的法律,不管起草动机如何,都必然是残酷和伪善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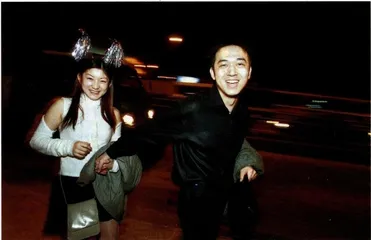
如此新潮的恋人,他们会如何看待(曾忆城 摄/fotoe.com)
争论无疑从侧面证明了社会学家既往的判断,事实上越是文化水平高的人群,更能容忍一个社会道德多元的状态。
不过,直到8月17日,传媒还在欢欣鼓舞地报道类似这样的“民声”——大多数人认为应将公认道德上升为法律。一个由沿海某城市妇联操作的调查再次宣布:“大部分专家认为,忠实应该是夫妻关系的最低要求,婚姻一旦缔结,家庭一旦建立,就产生了对配偶、家庭、子女,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将公认的道德上升为法律,就可以把‘婚外恋’、‘第三者’置于违法的境地。本次调查显示,99.7%的人认为夫妻应相互忠诚。”
由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仅限于此:如果你寄希望于哪一组数据更能成为立法笃信的依据,恐怕你就要被那个打着大多数人旗号的意见蒙蔽了。
法律学家说:人类进步的历史应当说是过去某种我们认为很正当的道德戒律不断被法律改变、冲破、越来越宽容的过程。
记者:法律跟道德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整个人类法律发展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地摆脱道德的过程,早期两者往往是混淆的。法律制度一定是有一定的道德基础,但这种道德基础往往是不同的社会力量妥协的产物。不同的道德观念或多或少会在最后的法律制度形成过程中互相冲突、妥协,最后形成一个新类型的法律制度的某种道德基础。
中国的问题比较困难,一方面是在许多人的观念中,还认为法律和道德应当保持一种更和谐的关系。许多人寄希望于用法律去拯救日益衰弱的道德,比如说前一段有人提出应该规定对见死不救的惩罚。这本身是个道德问题,但很多人觉得太可恶了。对这个说法,我是抱着比较质疑的态度,因为法律的操作性比较困难——如果没有相关的有效证据,完全没法判决。我们虽然制定了许多看上去很高尚的法律,但实际都操作不了,法律就形同虚设,那么有法不依更恶于渎法。
另一个中国的现实问题是,人们的泛道德倾向都很严重。这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传统,什么问题都以一个道德家的眼光去观察它。实际上这样我们会把人区别成好人和坏人,对坏人的惩罚就没有什么法律上的限度感。就会有过去常有的说法,“全民共诛之,全民共讨之”;就会人为地制造出一批跟我们不一样的另类。在这个领域中,相关的人权保障就会变得很艰难,另外一种意见完全没有办法突现出来,最终的灭顶之灾就有可能会降临在每个人头上,谁也不能说他是永远安全的。

贺卫方
记:法律的设计应该尽量地保证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贺:对。我非常欣赏的一个观点是,“大多数人的最大的幸福,是法律的宗旨所在”。
记:目前我们习惯于把大多数人公认的道德上升为法律,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会是什么样的?
贺:当一些人宣称他们知道或者获得了大多数人的道德观念是什么的时候,又要通过立法把它上升为法律,那是很值得警惕的。这些人是否真正能够有一种正确、合理的方式获得这种信息?如果没有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号称本身就会形成一种霸权。现代社会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对
少数人集团,或者说对道德观念抱有很不同意主流观点的一小撮人怎么保护的问题。既维系社会内在的某种一致,让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不至于四分五裂,同时又保障每个人能够按照他们自己恪守的道德准则或生活态度过这一辈子,这是现代社会中特别难办的问题。
法律总是要体现所在社会中人民的某种愿望,这需要一些更加细致的方法来了解什么是人民的意志,什么是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希望。在这个方面制度的缺陷很大,我们没有什么真正的法律搞过公开的听证。大家按照一定的规则清晰地表达观点,人民才会有选择。现在单纯地把一个问题摆在眼前让人选择的做法,不见得是真正的民主。
记:可能对于中国来说,是需要有更好的技术手段来辅助,促使观念上发生变化后,不断地促进、提升。
贺:对。根据我的观察,这可能是法律职业或者说法律制度能够为社会带来福利的一个方面。它不断地把你死我活的价值冲突给它下降,降低为技术的东西。道德还有最大的一个问题,不同的人太不一样,它没办法实现社会的整合。如果我们硬要用道德来整合,大多数人的道德必然导致对少数人的侵犯、压制和多数人的暴政。
伦理学家说:法律与道德有重合又有不同,有些不道德行为仅需从舆论上谴责,而有些不道德行为是可以通过法律做强制性惩罚的,但需要慎之又慎。
记者:修订《婚姻法》时,双方争论很厉害,又都能拿出很强的支持阵容,这种分化让立法者怎么办?
何怀宏(北大哲学系教授):有时调查是很难说的,很多东西可以作为了解民情的依据,但不是一定就能构成立法的主要依据。立法有时涉及到道德的法律强制。比如一些很基本的道德准则,过去历史上儒家、道家、佛教都强调不杀生、不伤人、不奸淫、不盗窃,包括西方的摩西十戒不做伪证,它们是道德,同时又都是法律强制的内容。但有些道德内容就不一定能强制,比如并未太涉及他人利益的说谎,就不宜用法律来惩罚。
记:大多数人公认的道德是否就意味着是合理的,公正的?
何:一般在社会比较稳定不变时,确实如此,但是像我们现在所处社会变化比较激烈的时候,这个多数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婚姻形式、性生活形式,某些具体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
记:在目前观念很混乱的时候,所谓大多数人公认的道德会不会本身就存在问题?到底什么是大家公认的?谁代表着多数人?如果把它升上为法律的话,会不会产生比较危险的后果?
何:更重要的是讨论的空间和立法的理性。我担心感情容易影响理智,一些人很痛苦,因为离婚、第三者,感情上同情弱者,想通过立法来帮助他们。但是法律到底能做什么,我们对法律能寄予多大的期望?法律不可能是一辆把什么东西都放进去的大车。
记:伦理和法律都可以从不同层面去建构一个良性社会。
何:法律就应该神圣,要非常谨慎地立法,因为立法就意味着强制性的规定,毫不含糊的惩罚。
记:作为一个伦理学家,您认为道德在今天还能有何作为?

何怀宏
何:道德的要义是不能任意强制。一般来说,要尊重每个人作为道德主体的权利j在社会生活中有不强制就会蔓延开来的邪恶,对比较重大的损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还是必须干预,我一直倡导一种“底线伦理”,即对道德本身也不能做一种非常高尚的理解,应从最基础开始。回顾一下20世纪的历史,很多时候不是说人不够高尚,而是丧失了起码的做人底线,才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另外,法律和社会都不可能去保证每个人的幸福,像有些乌托邦小说,设想人类社会一切都很美满,但还保留一种不幸,那就是失恋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