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派人来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王珲)

大象进村
村民们再次看见大象,是1992年。这以后,一个为数5头的象群固定游走在云南省思茅地区的山野田间。到了1999年8月,据有的村民讲,这个象群似乎又增添了一头小象。
从1976年到1992年,村民们已有16年没有见过大象的踪迹。《思茅县志》早有记载,“思茅县倚象乡的东南原为原始森林,因野象经常出
没,后转音为倚象山,乡由山而得名”,“1975年,13头野象进入 竹林小橄榄坝,践踏晚稻10余亩后自行离去。1976年,菜
阳河一带余存的3头野象被偷猎者捕杀殆尽。”
与西双版纳交界的思茅地区,村民们受傣家传统的尊象为神的宗教信仰影响,也视大象为吉祥物。1992年第一头独象出现时,人们惊喜过望,围观、投食,据说甚至还有人蒸了一锅米饭,跪在地上,双手捧过头顶供给大象。
思茅地区45.2%的土地上覆盖着森林,野象的再次出没无疑印证了该地自1991年来采取的种种措施的成效。1991年3月,思茅市宣布3年封山禁猎;1996年又宣布5年禁猎,并实行退耕还林;1998年收缴民用枪2万支;与此同时农村推广的沼气池又使柴薪用量从每户7~10立方米降至1立方米……生态环境的改善,吸引了从西双版纳游荡出来的象群,到目前为止,据IFAW(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洲象保护计划的工作人员估计,在思茅活动的大象有两个象群,大象的数量至少在20头左右。
人象冲突
当然,野生大象进入人类的活动空间之后,人们的欣喜很快便被另一种情绪取代。据当地林业部门调查报告,1997年7月27日,一头独象在思茅市飞机场跑道上漫步;同年8月7日,思茅市第三中学校园内闯入一只大象;1999年1月19日,象群出现在机场附近。
更令人恐慌的消息是大象伤人致死的事件。思茅地区一共发生过三起:1996年,一头野象闯进庄稼地,众多村民围观,大象受惊后误踩一名少女,少女顷刻身亡;思茅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在拍摄出现在机场附近的象群时,与大象距离过近,加之眼镜破碎、视线模糊躲避不及,被大象踏死;去年7月,三家村一位正在给竹子培土的79岁老人,因耳背未听到大象过来的声音,被踏死。
喜极生悲的意外惨剧,给村民们的生活笼罩上了阴影。据悉,在大象出入比较频繁的村镇,学生上学要大人接送,人们不敢上山挖竹笋,机场附近也不敢停留。
在人与象面对面的冲突之外,大象的生存方式对当地发展也构成威胁。据思茅市野生动植物管理委员会1999年8月的报告称,当年7个月农作物受损面积达2.85万亩,造成经济损失120万元;另据南屏镇政府《关于大象损毁农作物的报告》的数据,截止1999年9月,共有439.7亩水稻、245亩玉米、273亩芭蕉、137亩花生及黄豆、70亩菠萝、127亩龙眼及荔枝受损。
大象快跑
石头山社村民王增华一家人于1996年,种植了1.5万棵菠萝和2000蓬竹子。1997年野象来了。1998年,大象在他家地里待了整整两星期。两年的辛苦颗粒无收,损失达2万多元,不仅庄稼地被踏平,就连地里搭的房子也被大象弄个粉碎。 被当地人称作“老象”的野象们的足迹还四处可见,一只被踩瘪了的汽油桶,被折断了的竹茎,一大砣野象的粪便,吃剩的菠萝……王增华告诉今年7月前去采访的记者颜莹,老象经常光顾他家的地,因为象最喜欢吃竹笋、芭蕉、稻谷等,“它吃菠萝最有讲究,别的地儿都不动,专吃刚刚结出的菠萝果。”
为了驱赶野象,王增华一家凑了8000多元钱自费修起了一条深2米,宽2米,长约1公里的防象沟。可是面对竹笋和菠萝香甜的诱惑,有着2.3米宽沟壑跨越能力的老象还是会冒着风险跳过沟来。像王增华一样,附近的村民也想尽了各种办法:在公路上扯绳子挂小黄旗和灯泡——到夜里让灯光闪起来吓唬大象;让拖拉机整天整夜轰鸣,以嗓音驱赶野象……但这些方法很快对头脑聪明、适应力强的大象失去了效力。
1998年云南省政府颁布了第67号令——《云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生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第九条规定“政府补偿费用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分到思茅市林业局的补偿费是每年2万元。在思茅地区,除了大象之外,还有野牛、猴子、松鼠等野生动物的侵扰,2万元分派到各村各户,每公斤谷子的赔偿不过是几分钱。
捕杀野生保护动物违法,百无作为的村民们只有在自家门板上写写“象灾”之类的打油诗消消气。村民因象而起的上访率逐年增高,矛盾在激化。据悉,79岁的老汉被大家踩死,激愤的村民几乎提议要抬尸游行。亚洲象保护项目组成员张立告诉记者,流传在当地最典型的一句话是:“大不了就把老象杀了,判15年徒刑,15家人轮流去蹲狱,一家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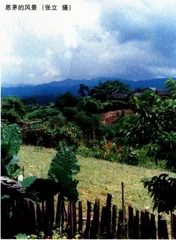
思茅的风景(张立 摄)
帮助大象,从帮助人开始
大象的处境岌岌可危。短短8年时间,人对大象从喜爱、过于接近到闻风就跑,对立仇视,态度的转变似乎也改变了大象的生活习性。据村民说,现在很少能在白天看见大象,它们一般都是在黄昏或夜里出现在村寨附近。从1998年年底开始,亚洲象保护项目小组下去考查了四、五次,至今无缘与大象碰面。但村民们听说他们是来解决人象冲突的远方客人,热情备至,每次返京前都要努力地往每个人的背包里塞下几根竹笋。
张立负责的项目小组决定尝试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人与动物对生存空间的竞争。“我们拿出100万元人民币帮助当地村民发展经济,提高他们的承灾能力,并向接受‘互助基金’的村民进行环境教育,实现人象和谐共处的目标。”张立说。2000年7月12日,亚洲象保护计划正式在思茅市启动,并为首批试点、受大象影响最大的4个村寨207户村民提供了82800元资金。此后的三年,以每年200户,每户800元的步骤进行。
动物学博士背景的张立对这个计划蛮有信心,“大家不在山上种经济作物,改做其他养猪、酿酒等非农经济,让山上长满大片大片的竹林,大象带来的损失就不会影响家里的收入。我们发现,大象常去的一个寨子是因为那有一片天然硝塘,它要补充生理盐分,所以才会发生把晾晒的棉被卷着吃了的事,多给它建几个硝塘,它就不会常来村子了。更重要的是,人要懂得怎么和动物相处。无论动物还是人,都有心理的安全距离。人来吓唬大象了,大象也会开始吓唬人。”
托动物们的福
亚洲象保护计划从论证到实施,历时两年,其中有一年时间是说服IFAW拿出100万元解决思茅的人象冲突课题。尽管每年有6000万美金的捐款进项,创立于1969年以倡导“动物福利”为宗旨的IFAW仍然对于在中国需花如此多的钱救助二十几头象的做法持审慎态度。“他们在肯尼亚,只花了5000美金,便把二十几只非洲象从人类的聚集地迁至保护区,与此同时,他们在非洲的做法是以每年200万美金的支出购买土地,来扩大象群的生存地。IFAW坚持认为,在中国也应该采取同样的办法。”张立说,“他们不理解在中国人口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买地根本不可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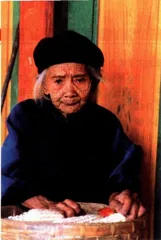
在思茅,很多人就像这位89岁的老人,一辈子守候在自己的土地上(郝冰 摄)
以思茅地区的南屏镇为例,从1989年到1998年,该镇的人口增长了近41.3%;而人均耕地面积却恰恰减少了48.8%。“人都把农田种到大象的餐桌上了,它能不吃吗?”张立替大象叫屈。这种矛盾即使在象群聚集的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也同样存在。1993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在版纳建设了24个用于防范大象侵扰的电围网试点区,最终由于村民的投入热情不高、维护不当,基本失效。张立们更不敢在人口稠密常有儿童嬉戏田间的思茅建电围网。
三年中,从建乡村科技图书馆开始,请科技人员下乡,开展村民的环境教育,搞野生象群的生活习性研究,将是亚洲象保护项目组要完成的事情。村民们在拿到钱的同时也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因为村民向IFAW承诺,“不乱捕滥猎,不毁林开荒,保护亚洲象及其栖息环境”。
在平衡野生动物的理想环境与人类的家园安全的问题上,承载着无数人爱心的IFAW无疑迈出了新的一步。不过,从人本位的私心角度来看,在人口仍趋膨胀的情况下,最有效的解决方式也许是让大象也一起接受环境教育,“不乱闯乱踏,不毁田伤人,尊重人及其居住环境”。
(感谢北京电视台新闻部《绿色经济》栏目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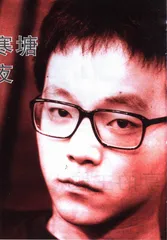
大象回来了
小资料
象作为陆地上体形最大的哺乳动物,有旗舰物种的意义,它生存状态的好坏可以直接反映出大批陆上动植物的处境。象有两种,亚洲象和非洲象,两者以头大头小、牙短牙长为区别。印度现有亚洲象的数量是我国的2倍。我国仅存200至300头,其中又以西双版纳为象群的主要栖息地。被列为中国一类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大象,同时也被列入CTTES公约附录Ⅰ,并被IUCN列为濒危物种。亚洲象属于群居性动物,通常由一头年长母象为头领,带领着其他几只母象和幼象。只有老年象或公象才会成为独象。尽管是草食性动物,一只成年象的体重能达到3500公斤,每天平均需进食150公斤。当它换完六对臼齿进入老年期至少要55年。历史上,亚洲象的活动领域曾一度到达黄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