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数字化电影浪潮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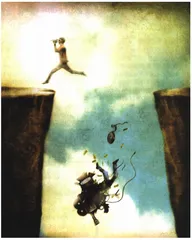
数百万人在电影院里观看的其实只是一部录像片
《女巫布莱尔》是去年的一部独立制作的低成本电影,以几万美元的制作成本和数百万美元的推广费用而获得全美第七位的票房成绩——1亿多美元。关于这部影片的种种故事,几乎已人所共知。但真正令人吃惊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它是一部没有恐怖的恐怖片,也不在于它的DIY(do it yourself自己动手)方式——三五个人拍出一部片子的事可以说古已有之,甚至也不是它利用互联网所做的市场推广,不是它那惊人的利润。
真正令人吃惊的地方在于,数百万人涌进电影院里,坐在那里观看的其实是一个87分钟的录像片。换句话说,《女巫布莱尔》最不寻常的地方在于它的屏幕的高宽比。它在拍摄时没有摄影机的快门声和胶片转动时的咔咔声,因为它使用的是两部普普通通的摄像机。
《女巫布莱尔》只是数字电影浪潮中一个小小的浪尖。
随着传统电影的摄制成本——设备租金、胶片费用、后期制作费等越来越高,许多独立电影工作者正在变成独立摄像工作者。他们用摄像机来拍摄“电影”。有的用比较专业的摄像机像数字贝塔机和贝塔机,有的仅用MiniDV机(微型数字录像机)。现在也有人用高画质的索尼VX1000或佳能XL-1,甚至有人用JVCDVM70。
但是这些专业爱好者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拍摄素材从摄像机下载到苹果机或PC机中,利用专门的软件进行剪辑,成品既可以输出印制到35毫米胶片上供传统放映,也可以放到互联网上发布。也许某一天,还可以通过卫星传输到影院去放映。“这就像是桌面出版系统的革命,电影制作进入了出版领域。”苹果电脑公司的一位市场经理说。
电影将是最后一个被数字化的媒体。不过这事儿终于发生了,而且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数字电影正在迅速被重要的电影节所接受,比如戛纳,圣丹斯(日舞)。去年戛纳电影节的技术展示会上展示了各种各样新的媒介,比如一个5.9G的数字放映机,一大批数字长片,包括一部成本仅900美元的长片《最后的广播》。
《庆典》为世界各地的录像拍摄者带来了福音
严格地说,《女巫布莱尔》并不是一部数字电影,因为它是超8格式。不过它拥有数字电影的诸多特性:由录像带转成胶片,摄制成本低,与互联网的紧密关系。《女巫布莱尔》巨大的商业成功证实了数字电影同样可以进入主流电影。“现在有很多主流导演开始拍摄成本在200万、600万或1000万美元的数字长片。”美国下一浪潮(Next Wave)制片公司的总裁,皮特·布拉德里克说,“这是真正的主流趋势。”
他说,虽然在七八十年代同样有低成本影片,比如名导演大卫·林奇和斯派克·李当时都拍过,但毕竟唱者寡而应者寥寥,没有人想到它会成为一种成功的范式。90年代初曾出过一批成本很低的独立电影。布拉德里克把这个始于90年代初期的浪潮叫做“超低成本电影运动”。
早在1985年就有人把录像作为一种电影制作工具。独立导演罗伯·尼尔森拍摄了一部旧金山出租汽车司机一夜生活的长片《第七信号》,用录像带拍摄,转成35毫米胶片,在圣丹斯电影节上放映。但这部影片并没有受到好评。因为对当时的电影人而言,胶片(电影)使用的是艺术语言,而录像则属于肥皂剧的范畴。尼尔森至今仍在继续他的录像事业,同时还为一本数字制片期刊撰文。他说:“我觉得从一开始,人们就对录像抱有偏见。”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998年。丹麦导演汤玛斯·文特伯格带领他的5人小组,用索尼PC7数字摄像机拍摄了一部描述家庭矛盾的情节剧——《庆典》(The Celebration)。这部数字影片(数字录像片)不仅在欧洲电影界广受欢迎,夺得了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还因此得以在美国商业影院发行,这使得数字电影长片的概念广为人知。它为世界各地的录像拍摄者带来了福音。“它就像是数字电影中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布拉德里克说。
导演斯派克·李的上一部片子《山姆的夏天》票房失利,他正在制作新片《受骗》。他的摄影师艾伦·库拉斯说:“预算变得这么低,我们计划用DV来拍摄。”但对于一个电影人那受过训练的眼睛,数字摄像机真能获得摄影机的效果吗?库拉斯说:“目前技术绝对跟不上。你用录像带来获得胶片的效果,但不是代替它,因为录像带代替不了。”
但很多人不这样看。斯蒂芬·阿弗洛斯、《最后的广播》的导演说:“对绝大多数观众来说,绝大多数电影都可以以数字化的方式来观看(如DVD)。录像并不比胶片差。”
阿瑟·甲发是一位录像工作者,去年秋天他跑到非洲8个国家去拍摄《地平线的希望》,他管它叫“90年代非洲观察”。他使用的是一部索尼DX1000数字摄像机。他说:“录像是黑人独立电影的未来,录像是美国独立电影的未来。事实上,录像是电影的未来。”他认为不只纪录片,故事片同样可以用录像来拍摄。“因为,第一,用摄像机你可以无限制地拍下去;第二,摄像机的小巧使你可以与被拍摄者保持最亲密的关系。”
电影使人幻想,而录像只能催眠?
数字技术已经进入了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电脑、网络还是各种家用电器,各种家用数字媒体如CD和DVD。而20年来,好莱坞也正在一步步地数字化。从《星球大战》中的X翼战斗机到《终结者2》中的金属人,到《星战前传》中的喳喳·宾克斯,数字技术已渗入电影制作的每一个环节。
“如果你能支持一整套数字化格式,从拍摄到剪辑,到展示和放映,包括影片存档;如果你能把每一个细节都数字化,特技、作曲、化妆、蓝幕,那你就能保证质量,并大大方便这种媒介的使用者。”Quick Time软件公司市场部经理说。美国最大的独立电影人是谁?乔治·卢卡斯,他的《星战前传1》已经部分用数字摄像机拍摄,用数字设备做后期,把片断拿到互联网上供下载,并在美国的两家影院用数字放映机进行放映。去年夏天,另外两部影片,《理想丈夫》和《人猿泰山》也试用了数字放映。
批评家罗格·艾伯特反对数字化电影趋势。他说:“我们站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数字化放映会给国家带来很多收益,但却会破坏人们看电影的感觉。看胶片使心灵处在一种A状态,而看录像使心灵处在B状态。A状态导致幻想,B状态则导致催眠”
据估计,在美国,使用传统的放映方式每块屏幕每年要花费22500美元,一旦使用卫星传输进行数字化放映,这个价格要跌到450美元。难怪通过卫星传输放映,或者采用其他数字化放映模式,已经成为电影放映不可避免的趋势。
批评家罗格·艾伯特反对数字化电影趋势。他说:“我们站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他在给独立录像和电影基金会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数字化放映会给国家带来很多收益,但却会破坏人们看电影的感觉。”他坚持认为,胶片的物理化放映有一种纤细的美感,它产生于大脑读解那断断续续的图像的过程中。“看胶片使心灵处在一种A状态,而看录像使心灵处在B状态。A状态导致幻想,B状态则导致催眠。”在黑暗的影院里观看录像(数字化影片),人们得不到他们在看电影时得到的那种东西,但又不知道为什么,结果就只能是看电影的欲望逐步消退。此外,数字电影的贮存方式也令人怀疑,今天任何人去找一个旧的5寸软盘,都会持同样意见。
如果说关于数字电影有一个绝对的说法,那就是,没有一种技术能使技术本身变得更好看,或者使一部不好的影片变好。今天无数的新设备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更快地做事,但如果你想让人们持久地关注一部电影,那快和多是没有用的。“仍然要花时间来和电影生活在一起,发现你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国内一位年轻的独立导演说。
罗伯·尼尔森说:“我对数字电影的希望是,能够像汤玛斯·文特伯格那样,更近地关注人类的经验,人的位置,并且为此讲一个故事。也许这是一个陈词滥调,一代人里只有一两个天才,100年也出不了一个莎士比亚。但你可以期待。我希望由于数字电影(数字录像)的普及,可以导致一个更加关注人类经验的艺术运动:它观察人类经验,为之着迷,并思索它,思索我们这短暂的、奇特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