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涧溪》到《丧家犬》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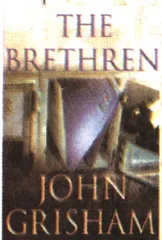
大地回春,美国的图书市场似乎也开始解冻,进入本期畅销书榜的竟多达7部新书。现在我们先来看看《涧溪》。
该书作者罗伯特·摩根现在位于纽约州北部的名校——康奈尔大学任教。他是阿巴拉契亚之子,具体地说,就是南北卡罗来纳州交界的群山密林一带,那里不但是他出生和成长之处,也是他的大部分小说的背景。他对18、19世纪美国的乡间生活研究透彻,所以他的作品中日常生活的细微末节写得栩栩如生,让人如身临其境。此前他的两部小说《穷乡僻壤》(The Hinterlands,1994)和《最真切的愉悦》(The Truest Pleasure,1995)也都是写得实实在在的类似题材。
《涧溪》是由一个名叫朱莉·哈门的坚强的17岁姑娘叙述的。故事一开始,就是两个冗长的死人场面,那种紧张气氛始终没有稍减。先是她的很小的弟弟得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慢性病,最后一口口地吐小白虫,挺恶心地死了。不久之后,她父亲由于长期患肺结核而去世。当年那里的医疗条件极差,中等发烧简直就和如今的癌症一样是不治之症。人们对疾病是那样的一筹莫展。
除去疾病的折磨之外,就是繁重的体力劳动。罗伯特·摩根是美国作家中为数有限的了解农村劳动的人,而且写起来还一丝不苟。例如,他可以不惜花费10页的长度描写杀猪,因为书中那些人物一文不名,为度过严冬而深为苦恼,一方面自然把每一件小事都办得很认真,另一方面也借以排遣忧烦。即使在朱莉父亲生前,她也在家庭农场上长时间地干活儿。当她抱着又一大捆木柴进屋时,她母亲说:“朱莉可以像男人一样干活。”而她自己却说:“如果有什么苦活要干,也只有我去干了。”她是个假小子,从来没时间打扮自己。所以当一个名叫汉克的既能干又英俊的小伙子向她求婚时,她颇有些不知所措。但他们的初吻还是让她恢复了女性的心理,她自忖:“这不是我,不过比我好,我受宠若惊了。”
他俩很快便结了婚,并翻过山岭,迁居南卡罗来纳。这对新婚夫妇在涧溪与一位年长的鳏夫在一处老房子中搭伙。新生活开始了。汉克找到了一个制砖的工作;朱莉则负责家务劳动。但几乎从一开始生活就脱了轨。汉克失去了工作,变得疏远陌生与牢骚满腹。那个老鳏夫原来贪色又凶残,很快便在一次油脂引燃的烈火中受了重伤并惨死。汉克和朱莉一时不知还能不能再在那房中继续住下去。冬天的一场水灾使他们唯一的一头奶牛丧了生,许多只鸡也同归于尽。他们发现了老鳏夫多年积攒下的一罐钱,重新燃起了一线希望;未曾想一名冒牌艺术家装出当地银行律师的样子,把那笔钱诈走了。随后又有一对骗子把他们仅剩的几个钱也洗劫一空。他们开始感到走投无路了。
当然,这还仅仅是他俩不幸的开头,后来还有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他们那种种艰难困苦可能会使生活优越的美国读者误以为是作者在故意夸大其词。其实,100多年前美国的穷乡僻壤的确如此,至少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会感到似曾相识的。作者并非只是一味地写生活的艰辛,其中也不乏苦中作乐的插曲,因而更显得生动真实。如这对小夫妻吵架后谁也不理谁,但柔情缱绻一番之后,又各自做起甜蜜的美梦。故事结尾处,朱莉怀了孕,但既没奶可喝,也没东西可吃。她说:“承认挨饿,尤其还是个成年人,实在丢人。”他们的困境引起了邻居的同情,一些人送来了些小礼物:两罐自制果酱,一些小孩的衣服。那景象感人至深。婴儿终于生了下来,由于妊娠期营养不良,小孩极其瘦弱,手指和脚趾像火柴头,胳膊还没有母亲的指头粗。简直令人不忍卒读。
另一部新书是卡尔·海阿森的《丧家犬》。美国人一向认为,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是藏污纳垢的城市。但过去几年中,卡尔·海阿森却通过他的几部小说,如《脱衣舞》(Strip Tease)、《旅游旺季》(Tourist Season),令人信服地指出,如今佛罗里达州才是全国最野蛮、最无知和最可怕的人聚居之地。目前他这部新作更将这一事实表现到了极致。
如其先前的小说一样,《丧家犬》一开始便是一个荒谬的前提,然后越写越怪。一个叫帕尔默·斯透特(原义为“果蛾鼬”)的闻人在高速公路上驾车行驶时,从车窗中扔出了一只小动物。跟在他后面的车中的人叫作退利·斯普瑞(有“交织着狂乱”之义),是个随着感情冲动而会维护树木的人。退利并不知道帕尔默是个与政客拉拉扯扯而且残杀弱小动物的人,却打定主意要捣毁帕尔默的汽车、破坏他的住房、绑架他的爱犬并诱引他的妻子。退利曾因炸掉叔父的银行而被罚以听取法律课程,如今有很多自由时间。
退利在执行他的破坏计划的过程中,发现帕尔默是腐败的州长的密友,遂通知的帕尔默,如果还想见到自己的爱犬,就要说服州长抛弃会进一步破坏佛罗里达野生环境的一项新的发展方案。这时书中又插入了一个受过心理伤害的的人,他专爱偷听人们遇到危险时所打的报警电话。不消说,在这一系列荒诞绝伦的人物及其作为中,也有些引人发笑的小插曲。至于全书的呼吁能否起到保护该地的生态环境乃至改变州政府的人选及政策的作用,则另当别论。
法国畅销书评
1789这样发明了大男子主义?
大革命200周年之时,法国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发现,当年革命领袖对于发动妇女参加游行示威毫不犹豫,比如1789年10月5日让她们去凡尔赛把逃跑的国王抓回巴黎。轮到制定宪法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妇女的选举权,而旧制度还赋予寡妇和女户主这一权利呢。女性主义者查证出《人权宣言》的内容之一就是剥夺妇女的人权,从另一角度看,男人把女人从政治逐入封闭的私人空间,为她们发明了“歇斯底里”的女性,男人同时也为自己发明了同样新颖且同样难以承担的男性。这就是哈歇特出版的新书《第一性·男性的变迁与危机》阐述的主题。
该作者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身体、运动和休闲历史的教授安德烈·罗歇,照他的论证,农民为了成为土地的所有者耗尽体力,工人为了获得更高的薪水四处奔波,学生为了赶快获得承认过早离开母亲的怀抱,总之革命给了男人一份有毒的礼物。为了成为合格的男性,他们被迫一面垄断事业的特权,一面在挫折中放弃“歇斯底里”的自然需要。本书写作模式不像学院派的历史研究,倒有点像巴尔扎克或左拉的文学作品。作者更倾向于使用见闻,他勾勒出了19世纪法国社会的部分面貌,而不是塞给读者一页页被学者奉为圭臬的统计图表。最有意思的章节莫过于“军队里的男性精神”那一章,他摘录了许多拿破仑军队士兵的家信,发现这些大革命子弟更看重的是忠于领袖,而不是热爱祖国,是光荣而不是平等,虽然他们也表示向往在家中床上善老善终,可挺住痛苦、挑战危险、慨然就死等字眼儿出现得更统一、更频繁、更真切。作者把这当作革命扭曲男人本性的证据,可《新观察家》书评认为,他论证环节的缺陷正在这里,因为拿破仑军队和现在的军队一样,也有女人在服役,而这些女人的精神跟整个军队的精神恰恰是有融合之处的。重差别,还是重平等,众说纷纭。 (刘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