茂名南路的怀旧情绪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唐波)

上海的一间酒吧(李晓斌 摄)
上海。淮海商业区,逛得有些累的梁小姐信步走进了安静的茂名南路。初春时分,路边的法国梧桐缀满棕色芽苞,等待萌发的绿叶将把街边的小店掩映在一片荫凉之中。
真实的阴凉是梁小姐伸手推开的玻璃门,一只只蝴蝶的铁花在透明玻璃的映衬下格外醒目。屋檐下,黑底招牌上写着两个红色的花体字——
花嫁
浦东川沙县人赵春兰被奉为上海女子时装业的创始人,因为收的徒弟都是同乡亲属的子弟,所以和男子西服业的“奉帮裁缝”相比,女装当然是“本帮裁缝交关好了”。
如今,在定制、售卖旗袍和唐装的花嫁店里,店长周女士已经不能确认裁缝师傅的帮派,但她强调“他们都是旧社会来的上海本地人”。“老师傅”有七八个,做唐装那个是家传第3代,年纪最大的已经70出头,“年轻时就是学徒,学做中式衣服的”。周女士拎起旗袍下摆,真丝的衬里隐隐透出密实的手挑针脚,“好旗袍的高衩可以合拢,因为老师傅手工好,把腰臀的线条收得服帖。”
房子是老板祖上留下的,营销方式是老式的口碑相传,“广告一分钱也没出过”。老师傅、老服装,老吆喝,生意却好得出奇:新世纪元旦,除了提前定制的,红色成衣全部卖完,“关门都关不掉,他们年轻人要玩通宵,都想买件穿穿……”花嫁的旗袍多是上海30年代的标准款型,因为受当时欧美服饰收腰和女性化潮流的影响,旗袍由清末的直板僵硬变得紧身高衩,突出女性高低起伏的身体曲线,从而符合30年代精致玲珑、开放活泼的名媛形象。
少许工薪人士为结婚而来,但主要顾客是外国人和外企的中方雇员。墙上镜框里,南美某国大使和夫人裹在描龙绣凤的红金面料中喜笑盈盈,他们为圣诞节特意定制了旗袍和唐装。这是1886年来华传教的美国人福开森开发的传统,他身穿朝服、足蹬朝靴、头戴花翎地收集大量相当罕见的织绣藏品,引发了国际上中国绣品的拍卖狂热。
对于静安希尔顿饭店的梁小姐,“有时一个月来几次,有时两三个月来一次”,定做了多少衣服、介绍了多少客人,恐怕自己也记不清了。如果说梁小姐和花嫁是个偶遇,那么对于关心时尚并身体力行的张小姐就是注定了。通过翻阅各种的中英文时尚杂志,英国某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张小姐迷上了1998年Christian Dior发布的“中国风”系列服饰,“我觉得那些绣花,织锦缎的图案真是太美了!……但人家是高档礼服,几十万法郎一件”,花嫁就不同了,一件上装的价格只是张小姐月薪的1/10。黑底金色团花的中式上衣,下装却是黑色泛银光莱卡紧身长裤和厚厚的松糕鞋,张小姐的搭配颇具后现代风格:“我喜欢中式服装,但生活在现代,传统的穿法肯定不够,要加些新的因素进去。”

在欧美已形成成熟市场的补子
上海1931's
离花嫁不过百米,在幽暗窄小的1931's酒吧,周璇尖细的嗓音从黑色密纹唱片里释放出来,被缓慢旋转的老式吊扇吹得若有若无,悄悄唤起了墙上月历牌女郎的无限风情。据说和花嫁一样,1931's的开设也是因了老板的兴趣。老板喜好收藏,月历牌广告画,美国的老无线电、菜刀样专熨裤缝的熨斗,吧台上的旧式留声机,30年代的上海世情随着这些琐碎的物件一点点展露在客人的眼底。菜单封面也是月历牌女子,和28元一杯的老上海盐汽水、家常芥菜肉丝炒年糕一起待价而沽。
在五星饭店免费提供的英文旅游杂志《That's ShangHai》里,1931's“不是因为菜肴,而是morning glory留声机,老上海张贴画和身着旗袍的侍者使它比周围的店更出名”。描摹精致的1931's旧上海布景吸引了中外时尚人士,报纸杂志争相报道,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的电视台蜂拥而至,每晚高朋满座,不预约就没有座位。Shirley小姐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按图索骥找到这里,却早没了座位,只好在附近的酒吧里闷坐一夜。
比较陶吧、织布吧、玩具吧的肤浅活力,1931's的怀旧情调似乎更有历史的凝重和文化的氛围,这感觉强烈吸引了自称“没有归属感”的张小姐。“在外企工作,不管你英语说得多好,思维方式努力向他们靠拢,除了工作还是没什么好说。”是否因为文化差异导致交流不畅?“当然有了,不过还有一点,我们做一样的工作,可我拿的是当地雇员的工资,他们拿的是海外雇员的工资,比我多三倍,不管我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和他们一样。”张小姐“有时会刻意换上中式衣服”,和朋友到1931's小坐,用音调活泼的上海话聊着衣服、男人以及从张爱玲时代就不曾改变的话题,“我喜欢这里的情调,很精致很优雅”。
钱宁在弄堂里长大,当他一有经济条件就搬出三世同堂的家,住进淮海路旁租来的一间10平方米的阁楼。“这样的气氛鼓励你幻想”,像1931's一样,钱宁在阁楼四壁也挂上了细眉红唇的月历女子。“有时睡觉前躺在床上,看她们有的打麻将,有的织毛衣,想想白天自己在广告公司那么累……也许我应该是坐在她们怀里的小孩子,一张脸喜气洋洋,看太太和姨太太们打卫生麻将。”1974年出生的钱宁在史书上读过,在考场上答过,知道30年代中国历史的风雨飘摇,但他更愿意相信且更容易接受月份牌广告画里的衣香鬓云,“谁不想过这样的生活呢”,钱宁半是解嘲半是辩解地说。
新与旧
同样的,“在英租界做生意,在法租界买房”,30年代传统生活方式仍然支配着美国公司雇员Shriley的选择。看着常熟路和茂名路之间的一幢幢高层涉外公寓,虽然Shirley已在万体馆附近购买了86平方米的房子,但“如果手头有可能,我还要在这里买房……因为这边热闹”。热闹也是传统,19世纪上海第一家欧式酒吧就在这里落户。而在1996年,仿佛一夜之间,各式的酒吧、餐厅、咖啡馆又出现在茂名路、衡山路的老房子里,卖西餐点心或上海家常菜,不定期举办“重回霞飞路”之类的主题派对,为长期生活在上海的6万外国人提供服务。和40年前的伙伴不同的是,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会说中文,熟稔国情,吃完爱尔兰炖肉后会叮嘱小姐开张发票;和40年前的伙伴相同的是,他们在上海投资、贸易,带来更多更新的汽车、香水、可口可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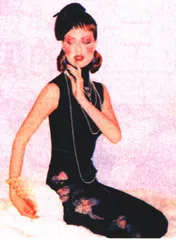
时装界也掀起了阵阵怀旧风、“东方情”
巨额的外资投入令上海日新月异。截至1999上半年,上海累计历年批准外商直接投资19700多个,吸收外资合同金额370亿美元,世界排名前100位的工业性跨国公司有57家在上海“落户”。1998年外商投资的汽车、通信、电站设备等六大支柱产业产值占据上海工业总产值的20%。根据《财富》中文版的调查报告显示,上海被评为最受欢迎的投资城市。
在雄厚的资本后面,是渐渐崛起的上海本土中产阶级的努力与失落。“也许可以做到人力资源部经理,但绝不可能当CEO。”在外企工作5年的张小姐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比一般人我们生活得要好,可永远也不可能进入他们的主流阶层。”和钱宁一样,在张小姐眼里,30年代是上海和西方流行文化结合的经典之作,旗袍自拟的中西和璧的名媛形象,1931's如古旧织锦缎的奢华氛围,渐渐消解着现实生活中的沉重与无奈。
相隔60年,历史的面目早已模糊,新与旧的对比令人唏嘘。淮海路上,蹬三轮车的老人如数家珍地指点你“白相”外滩的建筑——它们大多镶有一块咖啡色的小铜牌,这是上海市政府为保护少数著名建筑特意颁发的。而在对岸,作为上海新建筑的代表——东方明珠电视塔和国际会议中心正傲然矗立;曾经充斥着30年代欧美舶来品的先施百货重新开业了,但它是以上海第一家全开架的新型经营方式出现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投资15.7亿美元同样生产BUCK,但那已是90年代末的世界先进技术;“花嫁”工钱600元,加上面料往往逾千,而在方浜中路的服饰藏品市场,一件20年代的花绸女袄估价只是20~40元……
可是,怀旧仍然成为茂名南路的主题,成为弥漫整个上海的气息,这气息来源于索斯比拍卖行对乾隆年间的补子拍出的5000美元高价,也来源于法国时装杂志《ELLE》上Dior模特身着黑色绣花旗袍、佩戴和1928年的上海小姐郭守慈几乎同样的项链。事实上,John Calliano的设计绝不只是简单的重复,他用旗袍、绣花、折扇勾勒的是他的美人和他的中国。
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在西方70年代就开始进入的复古风潮的推动下,上海拥有足够的历史记忆实施怀旧,怀旧构成了上海这个城市的文化价值。但实际上怀旧只是卖点和噱头,是白领人士以壮声势的中国底板和为外国人的旅行明信片增添的异国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