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法改革说起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高昱)
“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对徐叶松案这样一起充满泪水和悲愤的凶杀案加以想象无疑是残酷的,但假如我们抛开法律是非的判断进行设想——这完完全全是一种假设:假设徐叶松真的不是凶手,那么就像他的律师所说的一样,是一起司法权利粗暴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巨大错误;而假设徐叶松确实是真凶——他的律师在辩护里从来没有排除过这种可能,只是在试图证明没有证据确认徐是真凶——那么徐叶松真的是异常狡猾,他尽可能地消灭证据,被捕后聪明地利用了侦查人员满足于获取口供的习惯性心态,转移了他们寻找其他证据的视线,用苦肉计等到法庭上一举翻盘,这种心智无法不让人叹服。
这两个假设虽然都属主观臆断,但它们非此即彼,总有一个是真实的。排中律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对无辜者的保护和对犯罪者的打击,有时候就是这样根本无法两全。保护权利、制衡权力和打击犯罪、控制社会秩序从来都不是一对可以轻易获得平衡的矛盾,在这个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出现两难抉择的时候,法治究竟该如何选择?
“这是一个司法公正的问题,更是价值取向问题,我选择前者,宁可错放,不可错判。”中国人民大学的何家弘教授的表态是旗帜鲜明的,“错放可能是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而错判不仅冤枉了一个好人,而且放纵了一个真正的罪犯,社会成本上的差异不言自明。”在何家弘看来,立法公正追求的是整体和普遍公正,司法公正应该追求的则是个体公正,“司法活动围绕着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只有从一个个具体个人权利的保护做起,才谈的上保护抽象的社会整体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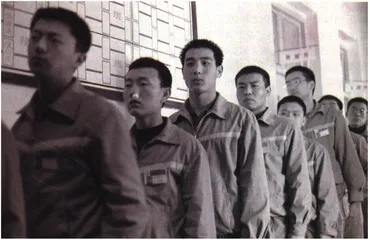
摄于北京某少教所,这些帮教对象正在被重塑为新人(娄林伟 摄)
“我们建立司法制度,其根本宗旨是为了强化社会治安,还是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同的法律精神,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诉讼和司法制度,两者的兼顾在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为世界上有些事特别是案件中的真实有时永远查不清楚,这个时候需要制度安排时作出选择:是选择把保护人权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维护社会治安放在第一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学博士蔡定剑同样选择前者,“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建立司法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选择后者必然对司法人员的行为采取宽容态度,这等于将每个公民置于司法权力的强暴和被剥夺权利的危险之中。”
蔡定剑把他最近的研究称为“冤案发生学”。“中国古代司法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冤案史,《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苏三起解》、《七品芝麻官》,中国古代最大众化的戏剧舞台上的司法就是一部部冤情控诉剧,中国古代人权受到的最严重的侵害之一就是司法迫害。即使是铲除封建专横的司法制度的建国后,有罪推定的司法思想和对社会控制的重视,使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仍旧杜而不绝。”蔡定剑给记者讲的第一个例子就足够触目惊心。1992年甘肃武威发生一起入室杀人抢劫案,当地警方不过是根据“作案者可能是急需要钱的人”一个推测,逮捕了三名无辜者,在逼供、指供和诱供之下,取得了与犯罪现场基本一致的口供,三人中两个死刑一个死缓,就在有关机关给办案人员颁发破案有功嘉奖令的时候,从广西桂林打来电话,他们抓住的另三名罪犯供认了在武威作案的全过程。
“对一个法院、公安局、一个社会来说,一个错案,一百个错案,在所有案件的百分比可能不算大,但对每一个公民个体来说,错误对他就是百分之百,这是不可以用任何代价来计算的。”蔡定剑引用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法官霍尔姆斯的话说,“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因为一次犯罪污染的只是水流,而一次错判污染的却是水源。这是培根说的。
要更现实的安全,还是要无法想象的司法人权?
“宁可错放,不可错判”,不禁让人想起6年前那起让世人瞠目的辛普森案。一位学者说:“辛普森案虽然说明了国家的无能,却说明了法治的成功,如果国家无所不能,那么要法治做什么?”美国人这种对法律至上和程序正义的尊崇令人心旌摇荡,为了那种程序上可见的,甚至是不完全的公正,他们可以不惜以实体上的公正和正义作为代价。那是他们的游戏规则,是他们几百年恪守的秩序。

又一次人大会的闭幕。我们对法治寄予着厚望(法满 摄)
20多年来,中国也一直在孜孜以求法治这个现代国家最富魅力的字眼。我们曾经骄傲地宣布制订了多少部法律,但最终发现,通过立法和条文许诺的种种权利,一到实际操作的时候却往往无法实现。人们把对立法的关注转移到对司法的关注,以1997年新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标志,中国逐步确立了从西方法治社会引进的法治概念: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疑案从无,程序公正,控辩平等等等。
然而,从法制到法治的转换也并没有将它面对的悖论解开多少。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现在所面临的犯罪高峰和犯罪升级。对没有成为罪犯和嫌疑人的大部分国民而言,社会治安是现实而具体的,在司法面前的个人权利反倒成了抽象的概念,要现实的安全,还是要无法想象的司法人权,人们给出的答案几乎是可想而知——这个抉择与法学家们的声音该是多么的不同。
与美国人讲究个性自由欲望和看得见的过程正义不同,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秩序是公共安全和个人禁欲,是结果的公正和真实。从传统的人治到现代的法治,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权威的问题,更多的是对法律功用的追究。在个体保障和公共保障这块跷跷板此起彼伏的两极之间,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激发着中国人个人欲望和保护这种欲望的要求,威胁着旧有稳定的社会秩序,由两极的双向拉动释放出的高速增长的犯罪,比美国式稳定的高犯罪率显得更为难以容忍。
枯燥的论述需要例证,即使没有关于司法改革的民意测验,我们也能从刑法的变更看出端倪。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蔡定剑博士告诉记者,1979年颁布的刑法典对死刑罪名的规定是十分慎重的,死刑条文仅15个,去掉反革命罪的普通刑事犯罪中,死刑罪名仅有13个,非暴力犯罪有死刑的仅有贪污罪。然而也就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面对日益猖獗的犯罪局势,“人民群众要求增加死刑的呼声一直很高”。于是在1981至1995年间我国最高立法机关先后制定的25部单行刑法中,规定有死刑罪名或对某些犯罪补充规定死刑法定刑的就有18部。15年时间,可处死刑的犯罪猛增到80余种,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我国平均每年增加3个多死罪,“在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而且死刑的核准权也大范围从最高法院下放到省一级高院。死刑适用的大幅度扩张受到国内绝大多数法学家的批评,但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立法者仍然不得不提出“不增也不减”的原则——只是由于一些罪名的合并,死刑罪名减少到60多种,原因很简单,犯罪形势越来越严峻,司法机关和普通民众普遍要求严刑峻法的呼声很强烈。
“乱世用重典”,这是中国千百年来口耳相传的济世名言,也是中国法治道路面临的独特规则。你可以说大幅度地增加死刑几乎是本能和直觉的反应,在中国这样一个报应观念根深蒂固、重刑主义思想有相当大影响的国家,这种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也可以用死刑刑罚量和犯罪量同步“双高”的事实证明扩张死刑立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犯罪率上涨,但谁又能想象,如果现在再以同样大的幅度削减死刑,又会出现什么样后果呢?
中国人的法治与现代化的法治
诚如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所言,制度是一种内在自发产生的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东西。法律不是一个产品,法治也不是某种可以“建设”的项目。“法律本身并不能创造秩序,而是秩序创造法律,”法学家朱苏力说,“作为社会的回应,法律的任务是将社会中已经形成的秩序制度化。”然而,这个国家对现代化的热望,把推进对现有社会秩序的全面改造和重新构建的期望没有保留地寄托在法治身上,希望它只争朝夕地创造出一种新的并且主要以先进法治国家为标准的社会秩序的模式,然后将中国社会装进这个模子里——像沉默权这样的法治话语的流行反映的正是对新的秩序和模式的渴求。
这样的法治更像是在变法,它必然打乱现有的秩序和规则。一个几乎无法避免的代价是,在一个发生着迅速变革的社会中,即使是长远看来可能是有生命力的秩序、规则和制度,也仍然可能因为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法验证它的生命力——甚至有可能夭亡。这个旧的要去、新的未来的间隔究竟有多长?“我们显然不应当简单轻易地以现代化这一宏大叙事为由牺牲中国社会目前所必需的秩序。当然,也不能相反。而如何协调我们对法治与众不同的需求,无论我们法学家和立法者如何信仰现代化,信仰现代法治,这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它更是深刻的道德问题。”朱苏力说。
我们对法治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像每个没有法律至上主义传统而又心向往之的国度所常见的那样有些矫枉过正的情绪。人权的尊重是社会民众价值观念的问题,犯罪的产生包含着深重的政治、社会、经济原因,现在法律成为了这一切的救世主。不幸的是,我们会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需要经常面临异常痛苦的抉择。就像辛普森的开释是一次法治的胜利,但站在被害者的一方来说,那又何尝不是一次法治的耻辱?对素来崇尚“包青天”一类人物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公道自在人心,正义无法伸张”的司法公正显然更难以容忍。对法治的理解,中国人和别人是不同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法律放回它在社会生活中本来的位置,什么时候我们的价值观念认可了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公平、正义,现在还在法学家热衷讨论的法治规则才会进入人们的心灵和身体的记忆,我们的心情也会平静一些。

什么时候我们能把法律放回它在社会生活中本来的位置,认可现代法治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曾璜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