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别无选择的悲喜剧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朱子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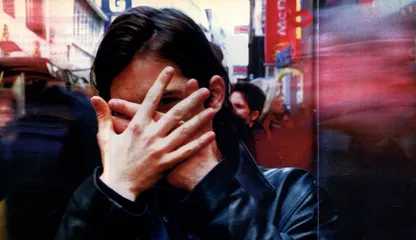
在这个世纪末,人们原有的生活计划和生活方式已经彻底面目全非了
1999年是个预言四起的年头。诺查丹玛斯关于世纪末灾难的预言像一个幽灵,跟随了人类400多年,今年该水落石出。不是所有人对此都无动于衷,就连美国《时代》周刊在预测1999年将要发生的事件时,其中一条也受其影响,含糊地指出:将有一件人们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
历史显得很凑趣,给我们的1999年安排了太多的灾难,“虹桥”倒塌、“2、24”空难、夏日蝗灾,以及舶来的“二恶英”,等等,一起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似乎都在向人们证实着,预言快灵验了。在这个时候,人们更容易把诺查丹玛斯《诸世纪》中“人们因瘟疫、饥饿、战争而死”的解释,和黄河断流,淮河、太湖、滇池的污染,南海、渤海“赤潮”等种种事件相连。一份最新统计数字同时向我们展示了大自然的回报:目前我国每8对夫妻中就有1对不育,元凶就是环境激素这一另类激素。
正如西方一位哲人所云: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也为我。“世界末日”的恐慌感就这样被引发出来,一点点地凝聚到了人们的心头。对于河北邢台的某些村民们,他们的恐慌来自于今年死去的两位产妇。年轻的产妇是在几年前住院生产中,因输血感染上艾滋病。据调查核实,全市19个区县医院用血量的缺口达8713个,全部为非法自采血或跨地区采血,没人知道该缺口中有多少为含病毒血液,也不知被输给了多少人。再者,死者们生前在当地门诊打针300次,多次用的不是一次性针管。贫穷的村民们为了省下5毛钱,也往往不用一次性针管。艾滋病的恐慌就像一粒粒种子,已播散到村庄的每一个角落,无法逃避,成了村民们难以醒来的梦魇。没有人知道,谁将是下一个。
无论是邢台深受艾滋病困扰的村民们,还是远离邢台的都市人,恐慌更多地显示在人们生活的现实和困境中。在这个世纪末,一些令人惶惶的事情像一股寒气总是无情地渗入我们的体内,“通货紧缩”的幽灵游荡在中国大陆上空,人们开始用“萧条”、“不景气”来形容眼下的处境,物价连续下跌,一份财经杂志如此描述:“日子好像从来没有这么难过,工资条上的数字凝固了,但是没有人敢像过去那样随随便便跳槽,因为每个人周围都有一个下岗的朋友,人们还在买东西,但感觉已大不如前……”
尽管传媒曾将居民们的储蓄比喻成“笼中之虎”,但政府的7次降息,也未能唤醒这只沉睡的老虎。建国50年,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未来真切地感到恐慌。经济学家汪丁丁的解释是,人民把储蓄当“保险”用了,他们为未来的不确定而储蓄,在这样的一个转型期,住房、医疗、教育、失业、养老——没有哪一方面是有确定保障的,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越高,人们的恐慌感也就越明显。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显示出,世纪末的人们感到恐慌的概率是50年代的10倍。有人把这种恐慌归为是经济起飞时代的焦虑,似乎应验了彼得·德鲁克那句漫不经心的话:“我们现在知道了,在一个经济飞快成长的社会,都有这种现象。”
在今天,没有人会忽视这样的事实: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令一位中学生百思不解的是,她那“辍学做工的同学辛辛苦苦干上一年所挣的钱,为什么还不够城里同学一次生日吃喝掉的”。毫无疑问,今天的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喜欢拿自己跟身边的人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被时代所抛弃的恐慌感使得各种技术培训的场所人满为患,人们开始盲目地追求着那些可以在人才市场上作为硬性指标、增加竞争筹码的学问。于是,求知的不真诚和生活的浮躁感就像两重阴影笼罩着我们头上,使我们的恐慌感挥之不去,因为,如果你不恐慌,你或许将失去一切。今年夏天,发生了南京5名大学生应聘当保姆的事情,相比之下,今年发生在中科院的一场人事“大地震”显然在人们的印象中更为深刻,中科院下属的科研院所或合并或重组,单数学所的重组就使得106名研究员们遭遇下岗,一位下了岗的研究员痛心地说:“我们这些人为科学奋斗了一辈子,现在让我们重找出路,我们还能干什么?”
在这个世纪末,人们原有的生活计划和生活方式已经彻底面目全非了。也许,感受最深的莫过于在家里等待着丈夫回家过夜的妻子们和等待子女回家吃饭的母亲们。没有人再敢于为自己到海南出差的丈夫打保票,北京一位妻子甚至开明地给丈夫的行囊里塞进安全套,然后“贤淑”地嘱咐丈夫要顾及全家人的健康。而11月1日正式投入实施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也破天荒地规定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夜不归宿。你可以笑话那位妻子姑息养奸,也可以责怪法律的制订者们不近人情,但除了这些,他们又能怎样呢?
恐慌的情绪也蔓延给我们祖国的花朵,“欢乐的童年”在这个世纪末已变得可望不可及。身体越来越差,眼镜越来越多,情绪越来越沉闷,心理越来越扭曲,因为不堪忍受重负自杀身亡和离家出走的事例已数不胜数。贵阳一个10岁半的小学生因为背不出学校创“卫”所规定的健康常识自缢身亡;成都三位初一女中学生1个月内先后跳楼,二死一伤,她们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另一个12岁的小学生则因为被老师加罚抄写11遍课文而自杀。一起起自杀事件笼罩在每所学校里,也笼罩在每一个有孩子的家庭里。你可以说现在的孩子缺乏心理承受力,但成年人又怎么样呢?安眠药的畅销和精神病患者的剧增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对大多数人来说,预言中的天灾人祸并没有发生,但弥漫在空气中的沉重和心里的恐慌却依然使人透不过气来,这其中,有自己选择的,有不得不忍受的,更有这个高速变幻的时代赐予的。在这个时候,也许我们已经忘记了,90年代我们是在一种乐观的期盼中开始的。没有人会料到,我们竟会在一种恐慌的情绪中匆匆地结束我们的20世纪。我们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用崔健的“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来解释这种感觉了。“现在是世纪末,我希望它也是世界的末日”不少人开始把上世纪末奥斯卡·王尔德的抱怨挂在了嘴边。
新年快到了,“咚咚”的爆竹声也快炸响了,也许,用恐慌来解读世纪末似乎有“杞人忧天”之嫌,中国人历来无畏、乐观,“天塌下来众人顶”,但是,我们有必要在这个世纪末看清人类的真实环境。我们更愿意新的世纪能带给人们美好的一切,阳光、鲜花、爱情,还有人们所渴望的金钱。但恐慌的感觉显然不会随着大预言的“破产”一起留给1999年,或许,我们能做的就是使这个悲观的字眼变得喜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