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身伤害》到《幸运的女儿》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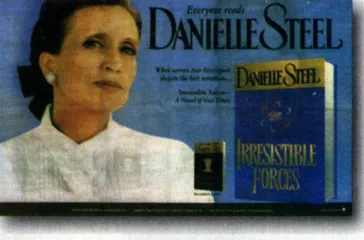
在本期的7部新作中,至少有两部的作者是我们熟悉的,她们都是女作家。一位是多产又题材广泛的丹妮埃尔·斯蒂尔,另一位则是苏·格拉夫顿,上次她的系列侦探小说上榜时是“M”——连续阅读本刊的读者大概还记得,她以私家女侦探金茜·米尔霍恩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依次以拉丁字母表排列,每个字母都代表一桩案件的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本期已写到“0”,代表的是“逃脱法律”。
《人身伤害》是上期就上榜的,我们尚未及介绍。作者是司各特·图洛(Scott Turow),他在这部新作中刻画了一名无法无天却又具奇特的吸引力的律师罗比·费沃。罗比作为一名演员未获成功,但他喜欢引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著名的俄国戏剧大师,世界戏剧三大体系之一的奠基人)的观点,且视人生如戏;而在这座人生舞台上,他却得心应手,扮演什么角色都不曾失误:无论是甜言蜜语地争取一位当事人,还是将他的梅塞德斯汽车装扮成新款。他对自己一贯的弄虚作假大言不惭:“这世上确实是一片混乱和黑暗,我们若是装作矢口否认的样子,那本身就是做戏。我们全都身处舞台,说着自己的台词,在某一时刻扮演着我们力所能及的角色,律师也罢,夫妻也罢。”但在他正直之时也直言不讳:“我说了谎,好吧?我一直都在说谎。”莫怪他成了肯德尔(意为“点燃”)县一名最成功的人身伤害讼师了。
不过,最高明的骗术也有失手的时候。联邦律师斯坦·显内特发现了罗比的秘密存折,是用来向法官和有关人员行贿以便赢得官司的。斯坦急于借此发现清理该县法院并进而推翻其后台亦即斯坦的对手、极有影响的大法官,便给罗比提出选择:要么揭发同伙,要么独自承担全部罪责。罗比无奈地屈服了,同意继续扮演他最擅长的角色——表面上和蔼可亲的腐败分子,不过他身后有了一群联邦调查局的技术人员记录他的言行。其中一位名叫伊旺·米勒的女探员被指定为他表面上的律师助手和情人。
罗比的妻子患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已成不治;他虽宣称忠于病妻,但尽人皆知他是个好色之徒。罗比发现伊旺对他的魅力无动于衷;原来这位便衣探员不但善于伪装自己的真实身份,也巧妙地掩饰着她秘密的同性恋行为。随着情节的发展,两人的帷幕和面具也逐渐剥去,这部分写得引人入胜,显示了作家的功底,而且与层层揭露骗局的主题相扣。
司各特·图洛已经写过5部法制小说,但这一次无论从深度上还是广度上都臻于完满,被评家称为这一题材的范本。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玩世不恭的浅薄层次上,而是深入挖掘潜藏在法制不公下面的根源。这样的题材恐怕有其普遍意义。如果以保证法律为己任的律师在撒谎骗人,那么岂止是“人生如戏”,简直成了“人生如儿戏”了。公正与真理一旦堕落成儿戏,人们还有什么指望呢?
另一部小说是《幸运的女儿》,作者伊莎贝尔·阿连德是智利人,曾任记者。1981年流亡委内瑞拉时,以年近40之晚龄才开始小说创作,以给她百岁高龄的祖父写信的形式发表,后来被改编成了电影。从她的经历看,笔者估计她是前智利总统、智利社会党创建人及领袖萨尔瓦多·阿连德(1908~1973)的女儿,他于1970年当选总统后因执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引起了1973年9月的军事政变,惨遭杀害。伊莎贝尔在90年代中止了小说创作,撰写了两部回忆录:关于她女儿之死的《波拉》(Paula)和关于人生肉体之乐的《阿芙洛狄特:感受的回忆》(Aphrodite:A Memoir of the Senses)。
此次这部原文为西班牙文,经玛格丽特·塞亚兹·皮登译成英文的近400页的新作是一部历史小说,起始于1843年,时间跨度约10年。书中有众多的人物,主人公叫伊莉莎·索玛斯。她在智利的英属殖民地瓦尔帕雷佐长大。伊莉莎是个孤儿,出生后即被抛弃在英国进出口公司的门口,被公司的业主索玛斯一家(罗斯小姐及其兄弟杰瑞米和约翰)收养,从此过着有钢琴教师、穿浆洗的衣裙、出入社交俱乐部的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伊莉莎并未感到不自在,因为英国人和智利人有许多共同点,包括遵循传统、热爱祖国和日常生活中的一成不变。但她仍觉得难以融入那个家庭。杰瑞米认为她不知自己的社会地位,罗斯对她喜欢待在厨房与厨娘兼管家的弗列茜娅大妈厮混颇感失望。那位大妈在一群动物身上花费了很多时间,其中有一只为伊莉莎提供过羊奶的母山羊,“要是杀了它,就等于弑母”。
伊莉莎后来爱上了索玛斯贸易公司的一个普通职员、激进的安杰塔,并为寻找北赴加利福尼亚淘金的这位恋人而出走。路上与她作伴的是一个叫陶坚的中国人——作家在回忆录《波拉》一书中就写到一位针灸医生,并表示将来会把他写成小说中的人物。本书中的陶坚色彩鲜明。
伊莉莎在加州以在妓院中弹钢琴为业。她发现装扮成男孩更自由,就此女扮男装,而且得了“智利男孩”的绰号。她和陶坚有过离合,后来她脱下男装,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评家认为,该书的情节和写法更像电视连续剧而不像电影,意思是精巧细腻有余,波澜壮阔不够。无论如何,伊莎贝尔·阿连德是想在书中展示一种文化上的冲突和融溶。
推介“外国佳作”
法国文化部组织的“外国佳作”活动始于1987年,每年从某个国家邀请一群有代表性的作家,向法国公众推介他们的作品。今年被推介的是来自捷克的13位作家,《解放报》重点访谈了37岁的亚希姆·托波尔和70岁的扬·特雷弗尔卡。
托波尔从小就反体制,少年时代给地下摇滚乐队写歌词,后来写书,出过诗集和6本小说。他说自己写的《姐妹》一书完全是“不可翻译”的,因为“旧体制下捷克语就像被狗看着一样,1989年以后出现了至少两万个新语汇,正是为了表现语言的变化,我才写了这本600多页的小说”。虽然不可翻译,这本小说还是被译成了德文和匈牙利文,并使托波尔在欧洲出了名。此次他的《安热出站口》被介绍到了法国,主人公雅切克住在安热地铁站附近,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自己别在某一天突然变疯,结果有一天他跑到精神病院去询问怎样才能让自己不变疯,在那里他发现了自己其实早就疯了,跟所有窃贼、杀人犯、吸毒者和胆小鬼一样疯。后来他去了巴黎,发明了一种可以让人忘记一切的毒品。法国书评界认为这部小说写出了过分宣泄、神经质、无根的感觉和无法对抗的封闭世界,托波尔则把自己所写概括成“后共产主义的特征之一:以前人们觉得缺少自由,如今好像想什么就可以有什么,可就是少几百万的钱”。
特雷弗卡尔是“布拉格之春”的知名作家,受前政府迫害的时间和受西方人关注的时间几乎一样长。这次在法国出版的作品有《向疯子们致敬》,讲的是一个农民把自己藏在谷仓里偷窥妻子以便了解“没有我之后,生活是什么样子”,杂文集《被诱惑的与被抛弃的》,小说《半岛精神》和喜剧《大工地》。他对前去采访的法国记者说:“在我这个年纪,我感到强烈的欲望和意愿,要影响事情的发展。我相信只要说出真话,事情就会变化。我几乎失去了耐心,可有些话必须重复地说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