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
作者:王珲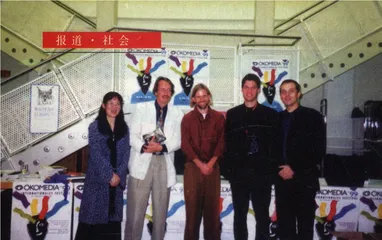
李皓(左一)和评委、制片人在一起

生态城市弗莱堡
一个8分钟的电视报道,制止了以四川洪雅地区为代表的几百万天然林被盗伐的命运。这就是影视的力量。日前,中央电视台唯一的新闻性环境栏目——《环保新干线》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重大改版。制片人任学安告诉记者,借助电视传媒广泛而通俗的特点,他们要让《环保新干线》成为环境保护运动领域里的权威!而塑成权威的关键是:跨出局限。在栏目组举办的策划会上,农业、林业、水利、气象、建筑多个领域的人士首次成为邀请对象。这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号。事实上,环保从来就不仅是环保界的事情。从德国弗莱堡国际生态电影节担任评委回来的李皓博士对此有更强烈的感受。
生态电影的聚会
1999年10月6日是弗莱堡第19届国际生态电影节开幕的日子。共有45个国家370部制作于1998年以来的影片送交组织者——德国生态媒体研究所。知识型市民和学生是电影节的主要参与者。电影节分为儿童专场、成人专场。长达1个多小时或短至5分钟的影片以2分钟的播放间歇密集地展现给观众,主题从欧洲的狩猎传统、生物物种的变异到工业国家的环境后果等,视野遍及全球。
李皓和评委们就坐在观众中间。每天从早晨9:00开始,眼不停歇地过滤着一部又一部经过初选的影片。在电影节上播映的54部影片中,至少有20部影片李皓希望能引进中国。真正的投票评选日在9日进行。引起最大争议的是欧洲电视片奖的评选。争议源于不同国家的评委们对问题紧迫性的关注。李皓说,她最想把奖项给一部反映丹麦船商将废旧船只运往印度海岸拆卸的影片,“这部片子非常好地揭露了发达国家转嫁污染的不道德行为,有诚实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态度和勇敢的报道精神,我觉得对西方和东方都有警示作用,可评委们没一个同意”。
奖项最终给了德国纪录片《狂躁的海风》。该片讲述德国为发展清洁能源专门成立风能发电站推广机构,遭到了当地居民莫名其妙的抵制。大量调查后发现,位于波恩的一个办公室源源不断地向这个地区的居民寄匿名信,宣扬风能发电的种种危害。事实上,此办公室属于德国一家著名火力发电电力公司,这家公司因害怕损失用户而不惜欺骗民众。来自德国和法国的评委们认为,该片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环境保护目的的尖锐对立。
尽管有争议,弗莱堡生态电影节在面对21世纪的环境思考上,仍就几个原则达成了共识:反对环境污染应该是每个国家的公民都要有的基本行为准则;把尊重生态平衡作为常识观念;生态环境的道德观一定是全球性的;对社会模式的思考应作为电视传媒启示公众的重要内容。
投向中国的眼睛
令李皓最为兴奋的是CCTV《人与自然》选送的专题片《拯救绿色》获得评委特别提名奖。在“中国与环境保护”专场,70分钟的《拯救绿色》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这种情况在整个电影节上并不多见。评委卡尔·费希纳先生(德国焦点影片制作公司独立制片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他承认,自己被这部中国影片深深地震撼,片中所展示的中国百姓的善良和大自然的美景是他从不了解的。他认为电影节上最佳生态片非《拯救绿色》莫属。
然而,由于另一位评委的极力反对,使《拯救绿色》最终失去了进入正式奖项的机会。反对的一条重要理由是,《拯救绿色》看到的只是政府下令禁伐,没有表现出中国民众自发起来保护森林的行动。其实,观众也向李皓提出了类似的疑问,“《拯救绿色》系列片是政府的宣传还是反映了中国的真实情况?”“《拯救绿色》片在中国的电视台播放没有?中国观众有什么反应?”他们甚至关心“中国政府的禁伐令是否能真正做到?”
事实上,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方式。1998年的《人与自然》开始对自己固有的赞美生灵、远离中国的节目形式进行改版,国家面对7、8月的滔天洪水发出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紧急指示触动了年轻编导李莉。从9月开始,她和摄影师为这部专题片奔波拍摄了5个多月,从大兴安岭到海南岛,李莉走了黑龙江、吉林、四川、云南、海南五省,拍摄了80多盘录像带。
拍摄的过程极为艰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当地政府,更为艰难的是,中国天然林的砍伐很多已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在进入四川阿坝之前,省林业厅的人干脆表白:“最好不要拍了,去了你们的人身安全我们管不了。”李莉告诉记者:“我们去的时候,四川已经下达了全面禁伐令,到1999年6月就不允许再往外运木材和进行木材买卖。但在往阿坝去的路上,搞运输的藏民为了在期限之前再挣点养生立命的钱,还是疯了似地往外抢运,山路上都是严重超载的卡车,歪歪扭扭跌跌撞撞地开过来,翻车的好多,太沉了,根本开不动!可是他们只能这么干。”
“天然林保护其实就像人走到悬崖边,再往下一步就完了,必须得停。我以前也只会发些很表面的、轻松的唠嘈,但这一次真是很扎实地了解了中国环境的现状和复杂性。在那些地方,人和自然的关系太直接、太尖锐,都是直接的索取、直接的报复。解放前阿坝天然林的覆盖率是60%以上,而一直以来人们都在砍天然林,覆盖的只是人工林。人工林生态系统太单一,根本起不到天然林完整而稳定的调节动能。去年的那场洪水把林场的设施都给冲光了,泥石流直接冲上街道,光阿坝就有1500多条泥石流,弄得特别惨。国家的保护政策就是停砍天然林,这一步非常重要。”
李莉告诉记者,是那些在深山老林里脸上带着高原红的伐木工人打动了她,“他们太苦了,就是为了生活,挣一点钱,长年都不能和家人在一起,心地却非常善良,你就觉得单纯地批评他们没有意义。现在国家每年要拿出60亿元投入到天然林保护,让这些伐木工人变为护林人。让人看到希望和出路不是很好吗?”
跨越东西方的思索

每一个细节都体现着人和环境的关系
短暂的生态电影节给了李皓许多重要的信息。美国纪录片《露娜——与大树生活在一起的女孩》讲述了16岁的露娜为了保护家乡的大森林,以居住在树上的方式向伐木商的电锯抗议。她成了美国青少年的英雄,更多的青少年组织起来,抵制伐木商进入森林,但他们却被警察用向眼中喷洒辣椒面的方式驱逐……面对大量的影片反映的西方环保事件,李皓说:“我觉得没有哪个地方的人是自然而然懂得环保的,生活在发达国家的人也很无知,不必把中国的老百姓想成跟他们差距很大,关键是国与国之间的环保信息交流渠道一定要疏通。”
用幽默、轻松并且充满美好情感的手法阐述环境问题将是环境教育的发展方向。“要出路,要希望,不要让大家一想起环境问题就感到头疼和失望,这也是我们评选的出发点。现在环境教育要让人们用振奋的心态来面对环境。”李皓说,“环境保护并不是个奢侈的事情,有时不花钱,治理效果却很好。关键在于观念上的转变。”
也许影片《禁区中的生命》便令人振奋。这部影片描述,在东德某露天煤矿,大量的开采使得这里地表裸露,寸草不生,成为德国绿洲中的一大片沙漠。原东德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试图恢复这里的植被,始终不见效果。两德统一后,计划被搁置。几年后,这片被废弃的荒地已然草木繁盛、动物出没。“其实,大自然的自我恢复能力是很强的,不要老是以为只有人才有这种力量。”李皓认为,“完全没有人涉足,也没有资金消耗,生态就复苏了。这不是个很好的启示吗?”
李皓的中国式的价值观对于《我们四人走向幸福》的理解引起了评委们的兴趣。片中讲述了两德合并后原东德集体农庄的农民的生活,有自己土地的农民有了新的失落。有一户农民贷款买了联合收割机,机械化耕作让他有了更多的土地。高投入、高产出,每天农民都守坐在电脑前,查信息、做买卖,从早到晚不能停歇。另一户农民保持着自然农耕,用马犁地,不撒农药,积有机肥,种出来的农产品拉到集市上,大受欢迎。他晚上休息,白天工作,生活富足。影片的结尾是这样的:在一个晨曦充裕的早上,农夫和他的狗蹲在地头,看着不远处终日与自己一起劳作的马产仔,阳光射在初生的马驹踉跄站起的身上,农夫的眼里挂满喜悦的泪水。
“这部影片使我震动。此时人和牲畜在那儿,发生着生灵间的情感交流,而面对大机械,这些感觉是不可能有的。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到底应该由什么组成?什么是幸福的感觉?如果你体会不到,也就无所谓幸福。”李皓说,“我讲这些看法时,其他评委觉得非常独到。从《我们四人走向幸福》的片名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人已经开始反省自己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观了。中国百姓以前常说‘知足者常乐也’。影片完全纪实,没有评论,但传达给观众的信息是:那位保持传统农耕方式的农夫过着幸福的生活。”
2001年有一种可能,弗莱堡生态电影节的组办者期望在中国的五大城市办一个生态电影节,届时将有更多的思索、更多的交流产生于东西方之间。
第16届弗莱堡生态电影节获奖名单
最佳艺术制作奖:巴西音乐片《沿着Capibaribe河的旅行》(颁发金猞猁,无奖金);
最佳新闻报道奖:德国纪实片《为水的血战》(颁发金猞猁,无奖金);
最佳自然片奖:澳大利亚科教片《沉默的珊瑚礁》(颁发金猞猁,无奖金);
最佳儿童片奖:拉脱维亚动画片《鸟屋》(颁发金猞猁,无奖金);
欧洲电视奖:德国纪录片《狂躁的海风》(颁发奖章,无奖金);
迪特弗特青年电视片奖:美国纪录片《露娜——与大树生活在一起的女孩》(奖金5000德国马克);
德国环境部奖:德国科教片《禁区中的生命》(奖金5000德国马克);
弗莱堡市鼓励奖:俄国纪录片《拯救和保留》(奖金1万德国马克);
评委特别提名奖:中国专题片《拯救绿色》,德国专题片《科索沃战后的环境危害》。 环保新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