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爵士 中国制造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刘索拉演出实况
印象
不是我无事生非地突然想起了十几年前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是今年北京的国际爵士音乐节上,刘索拉的一台爵士乐演出又一次让人感受到她的能“造”。不知道说她能“造”是不是准确,反正“造”不就是可劲儿地挥洒吗?当年她写了《你别无选择》后,把一大溜人煽惑得都跟没了选择似的,这次她以音乐人的身份出现又把听众们煽惑得也想跟着她喊两嗓子。就连我这种自认是很收敛的人,读她的小说和听她的音乐都好像能给心口戳个洞,不经意地让那么点未假修饰的真意流了出来,那种与生命有关的真意是无法选择的,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有就是有,没有的那就谈技巧。就算有,也得有机缘去触动它,记忆中刘索拉的小说就是这么个机缘。
已经说了,由头不是她是小说,而是她的音乐。11月10日,北京保利大厦,“刘索拉和她的朋友”在这里演出,作为爵士音乐节的一台节目。北京的国际爵士音乐节是亚洲最大的专业音乐节,今年是第7届。爵士乐在我们这儿可能不是那种蓬勃强大的乐种,因为它的技巧中有很多即兴的东西不是学习和演练就能成就的,它和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感悟方式息息相关,依蓝调的血统,它散漫放纵,刘索拉说,这对美国黑人来说是小菜,对她这种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人来说,是豁命。
我不是爵士乐爱好者,仅仅是因为刘索拉去听的,并且我知道为此而去的不是一两个人。开场,就听她念叨了一堆礼节的事,然后给观众来了一个被批斗式的鞠躬。“她的朋友”包括三个演秦者——一个鼓手,一个弹吉他的,这两位是黑人,一个抱琵琶的中国姑娘。刘索拉以唱与他们合作,像是萨克斯管或小号的位置,听不清她唱的是什么,大概也无所谓,但是能听出中国节日里的喧嚣声,京韵大鼓的调,可能还有西北的腔。新鲜的是,她不仅把这些腔调重写过,而且是放在那么个演奏组合里。有几个曲子听起来就是铺天盖地,旋律感拉着人别想安宁,同时又好像有自由的舒放和幽默的表述在其中欢腾,鼓和吉他已经够兴奋了,那把琵琶让人觉得它要是不够皮实就钉不住,就像刘索拉调动人声的表现力一样,琵琶也被调动得超出了常态。到了另一曲音乐,旋律忽然变得悠长飘扬,有些忧郁但没有忧郁那么沉,好像一只个头不小的鸟在清冷的冻日蓝天中飞着……
对话

演出结束后,观众请刘索拉签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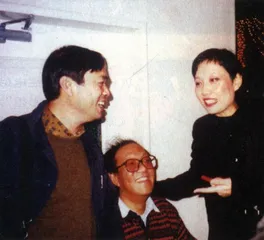
刘索拉和她的朋友,作家史铁生,摄影家鲍昆
在我对爵士乐的可怜的知识里,只听过一个老的阿姆斯特朗,一个不老的汗莫,一个雅的格什文,一个流行的斯蒂文·旺德,根本猜不出爵士乐的边界在哪儿,对于爵士乐爱好者来说,就有人觉得把她的音乐放在爵士音乐周的演出里,可能不大对头。要这么一说,问题就来了:
刘索拉答:我吸取爵士乐的形式,但也不非得是什么,你说它是什么就什么吧,给搁一摇滚节我也能进去,什么音乐节我都能进去就行了,这就是我的职业,我没有那么多局限,非得放到哪儿。
问:你说是吸取爵士乐的形式,但是爵士乐那种固定的风格好像不明显,是不是古典作曲方式的缘故?
答:说古典音乐与爵士乐结合,在我这儿就是按学院派方式作曲,同时,在演奏上保留爵士乐的自由发挥,和乐队之间的配合,互相呼应,就是即兴,这是特别来劲的。那不是学来的,那是灵魂里的东西,在一个好的演奏家手里,能出奇迹,那种运动感和效果不仅是写出来的,是演奏出来的。这些音乐家的好处不在于能照着你的谱子弹下来,是他能放纵音乐,他可能弹错,可能离谱,但是他弹出的那两个音儿,是换个人弹不出来的。这是美国爵士音乐中的生命,是从蓝调来的,只要蓝调在,音乐就必须从身体中来,这种东西不是在谱子上。有时候,他一高兴,“嘭嘭”两声鼓给你,你就得应着他往圆里找,但是我特别尊重这些音乐所以才有这种可能。不是说像学院派的作曲家,谱子写得特别特别难,写得音乐家根本演奏不了,使劲虐待人家,人家没辙,这是他的活儿,还得演。但是我合作的这些人他们要是演奏着不顺,人家能说我不弹了,我弹不出来!我还得给他们按摩。我的音乐家都是这种人。按学院派方式作曲有个好处,它有更宽的路子,不拘泥爵士的固定程式,在音乐结构上更宽,变化更多,也能更多地吸取别的音乐类型,本来爵士乐也是一种对外界各类音乐的形式都开放的音乐。
问:关于中国的音乐元素呢?还有别的艺术家,也都在用中国传统特色的东西,不仅在音乐中,也在别的艺术种类中比如绘画、装置、电影等。对这种方式也有一些不以为然的议论,比如对一直使用中国文字符号的徐冰,还有像几年前说张艺谋的电影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挪用是迎合西方,诸如此类,你怎么说?
答:别人的事我就不管了。就说即兴,音乐史上,好多是即兴的,如肖邦、李斯特,只不过他把谱子记下来了,很多爵士音乐家不会记谱,这就造成了一种误会,以为传统音乐是不即兴的,只有现代的试验性音乐和爵士乐才叫即兴。再细想,中国的传统音乐必大多来自即兴,但因为有人记谱把它们固定下来,传下来,到了后代就成了不准弹错的曲目。爵士乐是唯一没有延续这个规则的,它太主张演奏者的个性,你去采风,在中国民歌里也有这种很个性的。反正我没原则,哪儿的东西都用,什么非洲的、印度的,什么都可以用。用中国的元素也一样,这里边有可用的东西,还有,就是因为我熟悉,我能感觉到这里边那种可以发挥的东西。
也许听不清词倒对了,更能感受到音乐中抽象的张力,我也就理解了刘索拉到美国后倾心美国黑人音乐的理由,那种音乐不是针对生活,而是针对在生活中流动的生命动感,不论是伤感的,还是困惑的,或是欢乐的;也就同情了无论走到哪里的人,只要尊重自己,不会回避生命里所有牵连的东西,不管是乡音古调,还是东西南北大纠缠,只要它与你有关,就与你的艺术有关,才与听众或观众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