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亮妈妈》,新鲜巩俐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卞智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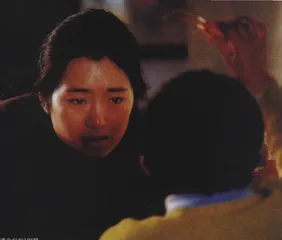
《漂亮妈妈》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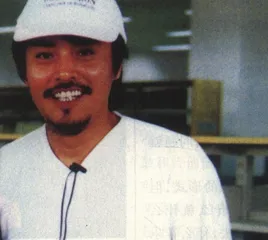
导演孙周


如果《红高梁》、《菊豆》、《秋菊打官司》和《霸王别姬》没有巩俐,那就像画画没有红颜料,宴会没有酒。但也因为这些影片,巩俐被定位成一个性感的、专演艺术片的国际女明星,我们想不起她在其他影片中的其他形象:《古今大战秦俑情》、《画魂》、《天龙八部》等。然而《荆轲刺秦王》中的赵姬形象已经很苍白了。
《漂亮妈妈》是为巩俐订做的——在《刺秦》的剧组里,饰演燕太子丹的孙周与饰演赵姬的巩俐一拍即合,决定拍一部以巩为主角的现代城市戏;但这部戏却又不是为巩俐度身订做。孙周说,他给巩俐唯一的要求是,把她过去的成就仅仅当做一种体验,而不是经验。这部影片里,巩俐一反她那已经成为经典的野性、刚烈、执拗的女性形象,扮演了一个六神无主的漂亮妈妈。
漂亮妈妈孙丽英是个普通的城市女性,原本“在家靠丈夫,出门靠单位,未来靠儿子”。但丈夫离了,工作没了,儿子是个聋儿。她唯一的愿望是儿子能像正常儿童一样去上普通小学。她去摆摊卖书,去做家务小时工,去送报纸,只为了能与儿子朝夕相处,教会他这个念“花”,那个是“红”色,好让他通过入学考试。但儿子还是上不了正常小学,他无法接受外界的歧视,大声问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戴助听器!”孙丽英终于不得不承认:“因为你是聋的,你和别人不一样。”
这句话有另外一个潜台词,似乎是导演对孙丽英而说,“因为你是女人,你和他们不一样”。《漂亮妈妈》是一部完全女性视角的电影。影片所触及的环境就是孙丽英的整个世界。她在生活中盲目而无助,欲望并不大却依然难以实现。她只能对热心帮她的女友说“你要是个男的就好了”,她在最无奈的时候,也只能对儿子说“你有委屈还可以找我,但我去跟谁说啊”。
在中国电影中,女性长期扮演着一种无私奉献、耐于受苦的“地母”形象(否则就容易变成一个“坏女人”),从最早期的《孤儿救祖记》到《天云山传奇》直到最近。但在这部影片里,观众会突然发现,其实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让孙丽英依靠。多少年来都是“他”在说她,说她好或者坏,“她”却很少说过自己的感觉。孙周想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看“她”看到的,说“她”想说的。
这部电影的力量在于它的真实。在所有宜于煽情的段落,孙周都及时“打住”。他说:“我只能提醒大家,我看到了。我不能去‘关怀’她。”
当已经离异的丈夫出车祸以后,孙丽英没法儿向聋儿郑大说清发生了什么事。她把一只活虾烫过,放到桌上,向郑大解释死的含义,“死了,爸爸死了”。但郑大却指着虾兴奋地叫道,“红了!爸爸红了!”这段戏并不是导演本人最欣赏的,而巩俐在最初表演时也觉得别扭——这肯定不符合巩俐本人的表述方式。但观众观看时却不能不受到震撼:生活就是这样残酷、平淡而真实。
给电影导演划代分类是很不科学的办法,孙周就是一个明证。80年代他就拍摄了颇有影响的城市题材电影《给咖啡加点糖》。1993年的《心香》,又成为国内少有的一部诗化电影。京京的父母忙于工作和离婚,让他只身到广州投奔外公。外公从前是个京剧名角,在外婆去世后一直郁郁寡欢,很不情愿地接待了十来岁的外孙。莲姑虽然和外公相爱已久,但又在等待40年音信全无的台湾丈夫。爷孙两代人,不知不觉影响了彼此的生活。
北京电影学院倪震教授指出,外公、莲姑、京京、珠珠,他们是生活在城市之中,又是游离于城市之外的人;对生命的体验与期待,最终化成一种流水一般的感悟,使《心香》颇具禅宗意味。能够在喧嚣世俗之中,另觅“心香”,使孙周成为90年代非常个性化的一个导演。《心香》又被誉为第一部广告化的电影,乃是因为孙周对精致影像的准确把握。在拍摄此片的前后几年,孙周确实一直在拍广告。
《心香》中有很多富有意味的场景,其中反复出现的是一个渡口,正是这个渡口将剧中人与纷扰的城市隔开,也将一个精神的、情感的世界与物质的、庸俗的世界分离。戏剧性的是,现实中这个位于广州市区内的渡口如今已不复存在,似乎恰恰昭示了,孙周接下来的这部影片——《漂亮妈妈》所具备的彻底的世俗性。哪怕“巩俐”只有一个愿望:让儿子与正常儿童一样生活,她也不得不全部投入这个世俗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