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再好不过,乔治·布什》到《我父辈的信念》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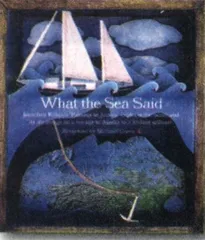
由于资料迟到的原因,两刊的日期相差较多,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可比度;但从上榜的书目上,我们仍不难看出二者间的差距;不过,新书之多(共10种)仍引人瞩目。其中尤以传记和回忆录为代表。
首先是布什前总统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布什一向以待人礼貌友好,为人真诚正直而著称,在选民中口碑极佳。当年他作为里根的副手参加竞选时,竟有人是因为他而投了里根一票。甚至有人迷信地认为,里根的当选是注定要被暗杀的(根据是林肯·肯尼迪等前总统的遇刺,后来里根果然遭枪杀,不过未死),认为布什一定会递补为总统。在他这部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中,最早的是他在海军中时的信件,其中包括18岁时写给母亲谈及男女交往方面观点古板的一封:“亲吻并非一个女孩不顾一个男孩带她出去多少次或花多少钱而欠下他的义务……我不高兴我的妻子曾经结识过别的男人,而且依我看,她也这样期望我才是公平的。”还有他驾驶的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被击落,两名机务人员牺牲后,写给他父亲的一封感人的长信:“恐怕我对此事很有些女人气了,因为我在救生筏中着实抽泣了一阵。这事很让我心烦意乱。我确实告诉过他们,而且在我跳伞时觉得他们已经跳出机舱了,而如今我感到对他们的命运负有可怕的责任。”看来,布什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是从年轻时起的。
布什1968年当众议员时,曾在地方报纸上写过一篇专栏文章,提出了自己的核心政治目标:“我们应该寻求新的途径将政府职能转给……那些十分成功的自愿组织。”他的一位助手甚至还使用过“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样的字眼。但他在总统任上却从未能将这一目标变成相应的政治想象力。或许可以说,他很温文尔雅,但绝不是个铁腕人物。
大概是布什的儿子乔治·W·布什——小布什现在又踏上了竞选总统之路,有一部以他本人为主角的作品:《长子——乔治·W·布什和布什家族王朝》(First Son,George W.Bush andthe Bush Family Dynasby),作者是比尔·米努塔格里奥(Bill Minutaglio),《达拉斯早晨新闻》的记者。他在该书中勾勒出了小布什与其父大体相似的经历:在安多瓦的少年生活,在耶鲁的大学就读,在飞行学校服兵役、学飞行,投身石油业,最后步入政坛。
小布什是耶鲁大学68届的学生,同学中不乏当今美国政界要人(如副国务卿斯特罗伯·塔尔伯特),彼时大多卷入了反战和反文化的校园风潮;而支持共和党的学生则在另一边设置路障,如奥立弗·斯通则离开邪鲁去了越南。但小布什却哪一派也不参加,到他父亲曾参加过的体育俱乐部中去度过一个又一个小时,就当时而言,如大学年鉴中所说,那里反倒成了一处“温和的小枝节”。他认为他的耶鲁生活从来没有沉闷,尽管有人认为这种轻松不宜任总统,但至少可以看出,小布什不是个受周围形势左右的人。他在1988年曾经写道:“我就是我,知道自己想去何方——具有达到目的的经历:工作,和平,教育。我知道是什么驱动着我——使我感到舒适:家庭,忠诚,朋友。强化家庭,抚养子女,人人都至关紧要。”
与其父相比,小布什似乎缺乏前总统的那种耐心,他目前致力的竞选运动却更训练有素、更专业化和更务实。果真当选,或许会更讲效率。无论如何,小布什尚无乃父的声望,因此,老布什的书虽然只是旧有文献,仍比这本有色彩斑斓故事的《长子》更畅销。
另一部已上榜7周的《我父辈的信念》,恐怕也是为竞选而做。作者约翰·麦凯现为参议员,也在竞选总统,他的特殊经历是曾在越南战场上被俘,蹲了5年半的监狱。1973年被释放回国时曾发誓要继续为公众服务,而他那拄着双拐一瘸一拐地走路,却挺胸敬礼的形象,使这位在侵越战争中被击落座机,摔得遍体鳞伤的飞行员,成了美国英雄。
其实,从他被俘之日起,就已经引人注目,因为他刚刚被俘,其父杰克·麦凯就被任命为美国太平洋地区(包括越南)的总司令。对于这一微妙关系,越美交战双方当然都不会忽略。
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美国的海军四星上将,是二战中的英雄。祖孙三代均毕业于位于马里兰州首府的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约翰17岁那年,当一艘新服役的驱逐舰以他祖父命名时,他就和在对日作战中屡立战功的海军五星上将威廉·F·哈尔西(1882~1959)共饮烈性威士忌酒了。该书书名暗示着这一军人家庭特有的荣誉感:军人忠于国家。尽管约翰后来的生涯与战场上和敌人面对面的厮杀毫不相干,该书只写到他获释为止。帮他撰写该书的马克·索尔塔,正是他在军中任职时的参谋长。
于是,读者更感兴趣,也是他人生更引起争论的1973年以后的故事,便由罗伯特·蒂姆伯格(Robert Timberg)在《约翰·麦凯:一部美国的奥德赛》(John Mc Cain:An American Odyssey)中完成了。通过该书,我们可以了解美国人的价值观。
嫩绿色的地狱
11月出版的《温柔》是克里斯托弗·奥诺雷的第二部小说,评论家说这本书就是一个嫩绿色的地狱,因为他写出了儿童身上残酷的一面。小说只有150页,分了很多简短的章节,始终用第一人称叙述,但每章都有不同的叙述者。故事的主人公是个11岁的小男孩,他卷进了一起谋杀案,他并没有杀人,但是他的一个好伙伴把尸体指给他看了,接下来两个孩子就开始了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游戏。
作者29岁,除了写小说,还写儿童读物,突然写出如此反儿童的东西,书评界自然关注。《解放报》对他进行采访,一开头就问:“你觉得给孩子看的书和给成人看的书有什么不同?”奥诺雷回答说:“写给成人看,我能允许自己冒昧,把事情说出来,把适合这种事情的形容词、动词、名词用上去。大家都说孩子天性也是残忍的,但他们的残忍是如何体现的呢?《温柔》就是要揭示野蛮行径及其相关的复杂性。人从小就会折磨别人,会杀人,孩子跟大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们没有社会责任感。我写这本书,就是要强迫读者看见他们不愿意看的东西。”至于这本书可能不被读者喜欢,奥诺雷丝毫不以为意,他这样表述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如果谁跟我说‘我喜欢你的书’,我一定会觉得他就像在跟我说‘我喜欢你做爱的方式’,结果我只能这样跟他撇清——‘我们俩可什么都没一起干过!’读者对小说的亲密感,是读者自己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