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类优化的哲学之争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熊康)
浮雕中理想的人类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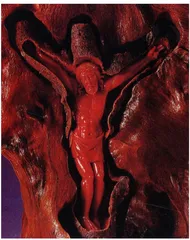
日本科学家对人工羊水的研究

精子银行中的检测

暖箱中的早产儿
人体工程学
不久前,在巴伐利亚召开的一次海德格尔研讨会上,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耶克(Peter Sloterdijk)晦涩地提到了海德格尔、尼采这些思想巨人曾经涉猎的领域,即“人类的自体成形潜力”。他在演讲中以尼采的学说为依据,主张除了对动物王国里最高级的直立行走动物——人进行传统的社会“驯服”之外,还要考虑对其进行“繁衍过程中的培植控制”和“选择”。这还不算,他还故意运用了肯定会引发人们的怀疑和厌恶的字眼——“人的培植”和“人体工程学”。此言一出,随即便在德国知识界引发了世纪末的震动。
德国人不禁要问,他莫非梦想在蒸馏罐里培育出超人来?
1999年9月初,当德国新闻界就斯洛特迪耶克的惊世话语论战犹酣时,美国的生物学家小组向世人展示了他们最新的试验室产品:一只被他们借助基因技术配备了智力的老鼠。
尽管器官移植的方法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科学家们尚未触及到胚胎细胞本身所包含的人类遗传特征。人类遗传学还仅只是一个在医院日常事务中起到次要作用的诊断原理。不过,现代医学还是早已把人当成了制模材料。外科医生、器官培植者、试管婴儿研制者和精神药剂开发者纷纷把塑造人的肉体和精神当成了目标。
“生物学的世纪”
在生物技术人员的试验室里,人的皮肤和软骨的培植已经趋于成熟了。医生们研制成了粉末化的颌骨,用人类细胞为原料制成了耳肌。他们让肝脏组织和结缔组织缠绕在人造的骨骼结构上,想从胚胎细胞中为重病号培植出第二个器官来。
借助医学手段塑造精神和性情的做法也进入了医生的实践。成千上万焦虑好动的孩子吞下了利他林,这种药能缓解他们的不安情绪,但同时也会抑制他们的创造才情。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人通过服用Prozac或类似的药剂感受到了快乐。药剂学难道不正想通过这种方法创造出一种新的时髦的人类类型吗?
在通往人类培植的道路上,生殖医学取得的进步最为可观。在美国的精子银行,女士们可以在大量的目录册中为自己未来的孩子寻找父亲。精子的主人拥有各种颜色的头发和皮肤、不同的身高、种族和学历,甚至还有诺贝尔奖得主可供选择。许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已经变成了现实。
每一年都会有更多的新鲜事情出现:9月份一个医生小组宣布,他们为一位30岁的舞蹈演员植入了一个卵巢。纽约的研究者声称,他们计划对睾丸进行移植。日本早已翻开了移植医学上的新篇章:在那里的试验室,一个盛着羊水的塑型盆取代了子宫,而山羊的胚胎已经在其中存活了三个星期。
受孕、出生、心理健康和死亡,这些原本归造物主、命运或是自然主宰的范畴,如今却被生物科学家们的创造意志强行占领了。当然,这在许多幻想家看来只不过是前奏。他们预言,“生物学的世纪”根本还没有到来。现在,生物技术人员的目光瞄准了最后一个禁忌——人类的胚胎。由此,塑造真正在基因上得到改进的人的计划被列上了日程。
“我们接管了对于我们自身进化的控制权”,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物物理学家格里高利·斯托克宣布。为了不给人以反驳的口实,他又补充道:“没有什么方法能够阻挡这一技术。”
“太阳帝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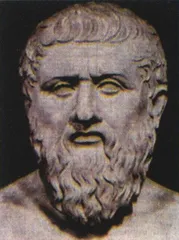


柏拉图、尼采、斯洛特迪耶克
斯托克的说法并不是孤立的。纽约的分子生物学家利伯·卡瓦雷利警告说,基因设计将会“比核裂变更具重要性,且其危险性不小于核裂变”。普林西顿大学的利·西尔沃甚至认为,新型人的诞生已经指日可待。
德国新闻界也不乏类似的预言。分子生物学家詹斯·赖希2月初在《南德意志报》发文说:“不仅生命的开始和人的体质配置可以通过技术来完成,生命过程和对生命的期望也是如此。”不久后,弗朗西斯·福山也在刊登于该报的文章中说,技术在未来将缔造出少些暴力倾向的人来,这种可能性几乎是无法抵制的。随后,他还谈到了“蒸馏瓶中的超人”以及“后人类的历史”。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斯洛特迪耶克关于基因技术培植的想法目前是不切实际的,但这无关紧要。在他的眼中,“人种政策上的决定”也仍然是遥远未来的音乐。令反对者坐不住的是他在讲话中所主张的原则性政策转折:以培植取代教育,以生物学取代政治,以人种取代阶层。在反对者看来,这实在颇具挑衅意味。
需要强调说明的是,纳粹分子关于人种控制和培植的妄想绝对不是由他们所发明的。在社会综合转折的过程中,单个人也必将突变为理想的生物,这种梦想在西方国家存在已久。
许多空想家的依据源于雅典人柏拉图。公元前375年,他在他的对话录《国家》中向苏格拉底提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公正?柏拉图设计了一种严格按照等级来划分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哲学家国王”可以决定,“最优秀的男人和最优秀的女人可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相会”。
在宗教改革开始的年代,英国王室法学家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中,引用了柏拉图的一些主导思想。100年后,多明我会教士托马索·堪帕内拉设想了一个“太阳帝国”,这个帝国中弥漫着上佳的繁殖条件:“高大美丽的女人只会和高大美丽的男人交合,胖女人与瘦男人、苗条女人与强壮男人交合,这样他们才可以成功地达成均衡……卧室里摆着著名男人的漂亮画像。”
直到进入启蒙时代,改进人类的想法在人们头脑中扎下了根。
早期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立叶在1808年时对未来的设想是:人们按照严格的规则在公社中生活,在那里,他们可以活到144岁,长到2米高,200公斤重。他预测,人的资质会呈天文数字增长,世界人口将达到30亿——这在当时可是个了不得的数字——诞生出3700万荷马般的诗人,3700万具有牛顿般思想才能的数学家,以及无数的其他超级人才。
在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划时代著作问世16年后,希腊语教授、柏拉图的信徒尼采写道:“通过幸运的发明,可以把大部分的个人教育到比迄今为止通过偶然性所达到的更高的水平。我的希望是:培育重要的人物。”
尼采所谓的“培育”近乎最严格的精英教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提到了“人种的改进”。1981年秋天的时候,他已经在想,“能不能以其他人为代价,将一部分人培育成更高级的人种”即“新贵族”?
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超人”的概念出现了。后来,尼采毫不犹豫地建议,“要为重大冒险行动以及教育和培育的全部尝试进行准备,以便使迄今为止名叫‘历史’的瞎扯和偶然所占据的主宰地位划上句号”。
从这类幻想中得出的结论显然影响到了其他人。诗人戈特弗里德·本在1933年写道,他期待着一种新的“德国人”的诞生,这种人“半是源于突变,半是由于培植”。
对于德国人来说,“优生学”的概念听上去就像是希特勒人种培植和人种毁灭妄想的一个变体。纳粹打着优生学的幌子为成千上万的人做了绝育,并且屠杀了几百万人。
但优生学却非国家社会主义者的发明。几十年来,它被许多科学家视为通向人类未来的阳关大道。这一学说的信奉者不仅包括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还有丘吉尔和罗斯福。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很久,优生学的观念就在左派和右派的圈子里被接受了。
“优生学”
“优生学”(希腊语中的含义是“遗传特征优良”)一词是由达尔文的堂兄弗朗西斯·高尔顿在1883年创造的,他称它是通过培育来改进人类基因的科学。从此,研究者们终于正视了在生物学意义上改进人类的梦想。在他们看来,对遗传特征的干预恰恰是伦理学的要求。20世纪开始后,世界各地建起了优生学的专业协会。
这些人的设想是:一旦成功地阻止了致病基因和其他有害基因的扩散,那么在短短几代的时间里,人类在遗传保健方面就会上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摆脱疾病和久病不愈的状况,摆脱饮酒癖和犯罪的现象,甚至摆脱贫困。
新的学说认为,优生学带给人的是一个辉煌的未来。诺贝尔奖得主赫尔曼·约瑟夫·穆勒在1933年说,只要经过200年的培植,“多数人都可以具备像列宁、牛顿、达芬奇、巴斯德和贝多芬这样的资质”。
在当时的研究者看来,贫穷不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而是不优良的道德和学习基因的载体。美国优生学家查尔斯·达文波特写道,“东南欧血统者的大量涌入”会在基因方面毁掉美国人,致使未来的美国人“色素沉着趋黑,身材变小,性格脆弱”,造成“偷窃、儿童拐卖、强奸、谋杀犯罪加剧”。
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美国在20、30年代让据说携带了劣质基因的人做了绝育,并过分细致地检查了移民的遗传特征。
德国的优生学研究进展与别国没有什么两样,只有一点不同,即德国优生学家自1933年起肆无忌惮地实施了他们的设想。人种保健学和优生学成了希特勒独裁的基石。
希特勒上台几个月后,“遗传病新生儿预防法”颁布,几千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癫痫病患者、盲人、嗜酒者和存在精神障碍者被消了毒。婚姻健康法禁止遗传病患者结婚。另一方面,纳粹却为在“遗传上健康”的非犹太人“同胞”提供结婚贷款,以便促进优质基因的再造。最不可思议的要属纳粹头子希姆莱实施的一项秘密计划,他让雅利安人妇女尽可能地与纳粹男子交合受孕,目的是再造出纯种的雅利安人后代。凡此种种致使二战后优生学在世界范围内丧失了名誉。
战后时期,双螺旋结构变成了整个科学领域的圣像,它能把一切遗传分子的培养基以及新的人类设计计划的原材料铸造成型。70年代初以来,生物技术人员也可以对遗传特征的线路进行剪切和重新粘合了。试管里诞生了拥有萤火虫基因的会发光的烟草作物,以及带有母鸡基因的宽肩膀老鼠。
基因技术的问世为医学治疗开辟了新的前景,现在,看似顽固透顶和不可战胜的恶心呕吐症状终于可以被连根剔除了。整个生物学都能在分子的螺旋型结构中找到渊源。但这场被宣告来临了的基因技术革命能否兑现它的诺言呢?通过消除遗传特征中的致病因素,一个能够抑制所有疾病的医学时代已经开始了吗?
人类培植时代的规则?

1933年时宣传人种知识的招贴画

纳粹在进行人种研究
迄今为止,人们对此作出的结论仍然很谨慎。尽管产前基因诊断已经成为医院的固定项目,但它却仅限于在知道父母亲带有重大遗传障碍的情况下,对母体中的胎儿进行检查。对于被诊断出的胎儿疾病,唯一的疗法仍是堕胎。
生理基因疗法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比这还要少。生物学证明自己要比乐观的研究者们所意识到的复杂得多。按照法国人詹姆斯·安德森的说法:“要是我们想期待成果的话,只怕是要等到太阳熄了火。”
现在,业内人士正在谈论的是胚胎疗法方面的突破。真正在基因上控制人的做法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列上了他们的日程表,基因外科医生就要朝着受精卵发起冲击。
迄今为止,基因研究者们总是只看到复杂的分子相互作用的表面。对于这一天然的互相牵制体系的每一次介入都可能会引发没有人想得到的后果。致病基因并非是由进化制造出来折磨人的。研究者们猜测,糖尿病体质的形成是为了适应饥饿状况。糖尿病基因可以更好地吸收营养,因而能够克服困境。如果试图消除这种基因的话,就可能会使人冒未来不再能适应改变了的环境的危险。
基因医学的幻想家们试图把从蒸馏罐中培植人的想法植入人们的头脑,他们对此直言不讳。如今,自然科学已经能够改变关于人的概念。尽管一次次地遭受失败,但他们仍在寻找着智力、攻击性或是忠诚的分子培养基。就这样,生命的多样性被紧缩到了遗传信息之上,大脑降格为“湿件”(计算机专家用语,指软件、硬件以外的“件”,即人脑)。
由此,一个哲学上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哲学能否建立人类培植时代的规则?它能否容忍人的形象的变化,会不会反对这种变化?
为了不致背上哲学思维的包袱,美国生物学家率先选择了他们自己的哲学:在过去25年间,生物伦理学的原则已经形成,其任务是,为如何对待来自生物试验室的新技术提供行动指南。
从哲学上来看,一个新的伦理学分支的形成被称作重大的进步。科学家们的借口是,像化学、核技术和信息技术这样彻底改变了世界的学科都没有能够衍生出自己的伦理学,但生物学要被赋予特殊地位,它应拥有属于自己的伦理学,因为它研究的是人本身。蒸馏罐婴儿路易斯·布朗在医学上的父亲之一罗伯特·爱德华兹说:“伦理学必须适应科学,而不是反过来。”